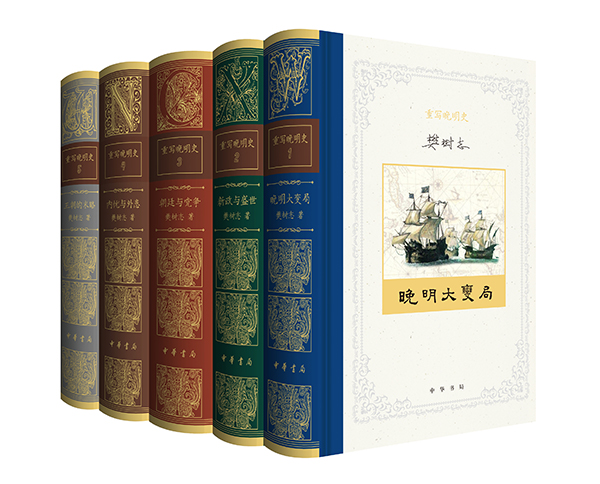-
 中华文化教师素养读本
楼宇烈,傅首清主编
¥58.0
中华文化教师素养读本
楼宇烈,傅首清主编
¥58.0
-
 辽史--全五册(精)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
脱脱著 刘浦江整理
¥280.0
辽史--全五册(精)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
脱脱著 刘浦江整理
¥280.0
-
 南明史(精装本)
钱海岳撰
¥980.0
南明史(精装本)
钱海岳撰
¥980.0
-
 宋书(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平装本)
(梁)沈约 撰
¥360.0
宋书(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平装本)
(梁)沈约 撰
¥360.0
-
 魏书—(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精装)
魏收著 何德章,冻国栋修订
¥510.0
魏书—(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精装)
魏收著 何德章,冻国栋修订
¥510.0
-
 史记--全五册(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精
[汉]司马迁撰 陈曦、王珏、王晓东、周旻译
¥298.0
史记--全五册(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精
[汉]司马迁撰 陈曦、王珏、王晓东、周旻译
¥298.0
-
 全元词(全三册)--中国古典文学总集
杨镰主编
¥298.0
全元词(全三册)--中国古典文学总集
杨镰主编
¥298.0
-
 金史(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精)
[元]脱脱等撰
¥540.0
金史(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精)
[元]脱脱等撰
¥540.0
-
 明实录 附校勘记(183册)布面精装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 黄彰健校勘
¥45000.0
明实录 附校勘记(183册)布面精装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 黄彰健校勘
¥45000.0
-
邹鲁文化研究 贾庆超等 ¥0.0
中国自古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传统,如《尚书》以记言为主,《春秋》以记事为主。言和事构成了历史材料的主体,如何利用“言”来增强历史叙事的场景性,是史家裁度材料时值得注意的问题。《重写晚明史》作者樊树志教授对各类史料中的“言”裁剪得当,化为己用,极大地增强了该书历史叙事的镜头感,是向传统叙事史学一定程度上的复归。
兹举二例,以观大貌。
例一:崇祯十一年,兵部尚书杨嗣昌主张集中全力平定内乱,倾向于与清议和,以缓和北方边境压力,黄道周连上三疏竭力反对。朝堂之上名为讨论纲常名教,实则针对“讲款”一事展开争论。
朱由检:朕幼而失学,长而无闻,时从经筵启沃中略知一二。凡圣贤千言万语,不过天理人欲两端耳。无所为而为之,谓之天理;有所为而为之,谓之人欲。多一分人欲,便损一分天理,天理人欲不容并立。你三疏不先不后,却在不点用之时,可谓无所为乎?
黄道周:圣学渊微,非臣所及。若论天人,只是义利分别,为利者以功名爵禄私之于己,事事专为己之私,此是人欲。为义者以天下国家为心,事事在天下国家上做,便是天理。臣三疏皆是为天下国家纲常名教,不曾为一己之功名爵禄,所以自信其初无所为。
杨嗣昌:臣入京闻黄道周品行学术为人所宗,意其必有持正之言,可以使臣终制而去。不谓其疏上自谓不如郑鄤,臣始叹息绝望。
朱由检:朕正要问他此事。
杨嗣昌:人言禽兽知母而不知父,今郑鄤杖母,禽兽不如,道周又不如彼,还讲甚么纲常!
黄道周:大臣闻言,应当退避,使人得毕其言。汉唐以来故事,谏官论执政者出听,谏官对仗读弹文。臣虽非言官,未有大臣跪在上前争辩,不容臣尽言者。
朱由检:你说了多时候,辅臣才奏。
杨嗣昌:臣为纲常名教,不容不剖陈。
黄道周:臣生平耻言人过,闻人之过,如闻父母之名。今日在上前与嗣昌角口,亦非体。臣知为天下后世留此纲常名教、天理人心而已。
朱由检:对君有体?这本前边引纲常,后边全是肆口泼骂。
黄道周:臣今日不尽言,则臣负陛下;陛下今日杀臣,则陛下负臣。
朱由检:你都是虚话,一生学问,止学得这佞口。佞口!
作者利用《明史》《杨文弱先生集》《春明梦余录》等史料生动刻画了性情耿直、淡泊名利的黄道周在朝堂之上出言顶撞崇祯帝,落得降六级外调处分的场景。
《重写晚明史》描述晚明吏治的痼疾:文官爱钱,从上到下的贪腐触目惊心。黄道周无疑是股清流。这段生动的对话,见出文官的文人骨气。这种文人骨气既是儒家涵养出的高贵品质,但在关键时刻也会成为权变决策的掣肘。皇帝本来支持杨嗣昌与清议和,及至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只得作罢。反对议和者占据道德高地,猛烈抨击,使得议和半途而废。士大夫勇于任事和短视软弱的双重性使得眼前虽有损尊严、长远或可翻盘的时机白白溜走。
例二:崇祯十七年正月至二月,农民军近逼畿甸的危急时刻,离崇祯帝殉国的三月十七日只数十日。朝堂之上就南迁之议展开争论。
李明睿:此诚危急存亡之秋,皇上不可不长虑!却顾只有南迁一策,可缓目前之急,徐图征剿之功。
朱由检:此事我已久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此意决矣。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尔且密之,密之!
驸马巩永固:若南迁,可招募义兵数万人,寇乱不难平也;若徒守京师,京师已玩弊久,只坐困无益也。
(皇帝把李明睿的奏疏交给内阁议论,首辅陈演坚决反对南迁,将奏疏透露给兵科给事中光时亨,要他谏阻。光时亨把南迁之议斥为“邪说”。)
李明睿:就使皇上发策南迁,此亦救时急着。唐室再迁再复,宋室一迁南渡,传国一百五十年。若唐宋不迁,又何有灵武、武林之恢复?又何有百五十年之历数哉?
(大臣们对南迁之议讳莫如深,使得原本倾向于南迁的皇帝感受到舆论无形的压力,立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朱由检:祖宗辛苦百战,定鼎于此土,若贼至而去,朕平日何以责乡绅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谢先经失事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独去,如宗庙社稷何?如十二陵何?如京师百万生灵何?逆贼虽披猖,朕以天地祖宗之灵,诸先生夹辅之力,或者不至于此。如事不可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
作者利用《绥寇纪略》《明季北略》《流寇长编》《牧斋有学集》等史料将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三到二月二十八日针对“南迁之议”的朝堂对话呈现出来(以上只是拈取关键对话)。我们看到,首辅陈演坚决反对南迁,光时亨把南迁之议斥为“邪说”,李明睿力主皇帝亲自南迁,皇帝虽与李明睿意见一致,怎奈阁臣怕背负千古骂名,不予声援!崇祯帝内心顾虑—恐遗恨于万世,动摇不定,终于错失良机。待农民军攻破畿甸,大势已去。
综合以上二例观之,制度问题当然是明朝灭亡的关键因素,但崇祯十一年与清议和的流产直接导致当年秋清军再次来犯,明朝在攘外与安内的抉择中失去主动;而崇祯十七年的南迁之议,或可让明朝偏安一隅,迎来卷土重来的契机,亦因阁臣不作为,生生错过。在与清议和、南迁等影响明朝命运的重大关节点上,夷夏之辨、华夏尊严使明朝继续国祚的良机丧失殆尽。
《重写晚明史》历史书写的“记言”特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作者在最后一册《王朝的末路》结尾用了《桃花扇》里明人的感喟寄托遥思:“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最后一句叹道:“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深沉的历史喟叹让人怅惘不已。这是后人对前人的“感言”,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记言”。
晚明的“全剧终”伴随着苍凉、悲愤、无奈的复杂情绪。其中历史当事人的“言”让人在鲜活的细节中看到人心底的各种执念以及由此带来的历史的必然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