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文化教师素养读本
作者:楼宇烈,傅首清主编
定价:¥58.00
中华文化教师素养读本
作者:楼宇烈,傅首清主编
定价:¥58.00
-
 辽史--全五册(精)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
作者:脱脱著 刘浦江整理
定价:¥280.00
辽史--全五册(精)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
作者:脱脱著 刘浦江整理
定价:¥280.00
-
 南明史(精装本)
作者:钱海岳撰
定价:¥980.00
南明史(精装本)
作者:钱海岳撰
定价:¥980.00
-
 宋书(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平装本)
作者:(梁)沈约 撰
定价:¥360.00
宋书(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平装本)
作者:(梁)沈约 撰
定价:¥360.00
-
 魏书—(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精装)
作者:魏收著 何德章,冻国栋修订
定价:¥510.00
魏书—(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精装)
作者:魏收著 何德章,冻国栋修订
定价:¥510.00
-
 史记--全五册(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精
作者:[汉]司马迁撰 陈曦、王珏、王晓东、周旻译
定价:¥298.00
史记--全五册(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精
作者:[汉]司马迁撰 陈曦、王珏、王晓东、周旻译
定价:¥298.00
-
 全元词(全三册)--中国古典文学总集
作者:杨镰主编
定价:¥298.00
全元词(全三册)--中国古典文学总集
作者:杨镰主编
定价:¥298.00
-
 金史(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精)
作者:[元]脱脱等撰
定价:¥540.00
金史(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精)
作者:[元]脱脱等撰
定价:¥540.00
-
 明实录 附校勘记(183册)布面精装
作者: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 黄彰健校勘
定价:¥45000.00
明实录 附校勘记(183册)布面精装
作者: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 黄彰健校勘
定价:¥45000.00
-
邹鲁文化研究 作者:贾庆超等 定价:¥0.00
前两期我们共读《淮阴侯列传》《萧相国世家》,探寻了韩信的军事传奇与萧何的治国之才。
本期聚焦“汉初三杰”的最后一位——张良,从《史记・留侯世家》的字里行间,解锁“没有张良,何来刘汉”的深层逻辑:他无萧何抚民之能,无韩信领兵之勇,却以独一档的智慧,既助刘邦成就帝业,又为自己谋得功成身退的圆满,堪称古代智者的典范。

一 出身与青年:从五世相韩到圯上受书——张良的“起点密码”
《留侯世家》开篇便为我们勾勒出张良的人生底色,也埋下了理解他的关键线索。
名“良”字“子房”:星象赋予的隐喻
张良,字子房,其名与字的关联藏于星象之中。据《史记・天官书》记载,“汉中四星曰天驷,旁一星曰王良”,而“东宫苍龙,房、心......房为府,曰天驷”——“良”指“王良” 星(主驾驭天驷),“房”指“房宿”(亦别称天驷)。为张良取字者,或许因 “汉中四星” 与“房宿”同称“天驷”的关联,借“王良驱天驷”的意象,为“良”配字“子房”,既含星辰之雅,也暗合其未来“辅佐明君、运筹天下”的宿命。
圯上奇遇:《太公兵法》与“强忍”的觉醒
青年张良的人生转折,始于博浪沙狙击秦始皇的“血气之勇”,终于下邳圯上受书的“智者蜕变”。《太公兵法》《黄石公三略》《素书》三部经典,实则是后世对“圯上授书”的溯源:
《太公兵法》:《正义》引《七录》称其为姜子牙所著,共三卷,是圯上老人授张良的核心典籍,也是他辅佐刘邦的“谋略蓝本”;
《黄石公三略》:《隋书・经籍志》认为是黄石公所作,东汉光武帝曾引其制定政策,书中 “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为帝王师”等句,恰与张良荐韩信、彭越、黥布,及刘邦对其的尊称呼应;
《素书》:晋代盗墓者从张良墓中获《素书》,张商英《素书序》称其“圯桥所授真本”,书中“阴计外泄者败”“吉莫吉于知足”等条,更是张良一生行事的精准写照(如劝封韩信防泄密、择留地自封显知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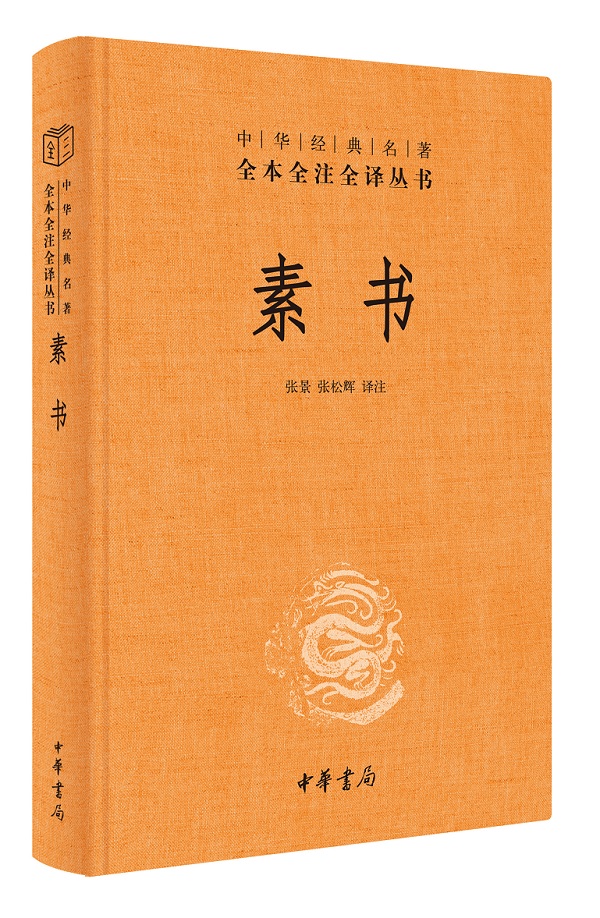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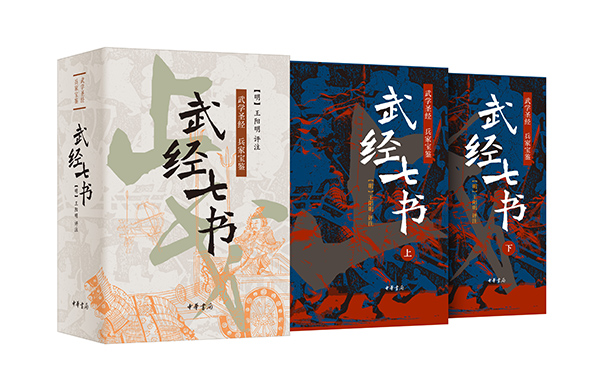
而“拾履”的核心,是凌稚隆所言的“强忍”二字。
老人三番刁难“下取履”“为我穿履”,张良压下怒火照做,这一品质贯穿其一生:击秦军时“因解(懈)而击”是强忍(不急于强攻),劝刘邦还军霸上是强忍(不贪秦宫享乐),捐关以东予三将是强忍(不吝土地换合力),蹑足封韩信假王是强忍(不逆刘邦情绪),天下定后辟谷学道是强忍(不恋权位)。
“强忍”不是妥协,而是张良审时度势的智慧底色。
二 佐汉定天下:帷帐之谋——从灭秦到破项的 “关键先生”
《留侯世家》第二部分,详述张良辅佐刘邦的核心历程,每一次谋略都堪称“扭转战局”,也让我们看清他与刘邦的独特关系。
谋略:无兵却胜万兵
峣关用计:反“减灶之计”设疑兵,趁秦军懈怠突袭,助刘邦轻松入关,这是他首次为刘邦献谋,尽显“以智胜力”;
鸿门宴破局:提前拉拢项伯,以“兄事之”结好,宴中借项伯求情、樊哙闯帐,助刘邦虎口脱险,是“未雨绸缪”的典范;
下邑献大计:刘邦兵败彭城后,张良力荐黥布(楚之猛将)、彭越(反楚诸侯)、韩信(军事天才),断言“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为刘邦制定“联弱抗强” 的核心战略;
阻封六国:郦食其劝刘邦封六国后代以弱楚,张良以“8根筷子”论证其误(如 “无复立者”“失信于功臣”),避免刘邦陷入“分地失人心”的绝境;
劝封韩信:刘邦怒韩信求封“假齐王”时,张良“蹑足”提醒“不如因而立之”,防韩信叛汉,稳住灭楚大局。
刘邦与张良:不止君臣,是“主宾”
刘邦与萧何是“君臣”(萧何掌治国,需承行政之责,属 “主从从属”),与韩信是“君将”(韩信掌军事,需听调度指挥,属 “主令臣行”),与张良是什么关系?答案藏在“主宾”二字里——刘邦是掌舵天下的“主”,张良是身负智慧的 “宾”,二者是“主敬宾、宾辅主” 的相得关系,而非简单的从属。
这份“宾”的尊贵,先见于称呼:刘邦对萧何常称 “萧相国”(重其官职),对韩信或直呼其名(论功时亦称“将军”,显指挥意味),唯独对张良,始终以“子房”“先生”相称。这是对“宾客”的礼遇,而非对臣子的日常称谓。在古代礼仪中,称字不称名、称“先生”,是对有德有才者的敬重,恰如主人对待座上贵宾,不以外在职位衡量,而以人格与智慧相待。
更关键的是“宾”的定位:张良不掌一兵一卒,不主一寸政务,却能以“宾客” 的身份,站在刘邦身侧提供最核心的战略支持。他无需像萧何那样“抚民给粮” 承担具体职责,也无需像韩信那样“领兵征战”受军纪约束,却能以“宾”的独立视角,成为刘邦最可靠的“智囊后盾”。
三 建国之后:安汉与自保——在“夺嫡之争”中全身而退的智慧
刘邦称帝后,张良面临两大考验:一是功臣分封的风波,二是刘邦欲废太子(惠帝)立刘如意的“夺嫡之争”。但他却能安然无恙,核心在于“自保智慧” 与 “顺势而为”的结合。
自保:不贪不恋,低调避祸
择留受封:刘邦欲封张良 “三万户”(顶级功臣待遇),他却选 “留” 地(与刘邦初遇之地),称 “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既表感恩,又显 “知足”,避免功高震主;
辟谷学道:刘邦定都关中后,张良以 “多病” 为由 “学辟谷,道引轻身”,主动退出权力中心 —— 此时韩信已被抓贬为淮阴侯,他以 “弃人间事” 避祸,是 “当退则退” 的清醒。
夺嫡:以柔克刚,顺势安汉
刘邦执意废太子,吕后求张良相助,他未直接劝谏,而是用“设变致权”之法:引入“商山四皓”,让四人陪同太子赴宴。刘邦见“四皓辅太子”,误以为太子 “得人心”,遂放弃废立——这既符合《素书》“设变致权,所以解结”,也因张良看清“刘邦死后吕后掌权,保惠帝更能安汉”的大势(顺势而为),既未忤刘邦,也未得罪吕后,最终 “安然无恙”。
四 太史公之叹:张良的“智者画像”
《留侯世家》结尾“太史公曰”,司马迁以“悠游唱叹”道尽对张良的推崇:“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他不写张良的“勇”,不写张良的 “功”,独写其“智”——这份智慧,是“强忍”的克制,是“谋全局”的格局,是“知进退”的清醒。张良的智慧是全方位的,大到经天纬地(定汉基),小到自我保全(避祸端),缺一不可。
张良的智慧穿越千年,对当代普通人仍有深刻启发:
后发制人,甘于人后:劝刘邦还军霸上,他在樊哙之后发声;劝定都关中,他在刘敬之后附和——不抢功、不冒进,等局势清晰再行动,更易被接纳;
欲取之,先予之:结好项伯时“兄事之”,先予“尊重”,再得“鸿门宴解围”;捐关以东予三将,先予“土地”,再得“灭楚合力”——懂得“舍”才能“得”;
以柔克刚,不硬碰硬:刘邦废太子,他不“强谏”,用“商山四皓”间接说服 ——面对强势者,“柔”比“刚”更有效;
无欲则刚,不贪为宝:不贪三万户封地,不恋权位,刘邦反而更信任他——欲望越少,越不易被牵制,越能掌握主动权;
顺势而为,不逆大势:保惠帝而非刘如意,因看清“吕后掌权”的大势——顺势者易成,逆势者难存;
当退则退,及时止损:天下定后辟谷学道,避开功臣清算;刘邦死前学道避祸,躲过韩信、彭越之祸——懂得“退”,才是长久之“进”。
读《留侯世家》,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完美的神”,而是一个“清醒的人”:他有“为韩报仇”的血气,也有“圯上拾履”的隐忍;有“定天下”的谋略,也有“保自身”的清醒;有“帝者师”的荣光,也有“从赤松子游”的洒脱。张良的智慧,不仅是古代的“治国之术”,更是当代人的“处世之道”——这或许就是“汉初三杰”中,他能“功成身退,安然一生”的终极答案,也是《史记・留侯世家》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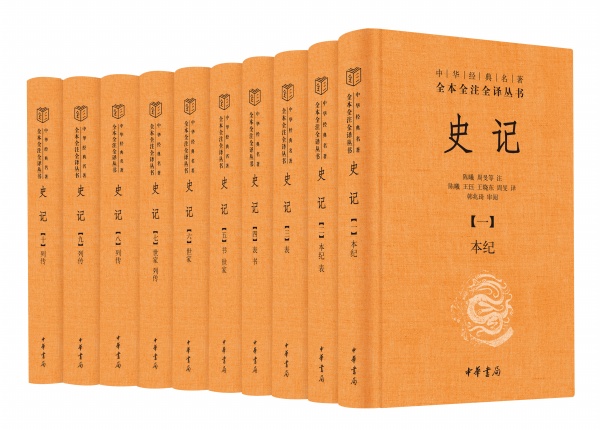

www.zhbc.com.cn zhbc@zhbc.com.cn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邮编: 1000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