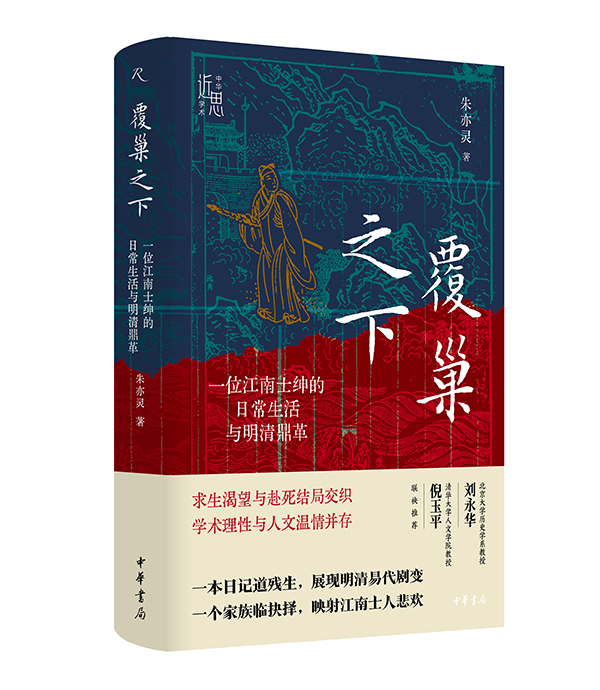导语
晚明是一个充满魅力与张力的时代,繁荣的市民生活与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并存,江南的岁月静好在清兵入关的铁蹄下终成落花流水。中华书局先前曾推出樊树志先生的《重写晚明史》(五卷本),系统地描绘出一幅晚明历史长卷。近期再版的《梁方仲著作集》,则有助于读者从经济史角度理解晚明社会的变迁。然而,在明清易代的剧变之中,一个个具体的人又是怎么样生活的呢?
南开大学青年教师朱亦灵的新著《覆巢之下:一位江南士绅的日常生活与明清鼎革》,便是对这个问题的诚意解答。他依托嘉定文人侯岐曾一年有半的详尽日记,结合传播学、医疗社会史及统计学等方法,从日常生活视角还原了这位“明遗民”竭力求生的挣扎与赴死的不甘末路,并探讨了明亡清兴之际江南士人普遍面临的命运与抉择。为了帮助广大读者走近侯岐曾其人其世、了解作者的治学心路,我们邀请到朱亦灵老师对若干相关问题进行了回答,详见下文。也欢迎广大读者在评论区留下您的问题或读后感。
01
《覆巢之下》一书源于您的硕士论文,您是因为什么原因在数年后将之扩写成书?
《覆巢之下》由我的硕士论文修订而成。学位论文的写法可以是数篇专题论文的整合,也可以较具整体性,写出来就像一本书,我更偏好后一种写法。2019年夏硕士答辩时,几位校内答辩委员表示文稿今后可考虑修订出版。但读博三年学业紧张,无暇抽身他顾,只能将修订工作搁下。直到2023年中,拙稿获评天津市优秀学位论文,三位校外推荐专家也做出了类似评价。我就不再犹疑,决心寻机出版了。2022年底,中华书局的编辑老师已问我是否有出版博士论文的意向,我虑及博论草成、尚需修订,惟有暂且辞谢。此时出版硕论的决心既定,便就此事洽询编辑,很快就《覆巢之下》的出版与中华书局签订了合同。
严格来说,从硕论到成书不是“扩写”,而是“缩编”。硕论原稿为26万字,修订后缩减为近21万字。删节的部分主要是一些赘冗或没有把握的论述,以及不少过分刻板而“学究气”的起承转合,并未破坏原稿的结构与核心观点。在“减”之外亦需有“增”,具体而言,是绪论、结语与第一章基本重写,第五、六章因须将发表在期刊上的论文重新并入,内容又涉及“大历史”,故也改动较多。二、三、四章修订较少,主要是文字润色,兼有史料与学术史文献的增补。希望最终呈现出的样貌,是一部具有一定可读性的学术著作。可读性虽然不是评判学术著作价值的主要标准,但《侯岐曾日记》的故事既已如此完整而精彩,倘若研究成果缺乏可读性无疑是可惜的。正如孔飞力所言,如果研究者把一段好故事反而讲得无聊,是对史料的浪费。
02
有关嘉定侯氏的前人研究已有不少,如《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第一等人》《嘉定忠臣》等。您觉得《覆巢之下》有什么创新之处?
在明清之际的士人家族中,嘉定侯氏确实较受今人关注。邓尔麟教授1981年著《嘉定忠臣》是研究明清之际江南社会的经典之作,特别是对抗清运动进行区域社会史的解读尤具前瞻性。不过,是书对侯岐曾着墨甚少,一些论述在今天也有待商榷。《嘉定忠臣》出版后,直到我撰写硕士论文的2018—2019年冬春之际,除张乃清先生《上海乡绅侯峒曾家族》外,市面上未见一部研究嘉定侯氏的专著。我当时已在网上读到周绚隆先生为《侯岐曾日记》撰写的四篇札记,这四篇札记文笔引人入胜,更兼考订精详,对我了解侯家亲友的身份与关系网络有很大帮助,节省了许多自行考证的功夫,可以将精力放到对日记文本的解读上。之后虽又涌现一些新的研究,但时至今日,拙作《覆巢之下》的研究视角、内容与前人著述仍有较大差异。首先,避免将侯岐曾描绘为传统的明末殉国者形象,而是力在还原他作为一个乱世之际普通士绅的面貌。其次,以日常生活为观察视角,对前人相对忽视的侯岐曾的消闲、医疗、社交、谣言传播均展开解读,继而对前人关注较多的追索危机与复明运动再作发覆。如果说日常生活是庸常重复的“小历史”,追索危机与复明运动则是关乎地方治理与王朝战争的“大历史”。但如果缺乏对前者的深入了解,对后者的宏观把握也容易失焦,这是本书将研究重点放在“日常生活”的主要用意。至于具体论述有何创见,还是要更多地交给读者来评判。
03
近年来日常生活史的潮流方兴未艾,您在《覆巢之下》中,是如何运用日常生活史范式的?
作为“范式”的日常生活史,既通过具有重复性的日常生活观察历史的深层结构,也旨在以日常生活为“接点”联通其他领域,还原历史的完整与鲜活。因此,《覆巢之下》将侯岐曾的日常生活归纳为消闲娱乐、疾病医疗、社交关系、政治活动等若干专题,依托《侯岐曾日记》中的生活细节,分别与相关专题的学术史对话,试图得出一些新见,亦旨在避免行文流于对生活状态的平面化叙述。比如,第三章通过侯岐曾与疾病的斗争,反思传统医疗文本对士大夫家庭医护活动的刻板描述,并探讨明清士人与慢性疾痛的纠葛;第四章由侯岐曾的社交关系,重新评估了晚明士绅社交网络“下移”的程度;第五章由侯家的追索危机,辨析士绅利用“非正式制度”抗衡国家机器的能力与限度;第六章借侯岐曾亲友圈误信谣言,对清初江南的社会心态试作一窥,等等。这些探讨不止是对相关研究议题的“旁敲侧击”,也尝试表达这样一种观念:日常生活不是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宏观研究“挑剩下”的细枝末节、鸡零狗碎,而是有助于反哺后者、更新既有认识的宝贵资源。
也需要指出,专题化的解读仅便于论述集中,不意味着要分解历史人物原本完整的日常生活。侯岐曾的家国创伤与恐惧破家的危机心态,是他从事日常活动共同的心理底色。对这一心理展开多层次的解读,可以说是贯穿全书各章的暗线,意在将不同生活史研究的专题予以弥合,尽量还原日常生活自身的完整性,也引导出侯岐曾的悲剧命运。读者所希望看到的,也应该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理的侯岐曾,而不是被社会科学器械拆解后的一堆研究碎片。
04
《覆巢之下》的写作主要依靠的材料是《侯岐曾日记》。对于日记类文本的可信度和利用价值,您如何看待?
史学研究素来重视日记,将其视为与档案、文书价值相若的一手史料。对人物研究来说,传主本人撰写的日记较多反映了自己的真实性情,也多能披露其他资料所不见的历史细节,具有无可取代的价值。明清之际的文人好写日记,但存留至今者应不超过二十部,此时的日记可以说是珍贵史料,都值得细致解读。但每部日记的性质未必相同,自我定位也可能有很大差异,这就影响了自身的可信度和利用价值。例如,明末有很多修身日记需要给同道中人传阅,用来“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期精进道德修为。还有一些日记写出来就是给别人看的,作者或为后世存史,或为打造自己的“人设”。因此,这些日记有多少可信度,就需要逐一辨明。另一些日记属于私密日记,写作时不打算给别人看,更不考虑在后世出版,比如晚清广东官员杜凤治的日记,可信度大概更高一些。至于本书依托的《侯岐曾日记》,性质应在公开日记与私密日记之间,且更偏向后者。侯岐曾在鼎革之前本来没有写日记的习惯,鼎革后写日记的初衷是给后人著史保存记录,打算日后公开,因此日记中还存留了不少他给亲友的信札和对社会的观察,大大丰富了史料的层次感。不过,文本一旦诞生,多少会超出作者的控制。侯岐曾主观上希望将日记作为后人著史的参考,又不禁将日记作为记录生活和情绪发泄的手段,不经意间透露了大量私密的生活细节。他对此也有察觉,希望日记务必从略,但没能实现。简言之,《侯岐曾日记》可谓“公私兼顾”,也反映出日记的公私之分并没有那么绝对,不同时代不同日记的可信度与价值也都是独特而相对的,需要根据研究选题分别研讨,未必能得出一个总括性的结论。
05
侯岐曾虽然不愿意亲身参与复明运动,却放任子弟与谋,您觉得他的这种心态是首鼠两端,还是心存侥幸?
侯岐曾为何对子侄参与复明运动采取“放任”态度,各方文献并未明言,只能据少量线索做一点推论。他曾感叹“倖事不可轻图,匪人不可误托”,多少反映出此举出自侥幸心理,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侯岐曾只能保证自己不参与复明运动,而对二子一侄(特别是丧父亡兄、复仇意志强烈的侄子侯玄瀞)的活动或许无力严格约束,只能寄希望于不要出事;第二是侯岐曾另有一些需求一时超过了对政治风险的顾忌。例如,侯玄瀞想向南明政权上疏陈情,对其父侯峒曾予以褒恤,侯岐曾起初虑及安全问题,并不同意,直到后来因事机“万不可待”才松口。侯岐曾为何转变态度,与他同样渴望兄长峒曾被南明朝廷褒恤应有很大关系。这是很多明遗民共同的心态,即希望为死于抗清战争的亲友向更高层次的政治权威“讨个说法”。诸南明政权覆灭后,遗民转而努力影响清朝官方的历史书写,最终促成了乾隆朝对前明“忠烈”的集体赠恤。
06
《覆巢之下》结尾侯岐曾的死,固然并非早有预谋的殉道,但其中到底有几分是一时冲动、几分是追索博弈导致的精神崩溃使然,抑或有更复杂的原因?
侯岐曾的死亡是多重因素促成的结果,既有个人一时冲动的成分,也源于较长时间形成的心理结构。目前可以掌握的情况有以下几点:
第一,侯岐曾在丁亥年的身心状况都出现了明显恶化,侯家所承受的追索危机愈演愈烈,自己的身体也没有好转,在《日记》中情绪低落、失控的时刻更多了,构成了他做出极端行动的基本心理背景。
第二,“松江之变”失败后,清朝又开始穷追“通海案”,侯岐曾深知子侄涉足其中,必难幸免,已经惶惶不安,束手无策。随后侯岐曾贸然决定藏匿陈子龙,不排除是灭顶之前的意气用事、放手一搏。
第三,由于侯玄瀞“通海”事发,侯氏的二度破家几乎不可避免,但侯岐曾的死亡却不是必然的。如果说侯岐曾藏匿陈子龙尚可归为血气所激,但他在被捕后的言行堪称主动求死,与他在丙丁之际表现出的强烈求生意志形成了剧烈转折。这就不能简单地将岐曾之死归结为一时冲动,需要考虑其人长时间形成的心理结构。
以上三个情况彼此应存在互动,但互动机制为何,各占几分比重,是一个重要却难以给出确凿答案的问题。因为历史学只能依托少量残缺史料,而无法像心理学一样,对研究对象的心理状况当面做出翔实而个性化的调查,只能是试作蠡测罢了。
07
《覆巢之下》中对医疗社会史、社会学、传播学等领域方法的运用,丰富了阐释的维度。您能否讲讲在历史学研究中运用跨学科方法的心得?
近年来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蔚成潮流,如医疗史、科技史、环境史等,均已形成十分成熟的研究模式。与之相比,《覆巢之下》大概谈不上是真正的跨学科研究,只能说是运用“拿来主义”,从其他学科中汲取营养,借用了一些概念和理论而已。日常生活的面向十分多样而复杂,《侯岐曾日记》所涉疾病医疗、社交网络、谣言传播等议题要想得到合理的阐释,都不是运用传统的乾嘉考证学所能解决的。社会科学既对这些议题早已形成了相关的概念界定与理论模式,例如谣言的定义、传播原因、传播模式等,历史学者不妨适当参考或挪用。借用到什么程度,需要以史料呈现的信息为衡量标准。历史学首先是史料之学,如果社科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手头掌握的史料,不妨暂以理论为基础,打造初步的研究框架。如果理论与史料存在明显抵触,自己的论述就必须从史料出发,大胆突破理论的设限,乃至进一步尝试理论的修订和重构。倘若人为剪裁或扭曲史料,使之匹配现有理论,无异于削足适履。史料与理论在学者头脑中的反复互动,或似铁匠锻铁,使研究愈锻愈坚,愈锻愈精,在自我调适的过程中不断走向体系化,向真正的跨学科迈进,这是我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
08
《覆巢之下》的主人公侯岐曾是您长期研究的人物,他所展现出的面相颇为复杂。您曾自述对嘉定侯氏怀有“温情和敬意”,那么您现在对侯岐曾这个人怀有一种怎么样的感情?
有关对侯岐曾怀有的感情,我在后记中写道:“对于笔下的嘉定侯氏,我自然怀有‘温情与敬意’,但这份情感仅仅出于职业要求,并不超过对明清之际其他普通人的同情。独研侯氏而暂不着眼他人,只是因为《侯岐曾日记》的性质特殊。”我从初次接触侯氏史料开始,这一立场始终没有变化。对研究对象怀有同情与理解,是希望在平等尊重对方人格的前提下,尽可能了解历史人物行动的真实逻辑,而不是秉持某种后见之明做出居高临下的粗暴判断。但除此之外,研究者更需要秉持高度的清醒和自律,自觉与历史人物保持一定距离。如果感到自己与古人已经“日久生情”乃至“心意相通”,往往需要提起警惕。学者对研究对象产生的特殊情感,如果导致对史料的裁剪和偏信,对研究可能是致命的。这些年来,我虽能更加真切地理解侯岐曾治生的不易,但也努力不生发出多余的情感,以免干扰《覆巢之下》的核心论断。也正因此,本书对侯尧封、侯震旸、侯峒曾、侯岐曾等侯氏男性尊长以及侯家的兴盛之路,均提出了一些与传统观点有异的观察。
09
您在博士阶段的研究聚焦于江南抗清运动,那么,回过头来,您是怎么看待侯岐曾这个人在明末清初的江南社会和抗清运动中的位置的?
对《侯岐曾日记》的研究,让我对明清之际公私文献之间的张力形成了直观认识,随之产生了重新解读江南抗清运动这一宏大事件的最初灵感。但在博论草成后回头来看,侯岐曾在明末清初江南社会与抗清运动中仍不算重要人物,在可预见的未来大概也不会变得更重要。侯岐曾平生引以为豪的选文事业,辐射范围仍主要限于苏松一带,他在江南抗清运动中也仅仅担任了前明江南副总兵吴志葵的幕僚,属于被边缘化的人物。但是,侯岐曾在当今的研究价值并不取决于他的历史地位,因为《侯岐曾日记》的丰富细腻已让我们窥见了许多有关明清之际不为人知的历史面向,也有助于我们调整对时代整体的认识。从“小人物”发现的“大历史”,不仅震撼人心,也可启迪新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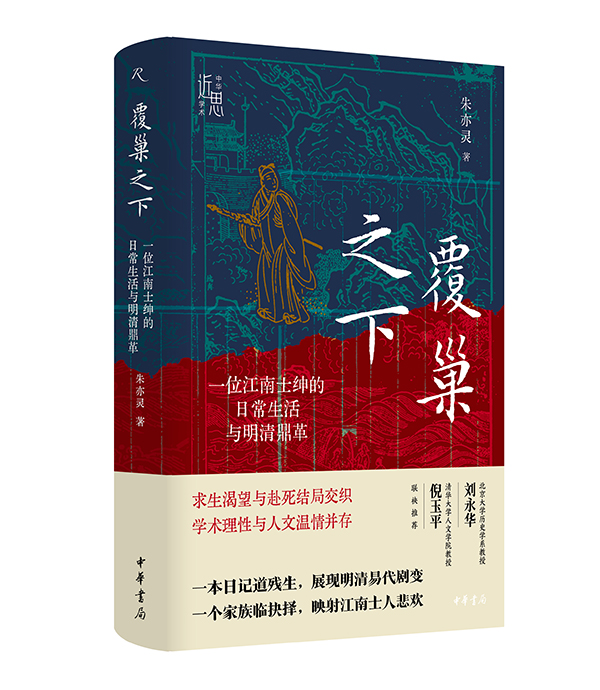

顺治三年春,在兄长因抗清罹难后,死里逃生的嘉定士绅侯岐曾始以“半生道人”之名作日记,“以备后人稽考”。透过日记观察侯岐曾“奉母保孤”的“遗民”生活,诗书游戏只是短暂的慰藉,与疟疾的抗争亦无成效。清廷的打击步步紧逼,侯岐曾竭力调度社交网络,却也无力改变大局。虽然心怀故国,他却对复明运动持谨慎态度,并无殉死决心。但最终精神趋于崩溃的侯岐曾还是卷入“松江之变”,家破人亡,成为明清易代史上又一幕悲剧。
本书引入日常生活史的视角,较完整地还原了晚明士绅真实的生命图像,展现了侯岐曾的求生渴望与赴死结局之间的张力,在学术理性之外亦饱含人文温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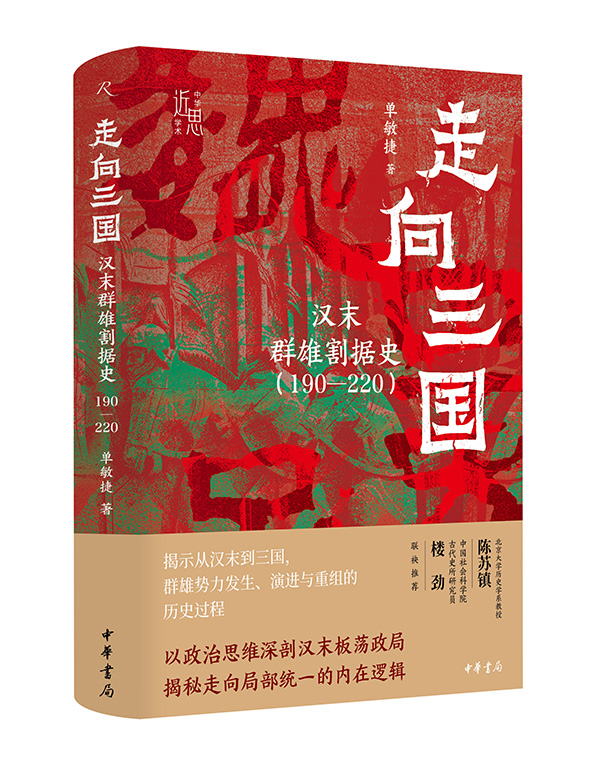
东汉中央朝廷崩溃后,各地势力在碎片化后重新整合,群雄并起,东汉名存实亡。本书聚焦于东汉末年直到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这三十余年间,群雄势力发生、演进与重组的历史过程,尝试通过对基本史事的重新梳理,分析各主要军阀集团的内部矛盾以及军阀之间的利益纠葛,并从秦汉大一统制度遗产的角度,来探讨秦汉旧制是怎样抑制了汉末“破碎性分裂”的延续,并将历史发展的轨迹重新引导向局部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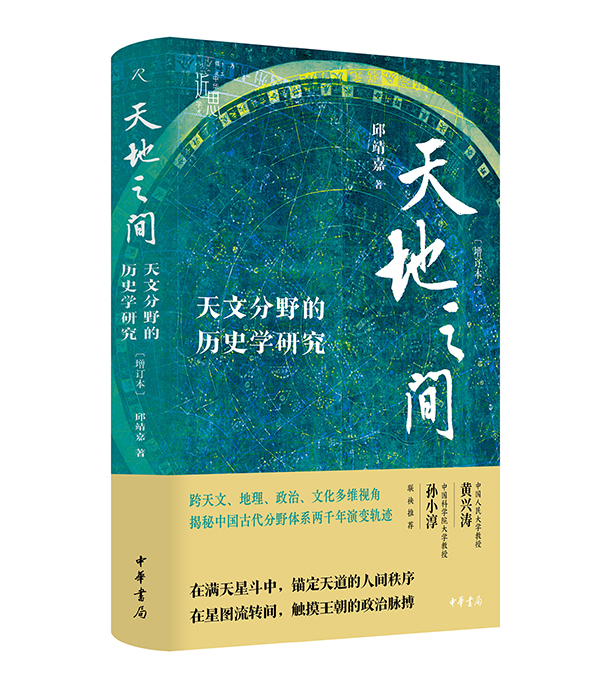


www.zhbc.com.cn zhbc@zhbc.com.cn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邮编: 10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