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文化教师素养读本
作者:楼宇烈,傅首清主编
定价:¥58.00
中华文化教师素养读本
作者:楼宇烈,傅首清主编
定价:¥58.00
-
 辽史--全五册(精)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
作者:脱脱著 刘浦江整理
定价:¥280.00
辽史--全五册(精)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
作者:脱脱著 刘浦江整理
定价:¥280.00
-
 南明史(精装本)
作者:钱海岳撰
定价:¥980.00
南明史(精装本)
作者:钱海岳撰
定价:¥980.00
-
 宋书(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平装本)
作者:(梁)沈约 撰
定价:¥360.00
宋书(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平装本)
作者:(梁)沈约 撰
定价:¥360.00
-
 魏书—(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精装)
作者:魏收著 何德章,冻国栋修订
定价:¥510.00
魏书—(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精装)
作者:魏收著 何德章,冻国栋修订
定价:¥510.00
-
 史记--全五册(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精
作者:[汉]司马迁撰 陈曦、王珏、王晓东、周旻译
定价:¥298.00
史记--全五册(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精
作者:[汉]司马迁撰 陈曦、王珏、王晓东、周旻译
定价:¥298.00
-
 全元词(全三册)--中国古典文学总集
作者:杨镰主编
定价:¥298.00
全元词(全三册)--中国古典文学总集
作者:杨镰主编
定价:¥298.00
-
 金史(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精)
作者:[元]脱脱等撰
定价:¥540.00
金史(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精)
作者:[元]脱脱等撰
定价:¥540.00
-
邹鲁文化研究 作者:贾庆超等 定价:¥0.00
-
 明实录 附校勘记(183册)布面精装
作者: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 黄彰健校勘
定价:¥45000.00
明实录 附校勘记(183册)布面精装
作者: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 黄彰健校勘
定价:¥45000.00
“半部《论语》治天下”,想不起自己在什么年龄段听到这句话的,那时感觉好酷耶。觉得说此话的一定是当了大官的读书人,遍观百家,总结自己辅佐皇帝治国的经验,认为《论语》最好用。后来知道这话是赵普说的,心想对头,赵普是帮着赵匡胤打天下的哥们,赵氏兄弟俩都请他当宰相,料理赵家江山,满肚子学问正好派上用场。
不过,什么事都经不起深究,一追究就大感意外:原来这赵普不怎么读书。《宋史·赵普传》记载,“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也就是说赵普年少时就有实践能力和行政工作经验,但是不怎么读书,只是当了宰相之后,赵匡胤劝他多读点书,不然,满朝文武都是学而优则仕上来的,一个当宰相的怎么与人对话。
赵普晚年倒是认真读书了,不是博览群书,而是少而精、学用结合。据说每临大事,他都要闭户开箧读书,第二天上朝断事“处决如流”,效率极高。别人都不清楚他书箧里装的是什么书,以为是类似黄石公授予张良的圯桥秘籍,直到他去世,家人开箧取书,才知晓那是《论语》二十卷。

其实要论读书,宋朝的皇室肯定是历代皇室中最用功的。他们的理念是以文治国,文化兴邦。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之?不说别人,以宋太宗赵光义为例,他不仅令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大型类书,而且自己带头表率,每日读三卷,一年读毕《太平御览》一千卷,这功夫、这毅力实在叫人钦佩。所以当他和赵普说起读书,赵普连忙坦承:“臣实不知书,但能读《论语》。”赵普又补充道,自己助太祖定天下才用了半部《论语》,剩下的一半可以辅佐陛下。于是传为佳话。
我怀疑,这用半部、剩半部之说,是后人演义的结果。因为赵匡胤、赵光义和赵普当初共创天下,互相知根知底。赵普的受重用是因为他处理事情的机敏果断,谋划得当的本领。据说赵普退朝回家后基本不换便衣,因为赵匡胤时不时会光顾他家。某日大雪,赵普觉得今晚皇上不会来了,可以放心躺平。不料叩门声响起,皇上驾到,并且还约了当时任晋王的赵光义,于是三人在厅堂中央铺了厚厚的垫子,一边吃着烧烤,一边讨论军国大事,如何扫平天下、如何缓取太原等等;赵普的妻子在一旁给他们斟酒,赵匡胤称呼普妻为嫂子,气氛很是融洽。什么用半部《论语》治天下,跟别人吹吹可以,赵普怎么着也不可能对当年的哥们——今天的圣上这样吹嘘吧。
想来演义和传播“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有两类人:一是儒家后生,认为孔圣人的思想遥遥领先;二是有丰富行政技术经验的官僚,瞧不上那些死读书考上来的儒生,认为书不必读太多,读多了反而弄坏了脑筋,关键在于如何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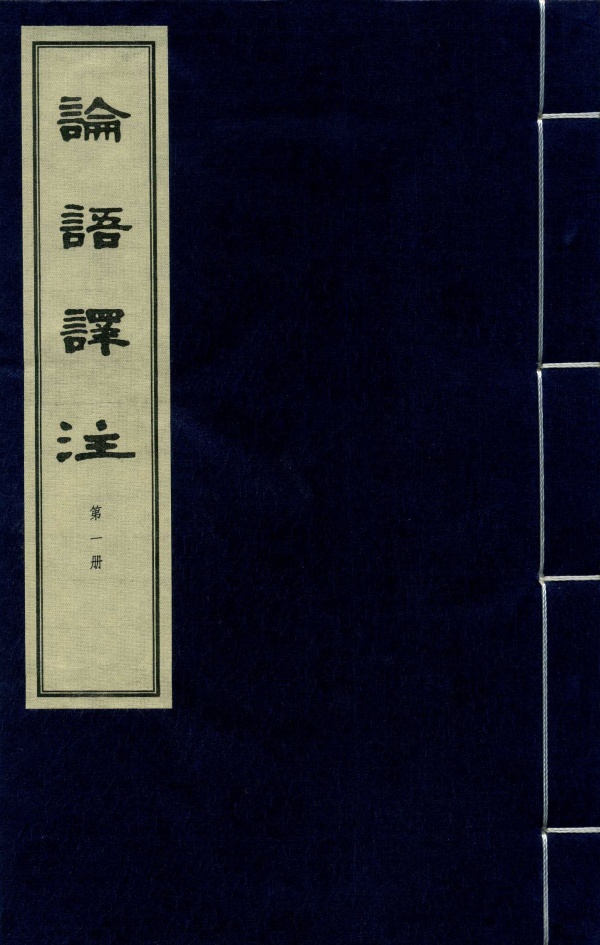
《论语》二十篇总字数有一万五千多,以赵普机敏聪慧的头脑不用多少天就背得滚瓜烂熟,何至于一个人躲在屋里天天翻看。赵普做出这番姿态,也许只是为了表示自己的所有想法都出于先贤,其来有自。当然更有可能他并不是闭户读书,而是在被窝里呼呼大睡,养精蓄锐,不让他人打扰。年纪大了,早朝回来要补补觉正常,但又不能让家里下人知道他大白天睡觉。熟读《论语》的人都晓得,宰予就因为昼寝,被孔子斥责为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赵普不愿给别人留下昼寝的坏印象,仅此而已。
赵普当然是奇才,许多人的信息来源是书本,他属于见微知著的那种人,各种渠道都是他的信息来源,包括日常的行政工作、各种朝廷的报表和奏折等。有一次,赵匡胤拿出一张幽州的地图来,他一看就判定是曹翰所作。赵匡胤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回答:“方今将帅材谋,无出于翰。”赵普接下来的意思是如果皇上想派曹翰带兵取幽州,肯定手到擒来,但是一旦拿下,派谁来接替曹翰是个大问题,所以事先要掂量掂量。类似这类重大事情,宋太祖都要征求他的意见,认为赵普靠谱。
读书和处理朝政遵循的是不同的逻辑,后者须洞明世事,练达人情,这些赵普都具备,当然还有对人主心思的了然。不过赵普并非圆滑之人,他也往往直谏,有时弄得皇上很不高兴。例如当臣子的立功受赏应该升职,可是赵匡胤偏偏看不上某人,不予升官,赵普坚持要赏,惹得太祖大怒,说:朕就是不给升迁,卿又如何?于是引出赵普一番宏论:“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岂得以喜怒专之。”太祖更生气了,拂袖而去,赵普则紧追不舍,最后还是听从了赵普的意见。上千年的皇权社会,人人皆知“普天之下,莫非皇土”,但是赵普说出“天下之刑赏”和“陛下之刑赏”的区别,是很了不起的,他划出了制度和皇上个人权力的各自范围。这个不怎么读书的赵普敏锐地洞悉了政权能够良性运作的某些基本条件和规则,甚至是体现了某些思想的萌芽。不由人不联想到德国学者坎托罗维奇的著作《国王的两个身体:中世纪政治神学研究》。所谓两个身体,一个是指国王的自然肉体,另一个是国王所象征的政治权力身体。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就是终止波旁王朝的统治。其实天下也有两个,一个是天下之天下,一个是陛下之天下。
当然,赵普毕竟和赵家兄弟俩熟悉,许多事情尽管意见相左,往往还有转圜馀地。这和另一位以犯颜直谏著称的魏徵有所不同。魏徵虽然位极人臣,但是开始一直没有跟对人,先是加入瓦岗军李密一伙,后来又投靠窦建德,最后归顺李唐王朝,但是却到了李建成的门下任太子洗马。魏徵因为文才出众,所以颇受李密和李建成的赏识,但是他的一些建议却不被重视。例如他曾经提醒李建成提防李世民,但是李建成似乎没有太在意。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指控魏徵离间他们兄弟,他却回应,如果太子早听了我的,就不会有今天这个局面。他的直率倒也没有激怒李世民,大概历史上有齐桓公招纳管仲这个先例,李世民就收留了魏徵,令他当谏议大夫,这也表明魏徵在他心目中的位置:称职的言官。史书记载魏徵“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这也是李世民所看重的品格。从那时起到后来官越做越大,官职头衔越来越多,魏徵一直坚持初衷,给唐太宗前后上奏折疏言二百多份,这可能还不算面谏的内容。唐太宗无论再怎么从善如流,也有脸上挂不住的时候。一日李世民退朝回宫,恶狠狠地说,要杀了这“田舍汉”,长孙皇后问是谁忤逆陛下,当然,除了魏徵没别人,李世民愤愤说道:“每廷争辱我,使我常不自得。”不料长孙皇后一听,似早有准备地说道:主圣臣忠,今陛下圣明,故魏徵得直言,臣妾也能安享在后宫,乃可贺可喜。长孙皇后是属于深明大义,命里相夫的那种角色,不过这里也透出当时宫廷的某种氛围,觉得有人提意见,总是强于一片阿谀之声。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贞观之治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

和赵普数十年只读一部《论语》相比,魏徵可谓博通群书,满腹经纶,这似说明要当好一个宰相,和读书的多寡没有直接关系,既不成正比,也不成反比。许多人知晓魏徵是因为收在《古文观止》的名篇《谏太宗十思疏》,更让人服气的是魏徵主持了《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的编写工作,盖朝廷命他“总加撰定”,正所谓盛世修史。魏徵本人则主编了《隋书》,据说为其中许多篇什撰写了序和论,特别是为《隋书·文学传》写的序,尤为脍炙人口:“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即便别的成就都不算,魏徵妥妥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文学批评家。
魏徵为人刚正,处事谨严,不过难免也有膨胀的时候。他在仆射任上,某日在衙所打瞌睡,听到窗户外有两人在争论,甲说,吾等官职的升迁是由屋中那位老翁说了算。乙则说,一切都是由上天安排。此时半生坎坷的魏徵正处于人生的高光时刻,他毫不迟疑就拟了便笺,命甲送到侍郎处,内写:给此人安排个好职位。不料甲刚出门,就犯了心痛病,让乙送去。第二天魏徵发现情形与意料中的刚好相反,叹息道:“官职禄料由天者,盖不虚也。”
赵普也有春风得意的时刻,他会将赵匡胤尚未发迹时的作为(也包括某些糗事)拿来与皇上打趣,宋太祖倒是豁达,说人在微尘时,看上去都差不多,如果那时就能一眼识别天子和宰相,人人都会去巴结。从此赵普就再也不提往事。
其实读书少,不等于不学习。赵普只是不光盯着儒家的那几部经典而已。再说了,那些篡位夺权的谋略很少见诸笔墨,全凭一己潜心揣摩。从他给宋太宗的几次上书中,亦可看出赵普阅历既广,又通晓史书。他劝赵光义,在师出无名的情况下不要劳师远征,这样往往“所得者少,所丧者多”。又说:“兵者凶器,深戒于不虞。”他提醒皇上,前书有“兵久生变”之言,深为可虑。他知晓宋太宗一心想收复北边的幽蓟地区,但是眼下条件不具备,就不要执念于此,称:“臣又闻上古圣人,心无固必,事不凝滞,理贵变通。”据说“欲攘外者,必先安内”的说法就是在赵普给太宗的上书中最早出现的(笔者没有找到出处,且存疑。但是这种理念应该包含在其中了)。赵普在宋太宗当国期间能两次拜相,既是缘于他的识见和判断,也是窥察圣心,迎合上意的结果,这些都不是书本能教得会的。
前文说过,赵普不太可能当着赵光义的面吹嘘自己“半部《论语》治天下”,但是也不排除是赵普在某种语境下的自嘲。既然从皇上到大臣,个个都雅好文艺,那赵普也得表示下。不过这自嘲里也透着自信,自己即便只读一部《论语》,也绰绰有馀,还剩下半部没用上,哪像你们这帮书呆子,皓首穷经仍旧不通世务。
赵光义尽管是东征西讨,但是在一些文献中记载他“尤留意斯文”,“常以经籍自娱”,整个朝廷的风气是崇文抑武。上有所好,下必甚矣,到仁宗一朝,情况更甚,因为自澶渊之盟后,宋朝太平了几十年,朝野一片祥和气象。在和平年代,舞枪弄棒不如吟诗作赋来得风雅,其时附庸风雅也是一种潮流。庆历年间,河北水患,仁宗忧形于色,正好地方上派员来汇报,仁宗急问水灾情形如何,答曰:“怀山襄陵。”(洪水滔天的意思,语出《尚书·尧典》)又问当地百姓生活情况怎样,答曰:“如丧考妣。”弄得仁宗很腻歪。待到来人退下,仁宗说,以后武官上殿奏事,有话直说,不得文绉绉拽词。
宋代是从五代十国群雄割据的纷乱中杀出,为了改变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局面,赵匡胤祭出“杯酒释兵权”高招,解除了一众高级将领的军权,接着又收回了地方节度使的权力。以文治国的国策又提高了文官的地位,所以有宋一代基本是文强武弱的格局,据说这里也有赵普的主意。赵匡胤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计,曾问询于赵普。赵普说了八个字——“制其钱谷,收其精兵”,意思是无论财权还是军权统统都要收上来。他认为唐代后期正是因为藩镇太强,君弱臣强,才导致数十年间兵革不息、苍生涂地的乱局。君臣一拍即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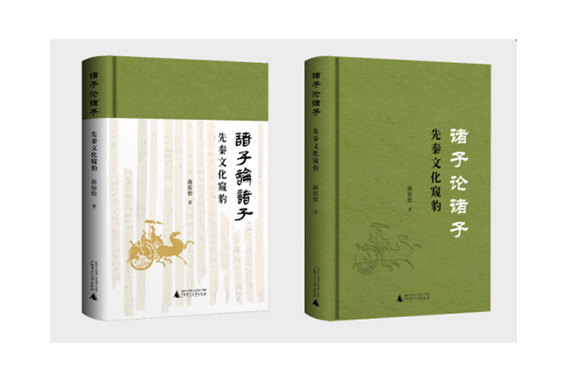
不过许多事情都有两面性。一方面,宋代的文化可谓星汉灿烂,用陈寅恪的话来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另一方面,却是武备不足,边患屡生。中央政府高度集权,削弱了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一到打仗,弄到皇帝都要御驾亲征的地步,事情总不太妙。因此许多民间戏曲里只能弄一帮杨门女将来抗辽,还眉飞色舞编派出佘太君百岁挂帅的名堂。北宋亡于金,南宋毁于蒙古铁蹄,分析起来原因杂多,每一条都有些道理,但是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打不过,为什么打不过?上无优秀的将帅,下无为自身权利而战的组织起来的个体。国运如此,文曲星闪烁、武曲星隐晦,《论语》更是帮不上忙的。(本文为作者原稿,与刊出的文章略有不同)

www.zhbc.com.cn zhbc@zhbc.com.cn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邮编: 1000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