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历史最有趣的时候,就是突然发现:
原来同一件事,在不同史家眼里,竟是两番天地。
而中国历史上最精彩的一场隔空辩论,大概要数“史学两司马”——司马迁和司马光了。
公元前227年,易水河畔,荆轲踏上了刺秦的不归路。

司马迁写完《刺客列传》,意犹未尽,专门加了一段“太史公曰”:
“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听这语气,司马迁在赞叹。他看见的不是“成功或失败”,而是“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在他眼里,荆轲们的刺杀行动,关乎个人气节,关乎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成不成另说,那股“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就值得青史留名。
但一千年后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写到同一件事时,完全是另一番口气:
“荆轲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
“不亦愚乎”,这不是惋惜,是批评。在司马光看来,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私恩,置整个燕国于险境,这是把个人恩怨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更何况,想靠一把匕首改变天下大势,“不亦愚乎”四个字,已经是很克制的评价了。
读到这里,可能会愣一下:同一个荆轲,怎么在司马迁那儿是义士,到司马光这儿就成“愚夫”了?
不只是荆轲,他们对很多人的评价都不一样


司马迁像 司马光像
如果以为这只是个例,那就错了。这两位司马先生,几乎在所有重大历史评价上,都站在河的两岸。
比如商鞅。
司马迁说商鞅“天资刻薄人也”。他写商鞅在秦国推行新法,百姓一开始抱怨,后来受益了又赞扬。但司马迁的笔锋一转,点出要害:
“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你最后在秦国落得个坏名声,不是没原因的。
这话说得含蓄,但懂的人都懂。司马迁看见的是商鞅变法背后的“人”。法令严苛,不近人情,最后作法自毙,被自己立的法逼死。
司马光呢?他承认商鞅“其政令必行,法不阿贵”,秦国确实因此富强。但他话锋一转:“弃仁义而尚权诈。”这才是根本问题。在司马光看来,商鞅最大的错,不是性格刻薄,而是把治国之道引向了歧途:重权术而轻仁义。
你看,司马迁批评的是“人”,司马光批评的是“道”。
再看项羽。
司马迁给项羽写的不是“列传”,而是“本纪”,和帝王同等级别。他在《项羽本纪》最后感叹:“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
这段话得细品。表面在批评项羽“自矜功伐”“不师古”,但字里行间是惋惜,一个从底层崛起、叱咤风云的英雄,怎么就败了呢?司马迁写出了项羽的悲剧性,那种“时不利兮骓不逝”的宿命感。
司马光的评论就冷静得多:“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失天下心矣。匹夫之勇而不能任贤,妇人之仁而吝于封爵;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战之罪’,岂不谬哉!”
他把项羽的失败,归结为清晰的政治逻辑:失民心者失天下。什么性格悲剧、什么命运不公,在司马光这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项羽的统治方式违背了基本的政治原则。
他们为什么总是“吵”起来?
读到这里,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这两位司马先生,根本是在用两套完全不同的尺子,量同一段历史。
司马迁的尺子上刻的是“人”。
他经历过李陵之祸,受过宫刑,对个人在庞大体制下的渺小与挣扎,有切肤之痛。所以他写历史,是在写“人”的故事,写他们的选择、他们的困境、他们的光芒与阴影。在司马迁眼里,历史是无数个体生命的悲欢离合。
所以他会为刺客立传,会替游侠说话,会在《货殖列传》里肯定商人的价值。在他的历史观里,那些不被正统认可的“小人物”,也有权在史册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司马光的尺子上刻的是“制”。
他生活在北宋中期,经历过王安石变法的激烈斗争,亲眼看到国家政策如何影响千万人的生活。他编《资治通鉴》,是为了“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给皇帝、给治国者看的历史教科书。
在司马光看来,历史的首要意义是提供政治智慧。什么该写、怎么写,都要服务于这个目的。所以《资治通鉴》里没有“游侠列传”,因为游侠破坏法治秩序;对荆轲的评价也更看重政治后果,而非个人气节。
最有意思的是韩信
最能看出两人差异的,莫过于对韩信之死的评价。
司马迁写韩信,笔法太妙了。他明面上说:“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乍看是在批评韩信不知进退,咎由自取。但仔细读,前面加了个“假令”(假如),最后用反问语气“不亦宜乎”。这哪是真心话?这分明是话里有话。
司马迁真正想说的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他写蒯通劝韩信自立的那段长对话,写钟离昧逃亡时韩信的处境,都是在为这个军事天才的宿命作注,不是韩信非要反,是走到那一步,已经没有别的路了。
司马光的分析就直白得多:“夫乘时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
他点破了窗户纸——刘邦难道不知道韩信没谋反吗?知道,但还是要除掉他。为什么?因为韩信“功高震主”,因为“功臣恃功骄恣”威胁皇权。这不是个人恩怨,是政治逻辑。
一个在为生命鸣不平,一个在为秩序找依据。两人都没错,只是看问题的层面不同。
我们该听谁的?
读史读到这个份上,可能要问了:那到底谁说得对?
其实,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判断题。
司马迁和司马光,各自抓住了历史真相的一面。
司马迁让我们看见历史的温度。在他笔下,那些两千年前的人物不是冰冷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会犯错也会发光的人。他教会我们同情地理解,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每个人都在做自己认为对的选择。
司马光让我们看见历史的规律。他梳理出一套政治运行的逻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治国需要法度,也需要仁义。他教会我们跳出具体的人和事,去看背后的结构性问题。
我们今天读历史,最好的状态大概就是:
读《史记》时,感受那些鲜活生命的悲喜;读《通鉴》时,思考制度与文化的兴衰。司马迁给我们一颗理解个体的心,司马光给我们一双洞察大势的眼。
历史从来不是单一的叙述。就像一条大河,司马迁在记录每一朵浪花的姿态,司马光在描摹河道的走向。浪花与河道,共同构成这条河流的全貌。
说到这,又回到之前朋友们经常问到的问题:
《史记》和《资治通鉴》, 先读哪个?
我们的建议是:如果一定要分先后,不妨先读《史记》;若有足够的时间,则强烈推荐两者都读。
原来同一件事,在不同史家眼里,竟是两番天地。
而中国历史上最精彩的一场隔空辩论,大概要数“史学两司马”——司马迁和司马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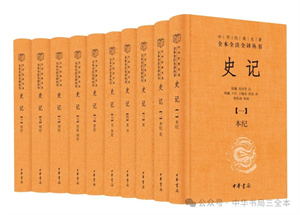

史记(全十册)精--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资治通鉴(精装全本全译十八册)--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
一场刺杀,两种评语公元前227年,易水河畔,荆轲踏上了刺秦的不归路。

荆轲刺秦王画像石拓片
这段故事我们都熟。但大家可能没注意过,司马迁和司马光是怎么评价这件事的。司马迁写完《刺客列传》,意犹未尽,专门加了一段“太史公曰”:
“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听这语气,司马迁在赞叹。他看见的不是“成功或失败”,而是“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在他眼里,荆轲们的刺杀行动,关乎个人气节,关乎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成不成另说,那股“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就值得青史留名。
但一千年后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写到同一件事时,完全是另一番口气:
“荆轲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
“不亦愚乎”,这不是惋惜,是批评。在司马光看来,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私恩,置整个燕国于险境,这是把个人恩怨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更何况,想靠一把匕首改变天下大势,“不亦愚乎”四个字,已经是很克制的评价了。
读到这里,可能会愣一下:同一个荆轲,怎么在司马迁那儿是义士,到司马光这儿就成“愚夫”了?
不只是荆轲,他们对很多人的评价都不一样


如果以为这只是个例,那就错了。这两位司马先生,几乎在所有重大历史评价上,都站在河的两岸。
比如商鞅。
司马迁说商鞅“天资刻薄人也”。他写商鞅在秦国推行新法,百姓一开始抱怨,后来受益了又赞扬。但司马迁的笔锋一转,点出要害:
“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你最后在秦国落得个坏名声,不是没原因的。
这话说得含蓄,但懂的人都懂。司马迁看见的是商鞅变法背后的“人”。法令严苛,不近人情,最后作法自毙,被自己立的法逼死。
司马光呢?他承认商鞅“其政令必行,法不阿贵”,秦国确实因此富强。但他话锋一转:“弃仁义而尚权诈。”这才是根本问题。在司马光看来,商鞅最大的错,不是性格刻薄,而是把治国之道引向了歧途:重权术而轻仁义。
你看,司马迁批评的是“人”,司马光批评的是“道”。
再看项羽。
司马迁给项羽写的不是“列传”,而是“本纪”,和帝王同等级别。他在《项羽本纪》最后感叹:“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
这段话得细品。表面在批评项羽“自矜功伐”“不师古”,但字里行间是惋惜,一个从底层崛起、叱咤风云的英雄,怎么就败了呢?司马迁写出了项羽的悲剧性,那种“时不利兮骓不逝”的宿命感。
司马光的评论就冷静得多:“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失天下心矣。匹夫之勇而不能任贤,妇人之仁而吝于封爵;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战之罪’,岂不谬哉!”
他把项羽的失败,归结为清晰的政治逻辑:失民心者失天下。什么性格悲剧、什么命运不公,在司马光这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项羽的统治方式违背了基本的政治原则。
他们为什么总是“吵”起来?
读到这里,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这两位司马先生,根本是在用两套完全不同的尺子,量同一段历史。
司马迁的尺子上刻的是“人”。
他经历过李陵之祸,受过宫刑,对个人在庞大体制下的渺小与挣扎,有切肤之痛。所以他写历史,是在写“人”的故事,写他们的选择、他们的困境、他们的光芒与阴影。在司马迁眼里,历史是无数个体生命的悲欢离合。
所以他会为刺客立传,会替游侠说话,会在《货殖列传》里肯定商人的价值。在他的历史观里,那些不被正统认可的“小人物”,也有权在史册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司马光的尺子上刻的是“制”。
他生活在北宋中期,经历过王安石变法的激烈斗争,亲眼看到国家政策如何影响千万人的生活。他编《资治通鉴》,是为了“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给皇帝、给治国者看的历史教科书。
在司马光看来,历史的首要意义是提供政治智慧。什么该写、怎么写,都要服务于这个目的。所以《资治通鉴》里没有“游侠列传”,因为游侠破坏法治秩序;对荆轲的评价也更看重政治后果,而非个人气节。
最有意思的是韩信
最能看出两人差异的,莫过于对韩信之死的评价。
司马迁写韩信,笔法太妙了。他明面上说:“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乍看是在批评韩信不知进退,咎由自取。但仔细读,前面加了个“假令”(假如),最后用反问语气“不亦宜乎”。这哪是真心话?这分明是话里有话。
司马迁真正想说的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他写蒯通劝韩信自立的那段长对话,写钟离昧逃亡时韩信的处境,都是在为这个军事天才的宿命作注,不是韩信非要反,是走到那一步,已经没有别的路了。
司马光的分析就直白得多:“夫乘时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
他点破了窗户纸——刘邦难道不知道韩信没谋反吗?知道,但还是要除掉他。为什么?因为韩信“功高震主”,因为“功臣恃功骄恣”威胁皇权。这不是个人恩怨,是政治逻辑。
一个在为生命鸣不平,一个在为秩序找依据。两人都没错,只是看问题的层面不同。
我们该听谁的?
读史读到这个份上,可能要问了:那到底谁说得对?
其实,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判断题。
司马迁和司马光,各自抓住了历史真相的一面。
司马迁让我们看见历史的温度。在他笔下,那些两千年前的人物不是冰冷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会犯错也会发光的人。他教会我们同情地理解,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每个人都在做自己认为对的选择。
司马光让我们看见历史的规律。他梳理出一套政治运行的逻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治国需要法度,也需要仁义。他教会我们跳出具体的人和事,去看背后的结构性问题。
我们今天读历史,最好的状态大概就是:
读《史记》时,感受那些鲜活生命的悲喜;读《通鉴》时,思考制度与文化的兴衰。司马迁给我们一颗理解个体的心,司马光给我们一双洞察大势的眼。
历史从来不是单一的叙述。就像一条大河,司马迁在记录每一朵浪花的姿态,司马光在描摹河道的走向。浪花与河道,共同构成这条河流的全貌。
说到这,又回到之前朋友们经常问到的问题:
《史记》和《资治通鉴》, 先读哪个?
我们的建议是:如果一定要分先后,不妨先读《史记》;若有足够的时间,则强烈推荐两者都读。
(编辑:知予 复审: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