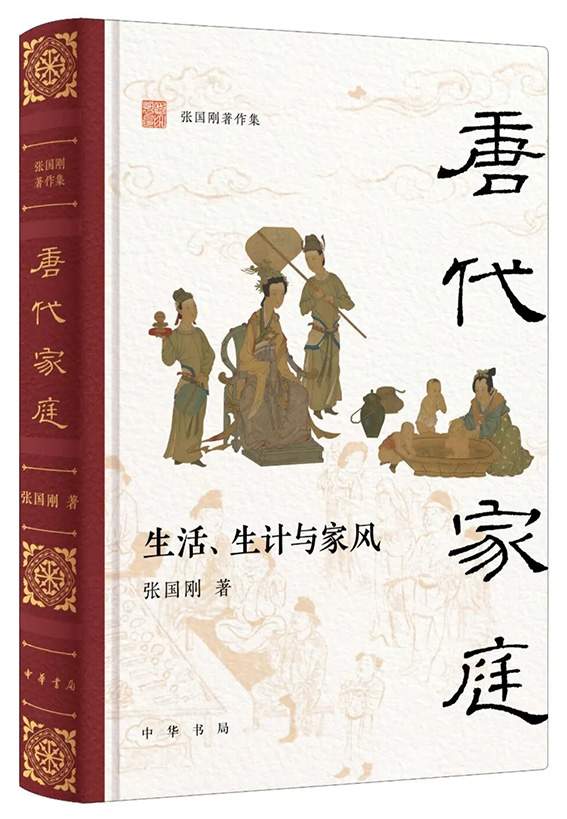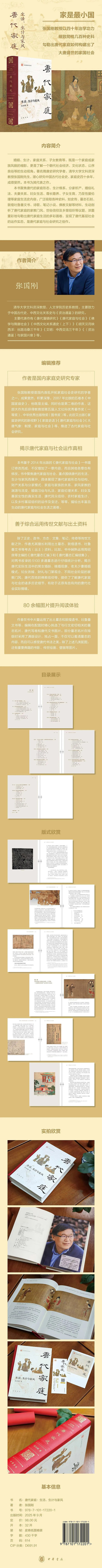根据马端临的说法,汉代举孝廉要求有实际的德行,要求行为上符合儒家礼法文化的准则,但是实际上很难做到,于是朝廷就采取了考试儒家文献的办法。东汉不仅把儒经的研修与示人好恶、改敝就善的个人修身相结合,而且将儒经的研习与个人的政治前途联系在一起,亦即把经学考试与做官直接挂钩。如东汉顺帝时期,“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试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 。这个措施大约出自左雄的建议:“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魏明帝太和二年(228)六月,“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察举制度增加了考试经书的环节。
把经术的研习与入仕做官挂钩的做法在魏晋时期更为明显。有人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尽管也有人提出“举孝廉,本以德行,不复限以试经”,但马上遭到华歆的反驳:“丧乱以来,六籍堕废,当务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经盛衰。今听孝廉不以经试,恐学业遂从此而废。”《全魏文》“体论·臣第二”还收入杜恕的《体论》,把德行修身、经术、才能与入仕联系在一起。

取士的要求是“经明行修”,虽然未必经明就行修,似是经不明则行是必不能修的。为什么呢?因为所谓“行修”就是要按照儒经的规矩做人。儒家的道德要求和人伦规范并不是先天就会做的。儒家的许多规矩需要有学习的过程。通过明经考试,就是为了使人们懂得规矩之所在,并在行动中加以实践。东汉迄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家包括玄学家极力提倡要把实践儒家伦理与入仕做官联系在一起。夏侯玄就说:“夫孝行著于家门,岂不忠恪于在官乎?仁恕称于九族,岂不达于为政乎?义断行于乡党,岂不堪于事任乎?三者之类,取于中正,虽不处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九品中正制度更是为把儒学世家转变成仕宦世家作出制度上的保证。
儒学世家转变为仕宦世家是汉魏以来历史发展的一个趋势。东汉时期出现了世代公卿、世代传经而又世出名士的家族。他们愈益表现出鲜明的文化色彩。“士”与“族”的结合,对于官僚选拔制度是一个挑战,而且对于文化的传承也是一个新的契机。陈寅恪说:“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也就是说,世代高门只是士族形成的外在政治标志,礼法及家学的传承乃是士族的内在文化特征。城南杜氏家族有杜预,清河和博陵崔氏家族有崔骃、崔寔,范阳卢氏家族有卢植,都是著名的学者或经学大师。钱穆先生还说:魏晋南北朝的士族希望门第中人,一则希望其有孝友的内行,一则希望其有经籍文史之学业。前者表现为家风,后者表现为家学。尤其精到的是,钱先生明确指出,“当时极重家教门风,孝弟妇德,皆从两汉儒学传来”,认为儒家经学与家庭伦理有直接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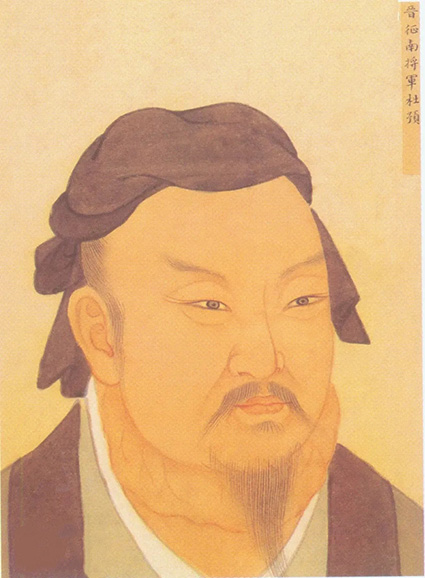
对此,《宋书》卷五五《傅隆传》提出了强有力的证明:“诸儒各为章句之说,既明不独达,所见不同,或师资相传,共枝别干。故闻人、二戴,俱事后苍,俄已分异;卢植、郑玄,偕学马融,人各名家。”对于文本解释的不同已经涉及对于国家和世俗礼仪设计上的差异了,后文接着说:“又后之学者,未逮曩时,而问难星繁,充斥兼两,摛文列锦,焕烂可观。然而五服之本或差,哀敬之制舛杂,国典未一于四海,家法参驳于缙绅,诚宜考详远虑,以定皇代之盛礼者也。伏惟陛下钦明玄圣,同规唐、虞,畴咨四岳,兴言《三礼》,而伯夷未登,微巨窃位,所以大惧负乘,形神交恶者,无忘夙夜矣。”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儒家章句之典礼如何向国家和民间(缙绅)应该遵行的礼法转化。如果说“国典未一于四海”表明当时全国范围内国家法定的典礼仪式尚未统一的话,那么“家法参驳于缙绅”则表明,士族门阀之家以其独特的家法和规约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作者在这里主要强调的是分歧来自对于经典的理解和遵从上的差异。比如,在婚礼及丧服制度上,对于经传理解的不同“家法”(章句之学的家法)就会影响到实际的士族之家采用不同的礼仪形式并形成各自不同的“家法”(伦理仪范的家法)。
儒家经典内化为士族的家法门风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曾经有很大的争议,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关于“名教”与“自然”的讨论。究竟是去名教而任自然,还是相反?魏晋时代风流名士的种种不合礼法的言行可以看作是儒家伦理向私家空间不断推进中遇到的反抗。最后的结果其实是名教战胜了自然,士族之家的礼法文化最终得以形成。江南的梁武帝不仅是以崇尚佛教知名,而且还以制礼作乐见称于世。士族的风貌产生重大变化,魏晋时期放荡的名士风气在南朝后期开始改变。当儒家伦理逐渐推进到私人领域的时候,魏晋风流终于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