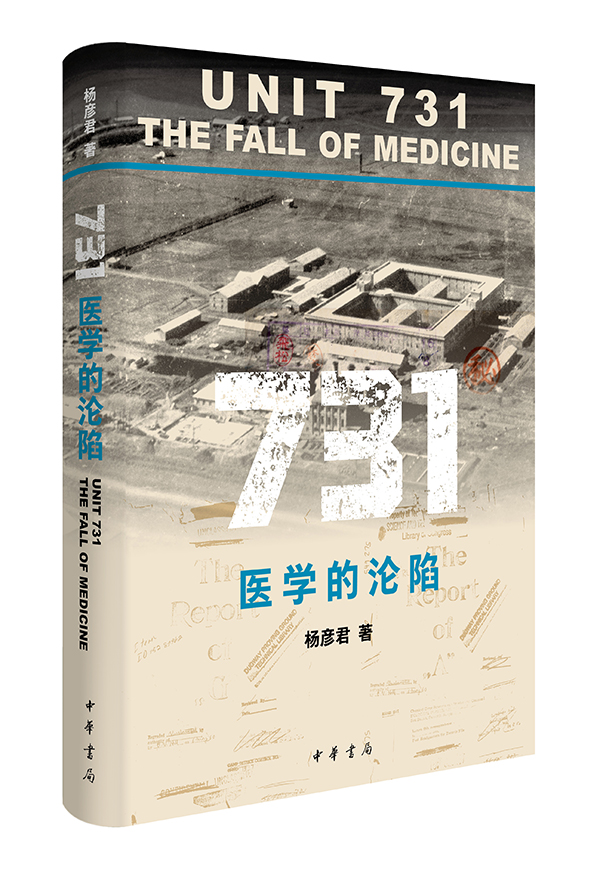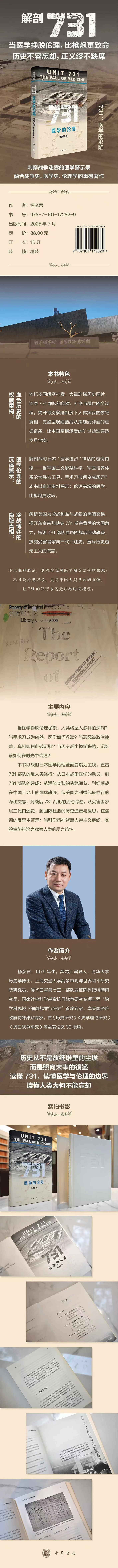导语
在九一八事变纪念日这个承载民族伤痛记忆的历史时刻,电影《731》在全球多地上映。据介绍,该片主要讲述了抗战胜利前夕,侵华日军为了扭转战局,在黑龙江哈尔滨平房区开展细菌战研究,屠戮百姓进行人体实验的故事。
侵略者曾企图掩盖真相,但中国人民揭露历史的决心永不磨灭。中华书局近期推出的《731:医学的沦陷》一书由杨彦君博士撰写,以严谨档案和受害者口述为证,为这段黑暗历史提供了扎实的学术注脚;书中所收录的大量图片更是历史的直接见证,文字与图片一起,共同致力于传递真实的历史记忆。
杨彦君博士交来《731:医学的沦陷》的书稿时,北京正值仲春季节。办公室外阳光明媚、万物升腾,340余页的书稿摊开如一幅沉重的历史长卷——书稿的731外文档案文献、泛黄的历史图片扫描件、受害者家属口述录音的文字整理稿,在纸页间凝结成一种近乎凝滞的重量,压抑得让人窒息。作为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我们知道,摆在面前的书稿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更是一场对人性底线、医学伦理与历史正义的深刻叩问。
想做“731”题材的念头,始于去年初哈尔滨文旅的一次出圈。南方的“小土豆”来了,台湾的“小当归”来了,让“尔滨”这个城市收获了极高关注度。但真正让哈尔滨在历史与文化层面出彩的是,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的热度持续攀升。南北西东来的游客在这里驻足,亲眼见证了侵略者的滔天罪行,重温了中华民族曾经历的深重苦难,各自媒体也随之涌现出了大量文章与视频,这股对731历史的关注热潮,为我们后续的选题探索埋下了伏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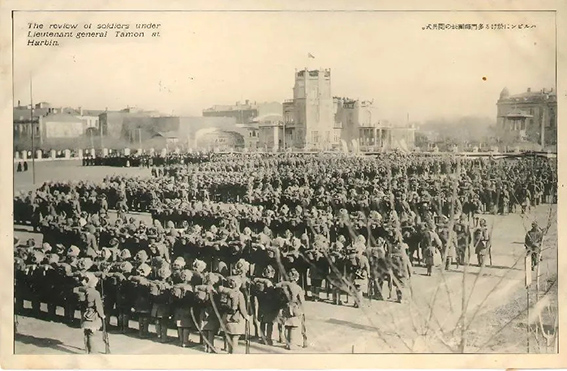
事实上,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海内外关于731部队的专题研究、文献汇编、纪实文学、口述历史、电视纪录片等体裁多样的出版物不断涌现。然而,这些作品大多侧重于呈现战争体验、考证事实存在、追溯个体命运,却鲜有对医学犯罪与人体实验产生的历史根源展开深入剖析,更缺乏探究国家政治、军国主义、社会制度、医学体制与731部队之间内在关联的研究。也正因如此,我们意识到,若仅将731部队的行为当作普通战争罪行来书写,便会遗漏最可怕的部分:他们是身着白大褂的屠夫,用手术刀实施了比枪炮更残忍的杀戮。这一认知,让我们更加明白,2025年是抗战胜利纪念80周年,需要一部作品撕开日本战时“医学进步”的伪装,解剖医学如何被军国主义绑架,最终沦为反人类的工具。
不过,这一选题的推进难度也显而易见。一方面,有关731部队的核心档案在二战后被美军秘密接管,大量关键史料散落在日、美、俄(前苏联)等国家的档案馆中,搜集与整合工作面临巨大挑战;另一方面,选题涉及抗战历史、医学伦理、冷战政治等跨学科议题,要求研究者既具备扎实的史学考据能力、广阔的国际视野,又拥有深刻的人文思辨素养。而杨彦君博士——这位同时任职于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与高校研究机构的学者,恰好成为了这一选题的最佳人选:他不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重大项目)“跨学科视域下细菌战罪行研究”,查阅了中外的档案馆,还深入采访受害者遗属,整理出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为选题的深入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编辑书稿前,虽需做足心理建设以面对沉痛的历史,但当直面那些“会说话的史料”时,其传递的呐喊声仍带来难以抵消的震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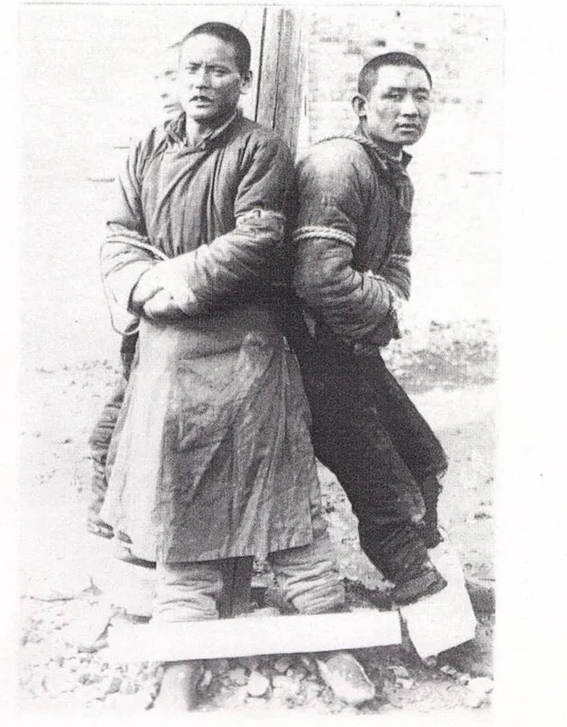
书稿以客观视角还原731部队肇建、扩张至覆亡的全过程,未过多刻意渲染恐怖血腥,但是原731部队成员口述与实验报告的冲击力依旧强大。如栗原义雄回忆“饮用水实验”:“喝普通水的人活了一个月,喝蒸馏水的人20天左右就死了,反正他死得挺早。”石川太刀雄丸的炭疽人体实验报告,详细记录32名受试者感染过程与结果,一句“此9名病例口服含炭疽杆菌食物后,数天因严重腹部感染和腹水出血死亡”,字迹冷静却字字浸血。《费尔报告》更揭露其残忍:731部队用多种细菌以不同方式做人体实验,精准记录“鼠疫菌皮下注射的半数感染剂量为10—6毫克,口服为0.1毫克”,以及炭疽菌“开放性伤口和吸入感染死亡率为100%”等数据;甚至记载使用陶瓷炸弹进行的鼠疫媒介物跳蚤感染人体实验,“约有80%的跳蚤在爆炸后仍能存活。在一个10平方米的室内,对10名受试者进行的爆炸实验中,有8人受到跳蚤叮咬而被感染,这8人中有6人死亡”。每组数据都是若干条生命的哀嚎。
编辑中,美方四次调查731部队的档案令人印象深刻,完整呈现其掩盖罪行的交易。美军化学战专家费尔是关键推手。他在报告中详细记录,石井四郎不仅愿意交出人体实验数据,献出细菌战构想,甚至提出“受聘为美方生物武器专家”,以20年研究成果换来其与下级的豁免。费尔建议美国政府“以书面形式豁免有关高级别官员的战争罪行”来获取资料,并“通过情报渠道留存,不会作为战争罪行的证据来使用”。肮脏的交易最终达成,美国认为这些人体实验数据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远超了战争罪审判价值。其继任调查官希尔在《生物战调查总结报告》中写道:日本人获得人体实验数据,花费几百万美元、历经数年,而美国获取这些数据,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并且“我们花费了25万日元,但是这与实际研究的成本相比实在微不足道”。
书稿收录了多名受害者家属的口述,他们的遭遇更令人揪心。其中王亦兵老人回忆:1943年父亲王耀轩被抓走,“母亲至死抱着他带血的棉袄说‘他被当成牲口宰了’”。王耀轩本是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站成员,因“大连黑石礁事件”被捕,遭酷刑后被“特别移送”至731部队,直至1956年王亦兵才确认父亲遭人体实验杀害。此后数十年,他四处奔波拼凑父亲踪迹及自己对父亲的记忆,1995年当参与“特别移送”的日军宪兵三尾丰向他当面谢罪,“我把他们像猪一样踢进黑车,送进地狱”,让他积压半世纪的悲痛有了落点。这些首次公开的三代人口述,填补了官方档案中“个体创伤”的空白——历史从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一个个家庭被撕裂的疼痛。

左一为三尾丰,左二为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左三为大连史志办主任单文俊,左四为王亦兵(王耀轩之子),左五为王晓光(王耀轩之孙)
这部书稿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突破了传统历史书写的单一维度,构建了“罪证—反思—记忆”的三重叙事体系。
第一重光是“罪证之镜”。书中用大量篇幅还原了731部队的运作逻辑:从陆军军医学校的“医学动员”,到平房基地的“防疫研究”伪装;从“特别移送”制度对平民的制度化绑架,到细菌战在宁波、常德等地造成的“千里焦土”。尤其是第四章对人体实验的解析,没有刻意渲染血腥,而是通过实验设计、数据记录、报告结果的分析,揭露其“科学化暴行”的本质——当医学伦理彻底崩塌,实验室便堕落成了屠宰场。
第二重光是“反思之锋”。书稿深刻剖析了两个关键问题:为何日本医学精英会集体堕落?为何美国会包庇战犯?前者指向军国主义对科学体制的异化——军医们以“为国家服务”“推动医学进步”为借口,将人道主义底线一步步碾碎;后者则揭开冷战政治的算计——美国为获取人体实验数据,与战犯达成秘密交易,导致东京审判对731部队罪行的“集体失语”。这种对制度性罪恶的追问,让本书超越了对个体恶行的谴责。

第三重光是“记忆之火”。第十章“负遗产与记忆之场”尤为动人。作者回顾了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的建设历程和731部队旧址考古发掘情况;跟踪了李凤琴老人跨越数十年的寻父之路——她父亲是1944年被“特别移送”的抗日烈士,至今尸骨无存。这些故事告诉我们:记忆的传承,本身就是对历史虚无主义最有力的反击。
编辑《731:医学的沦陷》这部书稿的过程中,有两个细节至今难以忘记,每当回想起来,都能感受到历史沉甸甸的分量与作者的深意。
第一个细节,是作者在书稿中特意收录的大量图片。这些图片跨越80多年的时光,构成了一部无声却震撼的“视觉史书”:这其中既有80年前731部队基地的全景照、成员合影,组织结构图,也有战后数十年原731部队成员举办“战友会”活动的照片;既有美军战后展开调查活动的影像记录,也有美方所藏核心档案的原件影印件;更有受害者遗属肖像照,还有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的图片。每一张图片都是历史的直接见证。收录这些图片,就是为了打破“历史虚无”的幻象,让读者真切感受到:书中的每一段文字、每一个故事,都不是虚构的叙事,而是真实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苦难与罪恶。

第二个细节,是与作者就图书读者定位展开的讨论。最初作者是想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以专著的形式出版,通过“医学伦理”“侵华罪恶”等来聚焦战争罪行,反思医学在军国主义裹挟下毫无人道的沦陷。但是我们认为,731部队的罪行应当让更多普通中国人知道,建议改成学术普及书,可以适当配图。杨彦君博士反复斟酌后,同意了我们的建议,书名确定为《731:医学的沦陷》,并对书稿进行了细致的修改。“沦陷”二字,既指向战时日本医学伦理的全面崩塌,也暗含着对当下的警示——科学永远需要伦理的缰绳,一旦挣脱,就可能重蹈覆辙。这个书名,让整部书的立意从“揭露罪行”升华到“守护底线”,更具现实意义。而学术普及的定位,让它贴近更多想了解731部队罪恶历史的读者。
5月初书稿在加工时,杨彦君博士发来一条消息:“下周四央视来上海采访我,14号拍,《国家记忆》来了4个央视记者,来录制节目。”我们突然觉得,这本书不仅是写给现在的,更是写给未来的。我们编辑的不仅是一部书,更是一份需要传递下去的记忆遗产。
如今,《731:医学的沦陷》已经面世,并很快迎来了再版。它虽不能改变历史,但能让更多人知道:731部队的罪行,不仅是战争罪,更是医学伦理的耻辱;对这段历史的铭记,不仅是为了追责,更是为了守护科学的人文底线。正如那句叩问:“当手术刀成为凶器,医学如何救赎?”答案或许就藏在每一个翻开这本书的人心里——唯有记住黑暗,才能守护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