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贶(kuàng)节,又有六月六节、晒书节、农家节、迎女节、半年节、鄱官节、牛羊节、清暑节等名目。这个节日主要源于传统历法中以“重日(日月重数)”为节的习俗,有着非常古老的民俗基础,而宋真宗利用道教编创了“降天书”的神话则最终催生了该节,形成了一个以祭祀、晾晒、尝新、酿造、郊游、沐浴、养生、回娘家等民俗活动为特色的传统节日。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演变,该节在现代民俗中已经基本消失。
一 汉唐时期六月六传统民俗
早在天贶节设立以前,六月六作为“重日”就被视为一个特殊的日子,形成了一些农业劳作、医学养生以及宗教祭祀等方面的民俗。
首先,在农作习俗方面,六月正逢伏天暑月,在夏季农作物收割之后,正好适宜种植秋季作物和开展其他农事活动,所以人们选择在六日这天种葵菜、萝卜和制曲造酱等。
种葵菜,据东汉崔寔《四民月令·六月》载:“是月六日可种葵。”葵菜,民间习称冬苋菜或滑菜。按收获季节可分为春葵、秋葵和冬葵,此月所种是秋葵。元代以前,葵菜曾广泛种植,被称为“五菜(葵、韭、藿、薤、葱)之主”,或“百菜之主”,成为蔬菜中的上品。王祯《农书·百谷谱集之四》就说:“葵为百菜之主,备四时之馔……诚蔬茹之上品,民生之资助也。”但是,随着新菜品种的大量引进和培植,葵菜种植逐渐减少以至被淘汰,到明代葵菜已经基本退出蔬菜行列,多以野生为主,所以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一六《草部》说:“古者葵为五菜之主……古人种为常食,今种之者颇鲜。”
种萝卜,据唐人韩鄂《四时纂要·六月》载:“种萝卜:宜沙糯地。五月犁五六遍,六月六日种。”萝卜,最早称“莱菔”,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据《本草纲目》卷二六《菜部》载:“莱菔乃根名,上古谓之芦萉,中古转为莱菔,后世讹为萝卜……圃人种莱菔,六月下种,秋采苗,冬掘根。”据清代王鸣盛考证,“莱菔”应即唐代讹为“萝卜”的(参顾美华标校《蛾术编》卷六二《说物》,上海书店出版社,2023,898页)。
制曲,据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七《笨曲并酒》引《四民月令》曰:“六月六日,七月七日,可作曲。”六、七两个月的“重日”,正是夏季高温湿热之时,特别有利于发酵,所以古人选择这两个日子来制曲,显然是赋予其某种神秘的涵义。《四时纂要·六月》也说:“六日造法曲。”据缪启愉解释:“在一定的日期,采取一定的方法配制并保证一定的质量的曲,古时叫‘法曲’。”(缪启愉《四时纂要选读》,农业出版社,1984,88页)古人之所以强调六日制曲,和医家倡导有关。唐人孟诜《食疗本草》就说:“曲,味甘,大暖……六月作者,良。”(尚志钧辑校《食疗本草》,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14页)宋人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四《天贶节》引北宋吕原明《岁时杂记》也说:“医方所用神曲,皆六月六日造也。”曲是一种催化物,既可用于酿酒制酱,也可入药。此后,六月六日酿制传统一直延续到近代,如康熙《宿州志》:六月六日,“造神曲”。又如民国《南陵县志》:“六月六日造酱及曲,谓之‘酿霉’。”

其次,在医学养生方面,六月六日也形成了一些特殊民俗,如收楮实,据《四时纂要·六月》:“收楮实:此月六日收为上。”《岁时广记》也载:“《经验后方》:‘炼榖子煎法:取榖子五升,六月六日采,以水一石煮,取五升,去滓,微火煎如饧,堪用。 ’隐居云:‘榖子即楮实也,仙方取以捣汁和丹用。 ’《抱朴子》云:‘楮实赤者服之,老者少,令人夜能彻视鬼神。道士梁顿,年七十乃服楮实者。 ’”《经验后方》为宋人编撰的一部医书,“隐居”指南朝齐、梁时道教学者、炼丹家、医药学家陶弘景;《抱朴子》是东晋葛洪编撰的一部道教典籍。这说明从魏晋以来楮实就成为一味著名的“神仙药”。
另外,六月六日还是道教的清暑之日,据北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卷三七《说杂斋法》引《三洞奉道科》记载,道教岁时杂斋中就有“六月六日为清暑斋”之说。《三洞奉道科》大约成书于南北朝或隋唐之际。每年农历六月六日前后正是大暑时节,为一年中最为炎热之季,道教将此日作为清暑之日,做清暑斋,祭祀神明,反映了此俗从南北朝隋唐以来就受到宗教的重视。
二 宋代天贶节的正式设立
六月六日被正式确定为天贶节是在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设立该节的主要原因是澶渊之盟后,宋真宗为了巩固统治,导演了一出“天书”频降的闹剧。
关于“天书”降临,据史书记载,前后至少有三次: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三日,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上书:“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宋真宗名讳赵恒,这等于宣告说他是应天受命的真龙天子,于是下令改元大中祥符;四月初一,天书又降;六月六日,天书再降于泰山,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广福。赐尔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国祚延永,寿历遐岁。”
于是宋真宗下令以正月初三为“天庆节”、四月初一为“天祯节”(后来为了避宋仁宗赵祯讳,改名为“天祺节”)、六月六日为“天贶节”。节日期间还要放假,并举行一系列祭祀庆祝活动。如:天贶节,休假一日,禁止屠宰、用刑,京城于上清宫建道场,百官行香,赐宴;当天夜里,京师还要举办灯会;各地州府,建圣祖殿,长官率僚属朝谒。所谓天贶,意为上天的恩赐。宋真宗认为“天书”降临就是上天的恩赐,故设此节,以示庆祝。
这三次“天书”降临事件,显然是宋真宗君臣合伙编造,并利用来达到宣示君权神授、皇权天授,进而神化赵宋王朝统治目的的。所以《宋史·真宗纪》“赞”指出:“及澶渊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遂进神道设教之言,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潜消其窥觎之志欤?”南宋洪迈《容斋五笔》卷一“天庆诸节”条也指出:“大中祥符之世,谀佞之臣,造为司命天尊下降及天书等事,于是降圣、天庆、天祺、天贶诸节并兴。”
由此可见,天贶诸节的设立纯系宋真宗借“神道设教”来巩固统治之举。不过,将天贶节设在六月六日,除了有一定的民俗基础外,还与传统的讨吉利说法有关。早在先秦时期,在传统文化中就形成了“六六大顺”的吉祥祝福之说,兼之又是岁时中的“重日”,这样就为该节的设立创造了有利条件。事实上,在宋真宗所设诸节中,只有六月六日天贶节在后代有所流传,并对传统民俗产生了一定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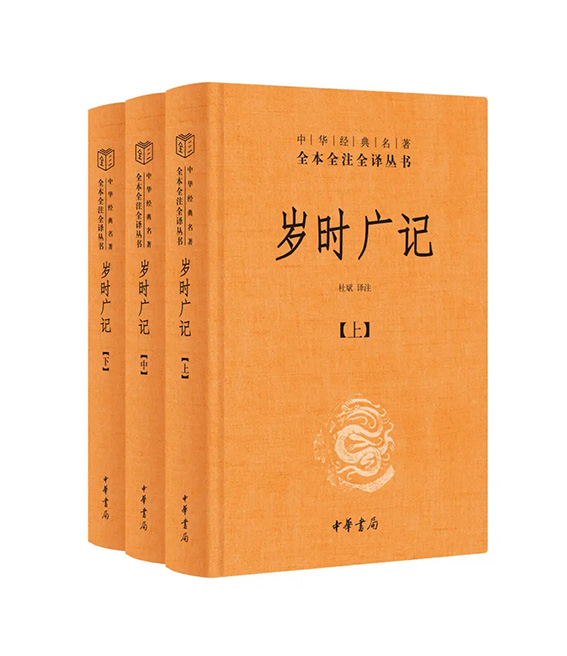
三 天贶节祭祀对象的多元化
中国传统节日大多与祭祀活动有关,天贶节更是如此。该节本来就是宋真宗为了感谢“天书”降临而设立的,所以最初主要是由政府举行各种敬天祭祖等活动,但是这些与“天书”降临有关的祭祀朝谒活动并没有延续下来,而是在长期的民俗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多种神灵祭祀共存的名目繁杂的六月六节,如:
大禹祭,据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五二《成都府路·石泉军》载:“禹庙,在军城南江外……《帝王世纪》以为鲧纳有莘氏,臆胸坼而生禹于石纽。郡人以禹六月六日生,是日熏脩祼飨,岁以为常。”此事又见祝穆《方舆胜览》。《帝王世纪》为西晋皇甫谧作。论者据此大多认为六月六日大禹祭民俗至晚形成于魏晋时期,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因为王书所引《帝王世纪》,在传世的各种版本中并没有“郡人以禹六月六日生……”句,显然王书记载的是当时的情形,又为祝书所抄袭。而稍早于王、祝二书的罗泌《路史》后纪卷一二也有“(禹母)以六月六日,屠疈而生禹于僰道之石纽乡”的记载,其子罗苹注曰:“今淮南俗,尚以六月六日为禹王生日。苏轼《游涂山庙》诗自注云:‘是日数万人。 ’”苏诗作于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名为《上巳日,与二子迨、过游涂山、荆山,记所见》,自注为:“淮南人相传,禹以六月六日生,是日,数万人会山上。虽传记不载,然相传如此。”(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三五,中华书局,1982,1866页)但都没有提到是根据《帝王世纪》。涂山,在今安徽凤阳。关于六月六日大禹祭之说,亦不见于《太平寰宇记》及之前的史书,应该属于宋代以来地方风俗相沿而成。到明代,六月六日涂山大禹祭还被定为官方祀典,如成化《中都志》载:“禹庙,在涂山绝顶……国朝定祀典,命有司以六月六日奉祭。”嘉靖《怀远县志》载正德十年《重修涂山禹王庙碑记》亦载:“涂山之有禹庙,其来不既远乎,迨我皇明益隆,祀典牲币有加,每岁六月六日遣官致奠,享祀不忒,其崇德报功盛矣。”大禹祭活动受到官方重视,祀典规模也越来越大、愈加隆重。直到民国时期,有些地方还保留此俗,如《新修张掖县志》:六月六,“有祭夏禹者”。
关于关公、真武灵应真君、崔府君祭,见《岁时广记》引《道藏》经云:“六月六日为清暑之日,崇宁真君降诞之辰。”又引《正一朝修图》曰:“六月六日,真武灵应真君下降日,护国显应公诞生之日,大宜禳禬。”由此可见,至晚在南宋时期,六月六日已经被道教赋予了更多神祇诞节。
崇宁真君,即关公,相传为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所封。明代张正常《汉天师世家》卷三载:崇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宋徽宗召见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作法,役召关羽,“上惊,掷崇宁钱与之,曰:‘以封汝。’世因祀为崇宁真君。”(《道藏》 34册,上海书店出版社、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827页)此事又见《道法会元》卷二五九《地祇馘魔关元帅秘法》(《道藏》 28册,594页)。关于关公诞民间还有几种说法,如五月十三、六月二十四等。而六月六崇宁真君诞,大概只是道教流传的一种说法。
真武灵应真君,即北方之神玄武,又称佑圣真君、玄天上帝,后世奉祀为真武大帝。据《宋会要辑稿·礼五》载: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六月,诏加真武号曰‘真武灵应真君’”。又据元代道士刘道明编集的《武当福地总真集》卷下收录有天禧二年七月七日《宋真宗皇帝加上真武将军圣号御笔手诏》则曰“镇天真武灵应佑圣真君”(《道藏》 19册,662页),简称“灵应真君”或“佑圣真君”。关于真武下降日,据《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载:“每月三七日,宜下人间。受人之醮祭,察人之善恶。”(《道藏》1册,814页)宋代流传甚广的佑圣真君生辰为三月初三,如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二《三月(佑圣真君诞辰附)》载:“三月三日上巳之辰……此日正遇北极佑圣真君圣诞之日。”不过,明代一些地方还保留有六月六祭玄帝风俗,如嘉靖《曲沃县志》载:“六月六日,上紫金山,祭玄帝。”玄帝,即真武大帝。
护国显应公,即崔府君、崔判官,为古代民间信仰的重要神灵之一,也是道教奉祀的神仙。崔府君信仰兴起于河北磁州一带,北宋时因府君屡屡显灵,受到统治者册封,故其信仰在民间逐渐兴盛起来。据《宋会要辑稿·礼二一》载:“护国显应公庙,庙在东京(今河南开封)城北,即崔府君祠也。相传唐滏阳令,殁为神,主幽冥事。庙在磁州。太宗淳化初(990),民有于此置庙。至道二年(996),晋国公主石氏祈祷有应,以其事闻,诏遣内侍修庙,赐名,并送衣物供具。真宗景德元年(1004)重修,春秋二祀。磁州庙,咸平元年(998)重修,五年赐额曰‘崔府君庙’。朝廷常遣官主庙事。仁宗景祐二年(1035)七月,封‘护国显应公’,仍令开封府、磁州遣官祭告,具上公礼服。一在西京庆州(今甘肃庆阳)。神宗熙宁八年(1075)十二月,诏府君庙特加封号。”又相传崔府君是唐初人,生前有惠政,死后被当地人奉为神。据说六月六为崔府君生日,故在东京汴梁要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载:“六月六日,州北崔府君生日。多有献送,无盛如此。”后来,金兵南下,北宋灭亡,传说崔府君显圣救驾,“泥马渡康王”,而得到宋高宗的褒封,从此崔府君信仰大盛。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载:“六月初六日,崔府君生辰,庙在湖上涌金门外,显应观者是,社火亦然。有烧香者不少,金橘团最盛。”(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11页)吴自牧《梦粱录》卷四《六月(崔真君诞辰附)》也载:“六月初六日,敕封护国显应兴福普佑真君诞辰,乃磁州崔府君,系东汉人也,朝廷建观在闇门外聚景园前灵芝寺侧,赐观额名曰‘显应’,其神于靖康时高庙为亲王日出使到磁州界,神显灵卫驾,因建此宫观,崇奉香火,以褒其功。此日内庭差天使降香设醮,贵戚士庶,多有献香化纸。”这里提到崔府君系东汉人,一般认为是著名学者崔瑗(77—142),字子玉。此外,还有北魏崔浩(字伯渊)说、唐代崔珏说。由于瑗、渊、珏,三字发音接近,所以在金元时期,民间在糅合了历史上这几位名人的名字、传说后,终于定型为崔府君名珏、字子玉、初唐人的说法。
此外,明清以来,各地六月六还形成了一些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祭祀活动,主要有:
祭天,如光绪《定襄县补志》:“六月六日,城乡各祀郊神,谓之祈伏雨。”所谓郊神,就是到南郊祭祀天神。
祭龙神(王),如光绪《岢岚县志》:“六月六日,迎神赛社,城乡虔祀龙神。”又如民国《通县志要》:“六月六日,祭龙王、冰雪各神。”祭龙神一般都与祈雨有关,如民国《陵川县志》:“六月一日至十三日,大小村庄咸聚会,上菊巘山龙神祠虔祭,祈雨泽。”
祭河神,如乾隆《孝义县志》:“六月初六,祀园场神、河神。”园场神应与农业、园艺有关,河神则与祈雨和防洪有关。如乾隆《乡宁县志》:“六月天贶节,以附河多水患,祀河神。”不过,孝义所祀应为汾河神,乡宁所祀则为黄河神。
祭山神,如雍正《泽州府志》:“六月六日,家家祀山神,相传神即射日之羿,以开门即山,祀以辟虎狼。”泽州山神奉祀的是传说中的射日英雄后羿,除了祈雨外,还与祈愿出行安全、避免野兽伤害有关。
祭土地神,如《兴仁县志》:“六月六日,俗谓是日为土地生辰。城乡各刑牲庆寿。农家剪纸为马形,插于田中,只鸡斗酒祀之,谓之敬秧苗土地。”又如《玉屏县志》:“六月六日,俗谓土地生日,家竞设祭。”在民间,祭土地神大都与农业生产有关。
祭畜牲之神,主要流行于晋东南一带,如乾隆《长子县志》:六月六日,“乡民争献牲于三嵕庙,又各享祀畜牲之神”。三嵕庙,为山神庙;畜牲之神则专管畜牧业,由此还形成“牛羊节”,如乾隆《沁州志》:“六月六日为‘牛羊节’。凡有牛羊者,必以美食犒牧人。”这说明在晋东南一带,畜牧业也较发达,因此才有此类祭祀。
祭田神。田神名目繁多,如神农,据康熙《隰州志》:“六月六日,三皇庙祭神农。”在民间,神农被当作农业神祭祀。祭方社、先啬,据民国《繁昌县志》:“六月六日,田夫合里党祀方社、先啬,树黄白帜,召巫诵道科书,以祈有年,亦《周礼》龡《豳》击鼓之遗意欤。”先社,指四方神和土地神;先啬,即先农,指教民耕种的神农、后稷等农神。祭方社、先啬有悠久历史,这是一项从先秦时期就流传下来的古俗。祭田祖,据民国《铜陵县志》:“六月六日,祀田祖祈谷。”田祖,也是田神。在长江流域,则流行祭婆官,并形成“鄱官节”,如乾隆《岳阳府志》:“六月六日,农家祀田神,谓之‘鄱官节’。”农家于此日五更,杀鸡祭鄱官,据嘉庆《善化县志》:六月六日,“农民于五更时割雄鸡祀田神,谓‘祭鄱官’”。鄱官,又名番官,讹作婆官,据说在五代时就被祀为田神。据同治《萍乡县志》:“六月六日天贶节……农圃各礼田祖,谓之‘祭婆官’。”自注云:“田神名‘番官’,始五代时,俗误为‘婆’。”
祭城隍,相传六月六为城隍生日,因此很多地区都流行此俗。如嘉庆《九江府志》:“六月六日晒衣,土人设会为城隍庆生。”又据同治《彭泽县志》:“六月六日,相传为‘邑城隍生辰’。前三日扫道清尘,临期出巡,扮伯爵旗卫,满街结彩,香案迎讶。各街坊装台阁故事,备极精巧,观者盈市。”由于明清时期城隍信仰大盛,所以民间祭祀非常隆重热闹。
拜墓,如顺治《真定县志》:“六月六日,以壶浆奠先墓。”民国《新乐县志》:“六月六日,是日俗多壶浆祭冢。”六月六拜墓祭祖习俗,当与祈祷祖先赐福、保佑子孙后代有关。
此外,有些地区还有祭祀李冰父子(水神)、杨四将军(又作杨泗,主要在四川、湖南、湖北、江西一带民间信仰的斩蛟除妖水神)、圣母(主管生育、送子、护佑儿童的女神,如河南密县以六月六日妇女结社祀圣母于广生祠、广西来宾以六月六日为“花林圣母神诞”等)以及灶神、虫王、八蜡神之类的习俗。这些祭祀活动大都与祈祷降雨、灾害不作、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福佑子孙等美好愿望有关。
随着六月六祭祀对象的多元化,民间对天贶节的称谓却越来越陌生,反映在宋元以降的各地志书中称六月六为天贶节的越来越少,而称“六月六节”的却越来越多。
四 天贶节的其他民俗活动
天贶节除了要举行各种各样的祭祀活动外,因六月恰为一年之中的半岁,所以有些地方又将六月六当作“半年节”来过,并形成了许多有趣的民俗活动,称作“半年福”。如万历《六安州志》:“六月六日,曝衣物,作‘半年福’。”康熙《永州府志》:“六月六日,谓之‘半年节’。以酒肴祀家庙,或曝书及衣物。”光绪《黄冈县志》:“六月六日,晒书籍衣物,造酱醋、盐豉,俗以为‘半年福’。”除了曝晒书画衣物、酿醋造酱、祭祀家庙等活动,还形成了出游、洗浴、回娘家、养生食疗、占卜等习俗。
曝晒习俗。明清时期,六月六发展出晒书、晒衣物习俗。据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四《风俗》载:“六月六日,本非令节,但内府皇史宬曝列圣实录、列圣御制文集诸大函,则每岁故事也。”又据清代富察敦《燕京岁时记》载:“京师于六月六日抖晾衣服书籍,谓可不生虫蠹。”据此可知,每逢六月六,不论皇宫民间,贫富之家,都要晾晒家居、衣物、书籍。不过,此俗应该是从汉唐时期的七月七日移植而来的。早在汉魏时期,七月七日就形成了晒书、晒衣风俗,如《四民月令·七月》载:七日,“曝经书及衣裳”。《太平御览》卷三一《时序部》引该书后说:“习俗然也。”又引唐代《韦氏月录》载:“七月七日晒曝革裘,无虫。”这说明唐宋时期延续了七月七日曝晒习俗。但到明清时期,晾晒习俗已经挪到了六月六日,各地志书也多有记载,如康熙《宿州志》:“六月六日,曝衣及书画。”有的地方还把此日称为“晒书节”,如乾隆《望江县志》:“六月六日,俗以为试新,曝书之节。”道光《武进、阳湖县合志》记载民谚曰:“六月六,晒红绿。”寺观也将此日当作晒经日,农家还要曝晒粮食,如光绪《定兴县志》:“六月六日,为‘佛寺晒经日’。因之文人曝书籍,妇女曝衣衾。”民国《新河县志》:“六日,居民出粮食、衣被、书籍、经卷而晒之。”有的地方还要大扫除,如民国《徐水县新志》:“六月六日,晒书、晒衣,以免虫蚀;将房屋、院宇大扫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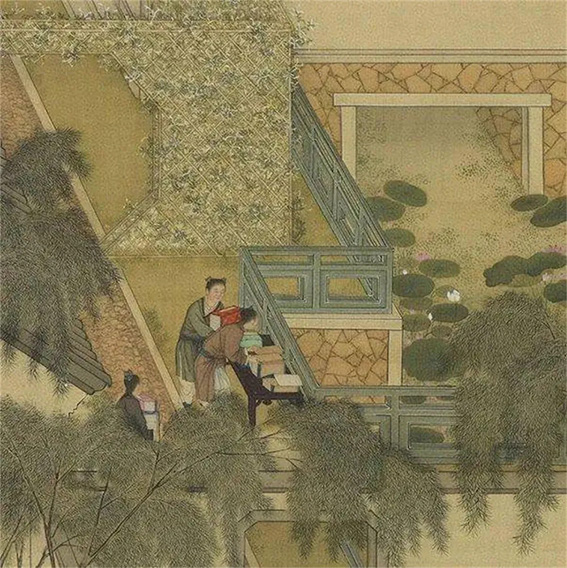
▲ 清·《十二月令 六月》(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
出游习俗。此俗在南宋时就已出现,人们将六月六日外出祀神逐渐扩展为消暑出游活动。据宋人周密《武林旧事》卷三载:“六月六日,显应观崔府君诞辰,自东都时庙食已盛。是日都人士女,骈集炷香,已而登舟泛湖,为避暑之游。”又如《梦粱录》卷四载:“是日湖中画舫,俱舣堤边,纳凉避暑,恣眠柳影,饱挹荷香,散发披襟,浮瓜沉李,或酌酒以狂歌,或围棋而垂钓,游情寓意,不一而足。盖此时烁石流金,无可为玩,姑借此以行乐耳。”人们借祭神出游,避暑纳凉,嬉戏娱乐,享受夏日难得的休闲时光。到明清时期,有些地方还发展出六月六赛龙舟活动,如道光《川沙抚民厅志》载:“六月六日……尤赛龙舟,士女喧阗,四城壕舟楫填塞过于端午。”川沙抚民厅约在今上海浦东一带。此地的六月六赛龙舟活动异常热闹,大有超过端午节之势。由于各地季节差异很大,此时南方正是避暑时节,而北方有些地方却刚开始“踏青”。如乾隆《大同府志》:“六月六日,东郭外菜园开,郡人争携壶榼往,谓之‘踏青’。”又如乾隆《赤城县志》:“六月六,具酒肴野游,名曰‘耍青’。”还有的地方有登高习俗,如宣统《固原州志》:“六月六日,游东岳山,谓之‘登高山’。”直到近代,许多地方仍保留有六月六出游民俗,如民国《雄县新志》:“六月六日……南浦之菱芡既登,荷花亦盛,民拉朋携妓,画船箫鼓,竟日忘返;缙绅或棹舟觞咏,泊柳堤,听渔唱,陶然自适。”
清洗习俗。古人非常注意卫生,重视沐浴,讲究择时与仪式。选在节日沐浴往往带有趋吉避邪目的,如三月三日上巳节祓禊、五月五日端午节兰汤沐浴等,莫不如此。不过,相比之下,六月六日的洗浴更有特色,它既是妇女儿童洗浴日,也是猫狗动物清洗日,还是家居器物洗涤日。早在元代,出于防疫目的,就出现了六月六“本日浴猫狗”之说(参汪汝懋撰,李崇超校注《山居四要》卷四,中国中医出版社,2015,58页)。到明清时期,此俗大盛,据《万历野获编》载:六月六日,“至于时俗,妇女多以是日沐发,谓沐之则不䐈不垢,至于猫犬之属,亦俾浴于河。京师象只,皆用其日洗于郭外之水滨,一年惟此一度。”清代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也载:“妇女多于是日沐发,谓沐之不腻不垢。至于骡马猫犬畜牲之属,亦沐于河。”六月六沐浴,不但清洁了身体,而且有祛病消灾寓意。如妇女在此日洗头据说可以止痒,光绪《甘肃新通志》就说:“六月六日,游五泉西龙口沐发,谓能已头痒。”小孩沐浴,据说可以“洗百病”。如民国时期的浙江建德、定海一带,一直保留着六月六日小儿沐浴之俗。据《建德县志》载:“小儿必于是日净浴,故俗又有‘六月六,黄狗洗个浴’之说,盖取其贱而易育也。”《定海县志》也载:“六月六日,燂汤为儿童浴,谓可免痈疡。”而在此日猫、狗、大象等动物洗浴,意在祛病防疫,如嘉靖《昆山县志》:“六月六日,浴猫犬于河,去蚤虱。”民谚也云“六月六,猫狗浴”(同治《安吉县志》),甚至称六月六为“猫狗生日”(见光绪《平望志》)。在河南、江苏、松沪一带,六月六还是家居器物清洗日,如嘉靖《尉氏县志》:“六月六日,家家洗涤器用。”又如乾隆《奉贤县志》:“六月六日,涤器于河,略仿修禊之意。”光绪《锡金识小录》也载:“六月初六日,居民多驱犬于河浴之,灯檠之属亦以是日濯于水,谓之‘天贶节’。”有些地方虽然还保留有传统天贶节之称,但节俗内容却与当初设节之意已大不相同。

回娘家。六月六还是出嫁女儿的回娘家日,如万历《滁阳志》:六月六日,“迎女之已嫁者”。回娘家也称“归宁”,如嘉庆《合肥县志》:六月六日,“妇女偕婿归宁”。因此,有些地方称六月六为“迎女节”,如光绪《高陵县志》:“六月六日,迎女节。”由于六月六,恰逢盛夏,所以在关中一带,还流行父母给新出嫁的女儿送单衣之俗,如民国《同官县志》:“六月六日为‘迎女节’,新嫁女母家授以单衣,谓之‘避凉’。”又如民国《盩厔县志》:六月六日,“凡新嫁之女,其父母多于是日馈纱葛、夏服之类于婿家”。在河北南部,女儿回娘家还要带新麦面蒸的馍头,如民国《成安县志》:“旧六月六日……每年麦后,已嫁之女,其翁姑辄与之蒸一盒子,令其向娘家瞧瞧,曰‘送麦馍首’。按之古俗,即女子归宁父母也,一岁一次,相率为常。”在江苏六合,还有娘家送出嫁女腊肘、花红之俗,如光绪《六合县志》:六月六日,“母家熟腊肘,市花红以馈其女”。有些地方还形成了六月六麦收后姻亲之间相互往来之俗,称为“缀节”,如乾隆《崞县志》:“六月六日,麦已登,男女亲家妇女相往来,名曰‘缀节’。”“缀节”,又称“追节”,一般是指出嫁女带着婆家准备好的礼物回娘家探望父母、娘家回赠礼物给婿家的一种民间习俗,体现了姻亲之间礼尚往来、相互尊重的良好风尚。
养生食俗。古人非常重视食疗养生,尤其是在季节变化之时。六月六日,正是天气炎热时节,需要清热避暑,所以称为“清暑节”或“清暑日”,此时饮食应以清淡消暑为宜,故人们多选择食用新鲜的瓜果蔬菜,如《武林旧事》记南宋时六月六节食俗曰:“时物则新荔枝、军庭李(二果产闽),奉化项里之杨梅,聚景园之秀莲新藕,蜜筒甜瓜,椒核枇杷,紫菱、碧芡、林檎、金桃,蜜渍昌元梅,木瓜,豆儿水,荔枝膏,金橘、水团,麻饮芥辣,白醪凉水,冰雪爽口之物。”《帝京岁时纪胜》记清代六月六食俗曰:“盛夏食饮,最喜清新,是以公子调冰,佳人雪藕……且有鲜菱、芡实、茨菇、桃仁,冰湃下酒,鲜美无比。”明清时期,在江浙沪一带还形成了吃馄饨食俗,如万历《嘉定县志》:“六月六日,其食馄饨。”这种食俗是取防病避疫之意,如乾隆《上海县志》就说:“六月六日,啖馄饨,云解注(疰)夏疾。”六月六还有采马齿苋为过年时食用做准备的风俗,如万历《杭州府志》:“六月六日,采马齿苋阴干之,以供元日晨食。”又如康熙《仁和县志》:“(元日)晨兴,则以六月六日所取马齿苋蒸熟食之。”马齿苋,别名马生菜(谐音“马生财”)、长寿菜等,六月六采马齿苋寓意“六六大顺”“马上生财”“长命百岁”等美好愿望。在江西有些地方,还形成了“食鸡粥”风俗,如正德《建昌府志》:“六月六日,晒衣,人家食鸡粥,谓能补阳。是时阴极,故云然。”这是传统滋阴补阳观念的一种体现。在河南一带则有炒面食俗,如嘉靖《尉氏县志》:六月六日,“炒麦面食孩童,可治泄泻”。用炒面治小孩拉肚子,是中医的一种传统治疗方法。
古人也非常注重医学养生,六月六日还形成了一些新的采收种植及针灸民俗,如:
采豨莶。豨莶是一种菊科草本植物,可入药,疗效广。据《岁时广记》引北宋苏颂《图经本草》(又名《本草图经》)云:“豨莶,俗呼火杴草。今处处有之,人亦皆识。春生苗,似芥菜而狭长。秋初有花,如菊。秋末结实,颇似鹤虱。近世多有单服者,云甚益元气。蜀人服之之法:五月五日,六月六日,九月九日,采其叶,去根茎花实,净洗,曝干,入甑,层酒与蜜,蒸之,又曝。如此九过,则已气味极香美,熬捣筛蜜丸服之。治肝肾风气,四肢麻痹,骨间痛,腰膝无力者,亦能行大肠气。”在古代,重日都是特殊的日子,这三个重日处于夏秋之季,中医认为正是补益元气的好日子。
收瓜蒂。瓜蒂是一种葫芦科植物甜瓜的果蒂,也可入药,用于杀蛊和治疗黄疸、四肢浮肿等疾病。据《岁时广记》引宋代陈晔《经验方》载:“治遍身如金色:瓜蒂四十九个,须是六月六日收者,丁香四十九个,用甘锅子烧,烟尽为度,细研为末。小儿用半字吹鼻内及揩牙,大人用一字吹鼻内,立差。”
种茉莉,据南宋陈善说:“茉莉惟六月六日种者尤盛。”(袁向彤点校《扪虱新话》卷一五《论南中花卉》,山东人民出版社,2018,185页)茉莉是一种外来植物,原产印度等地,其花既可入药,也可食用,还可用来观赏,南宋时妇女还用来妆饰,如《武林旧事》载六月六日风俗曰:“茉莉为最盛,初出之时,其价甚穹,妇人簇戴,多至七插,所直数十券,不过供一饷之娱耳。”
诸如此类的养生习俗,都是医家在长期实践过程中,逐渐摸索出来的一套经验。有些养生习俗,直到民国时期仍有传承,如《天门县志》:“六月季夏六日,各家晒衣物,并针灸、收诸药。”
此外,六月六日还形成了占卜之俗,如乾隆《石首县志》:“六月六日为清暑之节……农家以此日阴晴卜牛草之贵贱。”又如嘉庆《怀远县志》:“六月季夏六日……且以是日阴晴卜秋之旱涝。”卜阴晴大多与农牧业生产有关。
结 语
总之,天贶节是宋真宗为了感谢“天书”降临而设立的一个敬天祭祖节日。不过,该节也有深厚的民俗基础,这就是六月六日作为“重日”,从汉唐以来就具备了一些形成节日的民俗元素,如农业劳作、医学养生以及宗教祭祀等活动;天贶节设立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以祭祀、晾晒、游赏、沐浴、尝新、酿造、养生、回娘家等民俗活动为主要特色的传统节日。但是,天贶节在传统节日中并不算是一个大节,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各地又形成了一些具有本地特色的祝节活动,这样就使得该节的名称五花八门,而天贶节之称反倒逐渐被人们所淡忘,最终导致了该节在近代以来开始衰落,以至到现代民俗中已经基本消失。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