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知大道,必先读史。
先读什么“史”?很多人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当然要选择权威认定的正史,读“二十四史”!
而“二十四史”,由哪部起始?
正是《史记》。
·史学传统与个人天才·
司马谈、司马迁,两代史学家父子相继,将神话中的五帝时代到西汉初年,把近三千年漫长繁杂的历史,整理成一部皇皇巨著。

这部书,是纪传体史书的开端,为后世著史者立下规范。之后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至《清史稿》,都以纪传体编成。
《史记》首创纪传体,以人物为记载中心,其体例分为:
本纪 叙帝王,兼排比军国大事;
世家 记诸侯封国、开国功臣、特殊人物;
表 谱列年爵、事件及人物;
书 (后史皆改为“志”),记载重要典章制度沿革变迁;
列传 记述将相功臣、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少数民族及外国。
全书有五种体例,但核心是纪、传,故该体以此得名。
为何是司马迁首创了这种体裁?在司马迁之前,史书又是以什么体例来书写的呢?
人类发明文字以后,记录事情,最简单的形式,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因此,编年记事,成了较早的史书编撰法。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一些古早史籍,如《春秋》《竹书纪年》,就是依时间顺序进行叙事的。
但是,这些史书,严格说来,更接近于大事记——比较简单,不能全面反映社会活动、重要人物和制度变迁,后人理解起来有难度;第一部叙事完整的编年体史书《左传》出现,内容相对详细,但仍不能全面呈现这些信息。
另外还有一种史书体裁,就是“国别史”,比如《国语》《战国策》。编年体史书依循的是时间顺序,这种体裁,则以空间方位为统摄。
时空维度都有了,接下来就要看,如何把历史活动的核心——人,合理地安插进来。
先秦史官曾编撰过一部书,名叫《世本》,“世”,指世系;“本”,表起源。它是记录家族血缘关系的谱牒,以记帝王、诸侯、卿大夫世系为主,也记录社会生活的一些侧面。该书的“纪”“传”“表”以及“世系”,对司马迁创设五体有直接的影响;对上古时期内容的记载,则成为《史记》重要的材料来源。
再回到司马迁创设的“五体”,如果把“本纪”“世家”和“列传”比喻成一棵大树的话,这三者,就构成了树根、枝条和树叶;“表”,提供了时空框架;“书”,讲的是典章制度,是一种结构性的综述。
这种体例,使得历史记载的范围扩大,人物、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教育……大量内容得以有条不紊地安插于史书的各个部分,系统保存古代文献,便于后人从各个方面查找史料,是史书编纂方式的重大革新。
刘向、扬雄称《史记》:“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司马迁创立纪传体,不愧于“良史之才”的赞誉。

纪传体诞生在司马迁手中,固然离不开他个人的家学、天赋与努力,但也是时代和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纪传体为何诞生于这个时期·
纪传体产生于汉武帝时期,也是时代的必然。经历由分到合、由乱而治,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在汉武帝时期,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包罗全面、博大宏富的纪传体,正是时代之需。司马谈临终,叮嘱儿子写一部表彰“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史书,司马迁撰书,完全继承父志:“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幅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史记·太史公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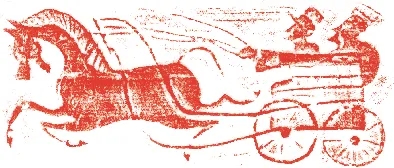
帝王为中心,群臣相辅佐,这是大一统政权以及相应产生的制度在史学领域的必然反映——这也是后世选择纪传体编撰正史的原因。
刘知幾曾评价纪传体:“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短处则是“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没有一种体裁是十全十美的,纪传体的优长和短处相比,实在非常突出。
后世正史出现僵化的问题,更多时候,是操作的人出现问题,就如章学诚所说:“后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则于记注撰述两无所似,而古人著书之宗旨不可复言矣。”
有了体裁的革新,若缺少丰富的材料来源、优秀的材料驾驭能力与高明的著史识见,仍然不足以成就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
《史记》的可贵之处,也在于司马迁对史料严肃审慎的考信精神和忠实于史实的实录态度。
司马迁作《史记》,材料来源非常广泛,有的来自国家收藏的图书档案,有的来自他四处搜访的故老传闻,类似于今天说的社会调查和口述历史。当代学者对《史记》引书之丰富做过查证,仅就今日可见、明确可考者而言,已经相当可观。
换句话说,我们见过的书,司马迁基本都见过;而司马迁曾见过、我们今日无缘得见的书,更是不知有多少!更遑论,“重回现场”访问故旧的条件,我们不具备,司马迁具备。
所以,如果读《史记》的时候,遇到暂时查不到书面来源或考古佐证的部分,就断言这是司马迁的“合理想象”乃至“主观臆断”,甚至进一步贬低《史记》的价值,岂不正是暴露了自己的草率与浅薄?
同时,司马迁对文字材料进行了全面认真的分析、核实,去伪存真,又以对人和历史关系的高度理解,流露了明确的褒贬态度。《史记》高超的文学成就,是来自司马迁大史学家、文学家双重素养的加持,让它易于接受,广为传播,更不应该成为《史记》被攻击的理由。

·“双璧”交汇处,更要看《史记》·
从《史记》开创纪传体以来,两千年来,官方一直延续这个做法来编纂正史,为什么到了北宋时期,又出现了《资治通鉴》这样的编年体巨著呢?
原因就在“资治通鉴”这个书名本身——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主编司马光曾明述编书初衷:史书文字繁多,人主日理万机,无暇通览。所以,他选取历代史书中,关系国家盛衰、生民休戚的部分,以编年体方式,为皇帝“量身打造”一份治国教材。
既然是教材,怎么选用原始材料,如何划定时间范围,决定详略轻重,主编的眼光就非常关键了。
我们现在说《通鉴》记载了长达1362年的历史;相比之下,这个时间跨度,比上起黄帝、尧、舜,共写了将近三千年历史的《史记》,要短不少。
对比一下,就可发现,《史记》《通鉴》,有从战国至汉武帝时期三百余年的历史交汇,《通鉴》有关这段历史的资料,大多来自于《史记》。
《通鉴》始自后世所谓“三家分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周威烈王姬午首次分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国君。
“三家分晋”,主要是指瓜分传统上属于晋国、但实际上早已被强势卿大夫控制的土地,因为晋国早在一百多年前,也就是晋顷公(前525—前512年)时,就已经是“晋益弱,六卿皆大”。
这是一个渐进长期的过程,在《史记·晋世家》能够清楚地看到。但是在司马光的叙事宇宙中,特别挑选了“三家分晋”的尾声——周天子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国君这个事件点,来作为全书开端,强调天子不可自坏规矩、崇奖乱臣,借此提醒当朝皇帝维护“礼”与“名”的重要。
“三家分晋”的描述,主要是在《史记》的《晋世家》《赵世家》中完成的,《韩世家》《魏世家》也有谈及。仅读《通鉴》,会留下赵为乱臣贼子的印象。《史记》,作为《通鉴》的重要来源,提供了更全面的背景与丰富的细节。

△三家分晋示意图
《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总结了写《赵世家》的原因:“嘉鞅讨周乱,作《赵世家》第十三。”对于赵国的奠基者、当时仅为晋臣的赵简子讨平周朝叛乱,帮助周敬王打回都城,司马迁表示赞许。《十二诸侯年表》中,记下晋顷公十年,“知栎、赵鞅内王于王城”。
通读《赵世家》,我们才能了解,赵的祖先也是名门望族,曾对晋国有过大功,因此,赵最后晋升为诸侯,并非凭空篡夺,而是存在一定的历史合法性。
司马光根据“资治”的主旨,有时会对史料真伪、取材进行一些处理,朱熹对此就有过批评,明人娄坚提出,读“秦汉而下讫于五代之季”的历史,“必先求之正史而参以司马氏之《资治通鉴》,错综其说而折衷之”。如此,才能在价值判断引导的书写之外,看到更丰富、更本原的历史面貌。

作为正史发端的《史记》,既在体裁上有开创纪传体之功,又在文学高度与史学成就双方面达到“二十四史”的至高之处,还是编年巨著《通鉴》的重要来源,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值得我们尽早去读;尤其难得的是,《史记》还是一部百科全书,从各个角度进入它的世界,都如入名山宝库,能看到目不暇接的奇观。
源正,则流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