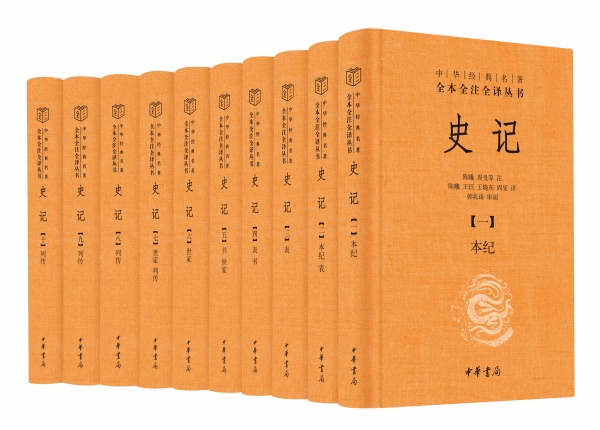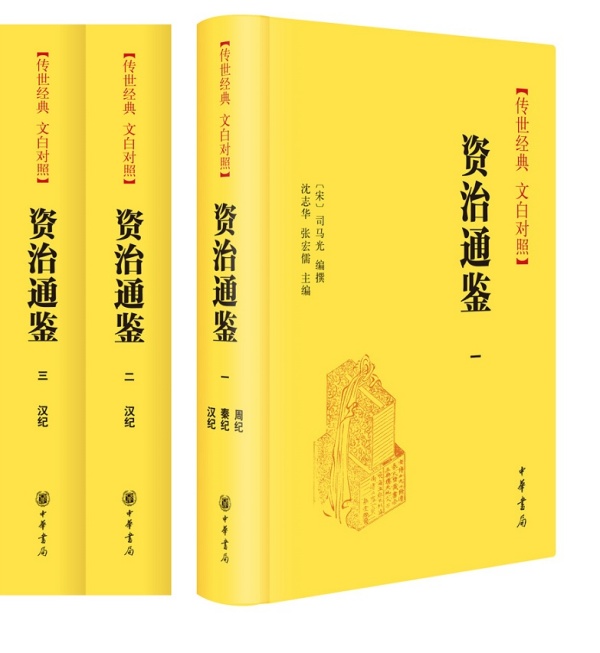无论在直播间还是在公号后台,这个提问出现的频率都很高。
确实,《史记》《通鉴》,书,并称史学双璧;著书者,合称史家二司马。
成就同样举世瞩目,地位同样举足轻重,无论能沉下心来读进去哪一部,对人的能力、文笔、眼界、格局提升,都是作用巨大的。
但是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必须做出一个先后选择的话,三全君的建议是:
先从《史记》读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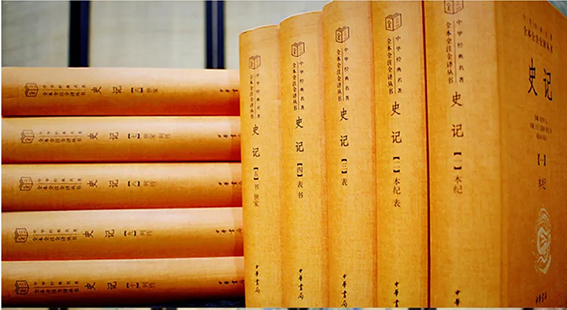
原因可以列出很多,但是中心点,其实正在于《史记》《通鉴》体裁的不同:
一个是纪传体,一个是编年体。
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编年体,以时间为线索。
再收拢,则归于一个字:
人。
人,怎样看待人,怎样看待由人组成的历史?
如果把看历史这件事,比喻成镜头语言的话,同样一段历史,导演要怎么在有限的条件内,展现出他对于万般熙攘兴衰荣枯生灭的理解?
纪传体,是聚焦在个体的身上,让镜头跟随这个人的活动、选择、摇摆、遭逢,以小见大,铺排出更多有关时代、有关命运的画卷;而聚焦于哪些“人”,他的事迹生平如何安排详略删削,就完全体现出导演的褒贬与判断。
编年体,是把镜头拉远,让无数个体的运动轨迹,交叉融汇成一条长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运动轨迹,但服从于时间的逻辑,时隐时现;每一件事有它自身的演进速度,但同样服从于时间的流动秩序,或明或暗。人与事在时间长河中的浮与沉,共同指向“鉴往知来”这一读史的终极目的,也即,从纷乱变易中,寻找相对固定的规律。
回到两部书本身,《史记》的著作宗旨里有一句话:“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呕心沥血独立著成这样一部鸿篇巨制,融入了个人毕生的学识、心血与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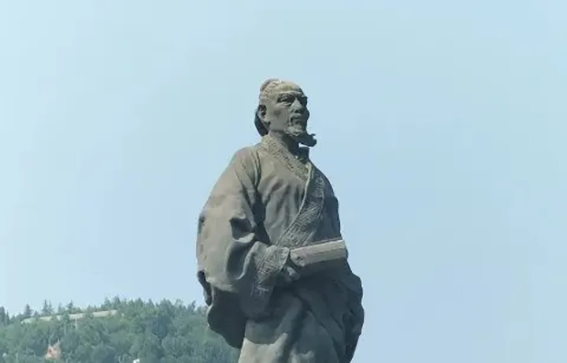
而《资治通鉴》,是由司马光担任主编,多人协作完成,面对北宋的内忧外患,司马光希望通过史料的合理剪裁,为统治者提供治国经验,因此,更注重实用理性,讲求“有资于治道”。

于是,同样的一个人,一件事,在《史记》和《通鉴》里,处理的方式就不一样了。
我们之前循着梁启超先生推荐《史记》十篇的路线,给大家做过《史记》的展示。
同样,我们也可以此为出发点,比较一下《史记》和《通鉴》的讲述方式。
就拿十篇中的《李将军列传》来说。

汉武帝时期的名将李广,是司马迁特别偏爱、投入大量情感的人物;《李将军列传》,也是《史记》文学价值相当高的名篇。
这一篇的第三部分,讲到李广晚年随卫青伐匈奴,被倾轧、逼迫至死。
其中,元狩四年(前119),李广被武帝、卫青徇私由前将军调往东道,最后因迷路失期,被逼自杀之事,尤其令人唏嘘——卫青要调走当时担任前将军的李广,好把建功的机会留给公孙敖。李广对此心知肚明,带着情绪执行军令,结果迷路,错失军机。
司马迁随后用十几个字交代了卫青遇到了什么事情:
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
什么意思呢?卫青与单于开战,单于发觉形势不利,撤军逃跑,卫青没能抓到单于,只能回来。
接着,司马迁记述了李广被责令听候审讯,愤而自杀的经过。
而在《资治通鉴·汉纪》里,元狩四年,可不止发生了这一件事:
一开篇,先是汉武帝推行的一系列重要经济举措:制作皮币、重用桑弘羊;盐铁专营,推行“算缗”;重赏为国捐产的卜式。接着,记载天有异象。然后,讲到李广的遭遇。随后,是卫、霍打击匈奴,武帝重用酷吏,少翁装神弄鬼……
就在李广和卫青发生冲突这个关键点之后,《通鉴》详细记录了卫青遇到了什么:
大将军出塞千馀里,度幕,见单于兵陈而待。于是大将军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匈奴亦纵可万骑。会日且入,大风起,砂砾击面,两军不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强,自度战不能如汉兵,单于遂乘六骡,壮骑可数百,直冒汉围,西北驰去。时已昏,汉匈奴相纷拿,杀伤大当。汉军左校捕虏言,单于未昏而去。汉军发轻骑夜追之,大将军军因随其后,匈奴兵亦散走。迟明,行二百馀里,不得单于,捕斩首虏万九千级,遂至窴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留一日,悉烧其城馀粟而归。
比起《史记》的一笔带过,要详细得多。
所以,寥寥“弗能得而还”数字的背后,卫青其实打了相当漂亮的一仗!
更有意思的是,《通鉴》这段话的来源不是别处,正是《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这就是司马迁的用心所在,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互见”手法:《李将军列传》的主角就是李广,其他人的相关情节,在合适的地方再行安排;卫青的战功如果放在这里,横生枝蔓,不免冲淡李广的悲剧色彩。
如此处理,读者的目光,方能始终跟随着高明的史家笔法,缠绕在李广身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李将军,才能引起后世无数不得志者的长久共鸣。为李将军下涕者,从此远不止司马迁一人。
有类似遭遇、相似个性者,读到这里,往往情感上触发巨大震动,从而展开联想:
究竟李广不得封侯,是个性的原因,还是时代的问题?
在他的故事里,卫青、武帝等等,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他的结局如此惨烈,是不是在早期,就已经出现了危险端倪?
如果我是李广,从哪一刻开始改变做法,能够扭转命运?
再由李广这个人向外延伸,就可以触及汉武帝对匈奴作战的各个层面,包括人员调度、战功奖惩、钱粮保障……
就像在长河之中,找到小舟一叶立足,远眺近察,便有了据点;至少,在这一段,再怎么波浪翻天,也不会目炫神昏。

两书的差异,不仅源于纪传体、编年体体例之别,更反映作者对著史的不同理解:《史记》,是人性的史诗;《通鉴》,是治国的镜鉴。
所以,出于这个考虑,在同样伟大的《史记》和《通鉴》之间,我们推荐优先读《史记》。
这就是因为,读历史的,是人。
人,天然就对人的活动、人的选择、人的命运、人的结局,更感兴趣,更加留心,更容易调动情感,从而形成深刻的记忆。
这遵循人的一般认知规律:由己及他,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由情及理。
愿每一位爱读历史的人,不论是从《史记》读起,还是从《通鉴》读起,都能读出专属于自己的心得体悟,殊途而同归,达到通透澄明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