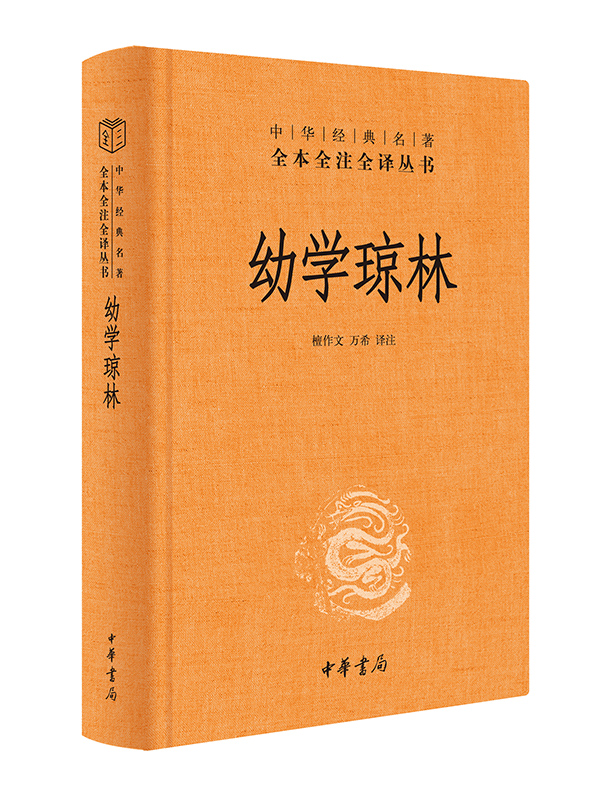编 者 按
近日,我们收到青年学者宋超的来稿,他深耕于传统文化研究领域,以自己扎实的专业知识,介绍了“三全本”《幼学琼林》的精妙之处。我们衷心感谢宋超先生的分享,今天特将这篇文章予以发布,希望大家借此走进《幼学琼林》,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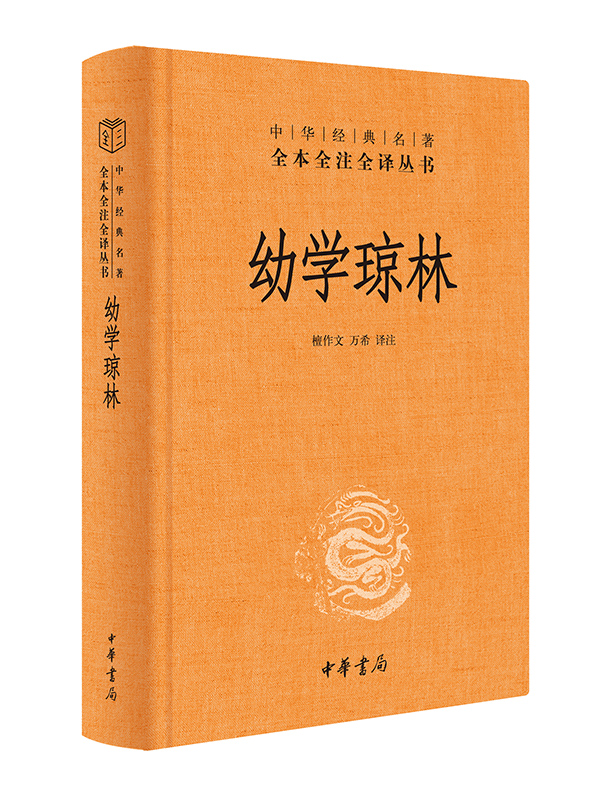
《幼学琼林》一书编著于明末清初。成熟的科举制度,兴起的出版行业,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流传广泛的童蒙读物。还有如《笠翁对韵》《声律启蒙》《古文观止》,这类书籍原本是为科场应试服务的。随着科举退出历史舞台,以及“五四”白话运动的兴起,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重新看待传统文化,这类童蒙书籍反而受到了更大的关注。人们读古书的能力下降了,对传统童蒙读物却更为重视,这本身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
在同时代的童蒙读物里,《幼学琼林》可谓是极难读的一本。
中国自古就有掌故之学。就古人而言,作诗要用典,作文要为古人立言,诗文好就有机会做官,被古人视为最大的人生出路。就古代国家和社会而言,传统价值观念牢不可破,万事万物都有故事成例可以因循。
因此《幼学琼林》的优点在于内容上每条字句均有出处,在形式上又要讲求韵律对仗,耐得住细读细品。思想上虽无法跳出传统的人伦纲常,篇章也要符合“天地君亲师”的排序,但好在包罗天文地理、饮食宫室、鸟兽花木,阅读价值远在那些规训行为的说教作品之上。好比是一座古代宫殿,左右对称,比例和谐,上有黄瓦,下有青砖,雕梁画栋绘舞凤飞龙,殿堂廊柱列君臣文武。在古代,这宫殿的每一处细节都体现着等级森然,而在今天人们看来却又多为文化遗留的瑰宝结晶。
因其丰富的内容,《幼学琼林》对注释整理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可以想见,在该书的创作过程中,作者应是广泛借鉴了包括类书在内的各种古籍。作者能够协调杂乱的文本信息已是难事,而对每处典故的出处考证,不仅是力有未逮,也是没有必要的。这就造成了该书内容里面正经正史与野史笔记的杂糅共存。如《天文》篇讲“云从龙,风从虎”本自《周易·文言上》这是重要的先秦文献,而上面一行“夏时大禹在位,上天雨金;《春秋》《孝经》既成,赤虹化玉”的两条文字又是汉代以后的附会之说,用这种内容讲述早期历史,可信程度自然要大打折扣。
原书作者受限于时代,是没有严格甄别故事材料的。如今文献整理者重新核对解释每一条故事的文献来源,正是要后出转精,对传统文化也是大有裨益的。这一工作必须由对古代文献有着极深厚功力的学者方能胜任。长期以来,市面上出现了诸多《幼学琼林》的注译版本,其中多有谬误,甚至闹了不少笑话。有学者将这些错误归结为四类:不通史实,不通文意,不通文法,不通事理。谬本流传于世,难免会误人子弟。
以我有限的目力,中华书局2023年出版的三全本《幼学琼林》可以说是目前该类书籍中,注释最详,考辨最精的一个版本,极大地弥补了过往的种种缺憾。

三全本《幼学琼林》的注译工作由檀作文、万希两位老师承担,注释译文中能够体现出学术性的考辨是很不容易的。如《花木》篇中对于郭林宗 “冒雨剪韭”一事的质疑。这则东汉人物故事,注释者遍查诸书,发现最早的文本来源是宋代苏轼所注的杜甫诗作。然而该诗应是伪托之作,却经过苏轼注释在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所以这则故事最早应是来源于宋人。如此,我们在阅读注释的同时,也了解到了古代知识的形成与传播。文献整理工作是一门科学,要讲究证据。如《人事》篇“破麦、破梨,见夫见子之奇梦”,整理者并没有找到任何相关记载,但是版本旧注里讲述了一段宁波妇人的奇闻,整理者便老实地将已有旧注内容详录,以待后学。这些都是具体条目中把握分寸,值得赞赏的工作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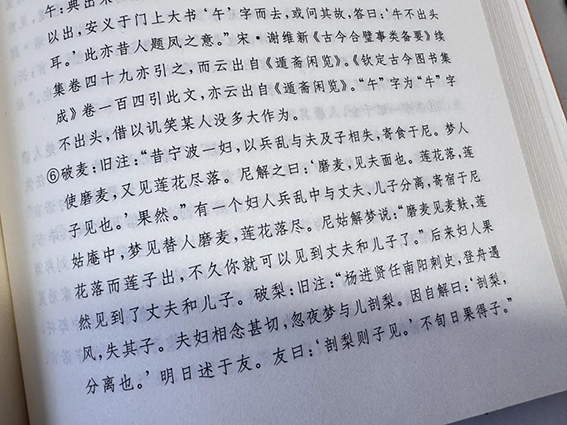
书名虽号“幼学”,但有了三全本的注释版本,不仅更好读,更好懂了,也提高了相应的学术价值。
我认为该书不仅适合传统文化的爱好者,对于刚刚就读文科专业的在校学生,也有着极高的阅读价值。正文字句凝练,对仗生动,而注释部分体例完备,引用的正经正史、名家名篇、野史笔记,几乎涉及到了古代典籍的方方面面。大学课程长期以来,都有重视通论讲授,轻视亲自翻书的老毛病。而三全本的《幼学琼林》为我们翻阅浩如烟海的传世古籍,提供了不少趣味性的线索。更何况书中原本的不少生僻典故,对于今天的专业研究者也会感觉到非常陌生。深者读时不觉浅,浅者读来不觉深,方是匠心独具之处。
有人说《幼学琼林》是古代儿童的“小百科”,为百科做注释自然有许多细节可以进一步讨论。我冒昧地以末篇《花木》的两条举例。
一条是注释方面,“竹称君子”注释部分认为此条“语本明·王阳明《君子亭记》”然而从《诗经·淇奥》的“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到东晋王徽之“何可一日无此君”,再到北宋初年陶谷诗“高节凌空君子竹”。“君子竹”至晚在宋代已是习语,明代小说演义中多有提及,似乎不宜认为出于王阳明。《幼学琼林》一书有明显的朱子学倾向,不仅由于学派门户,更是作为童蒙读物,必须要与科举教材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保持内在理路一致。当我们论述某典故出自明代同时期的文献,尤其是出自阳明学派时,论述可能要更为慎重。
另一条是译文方面,“越王尝蓼,必欲复吴之仇”译为“越王勾践用辛辣的蓼草熏眼提神,决心要灭吴报仇”。译文内容可能是考虑到《吴越春秋》讲勾践“目卧,则攻之以蓼”的相关记载。但是,《吴越春秋》对于“攻之以蓼”并没有进一步解释,是食用、是涂抹,还是烧熏,似乎都没有更为直接的证据。既然是译“尝蓼”,或许还是译为“食用蓼草”可能更妥当些。
无疑,三全本的出现是《幼学琼林》整理工作四十多年来的一个重要进步。对于传统童蒙教材,在当下的社会要不要读?怎么读?读哪本?每个问题都是颇具争议的话题。我们的认识也是在时代的曲折中不断变化前进。不过,这些讨论都至少要建立在注释准确,译文严谨的文献整理工作之上。希望此类的工作不要止步于眼前,而是精益求精,在未来推出更为精准的注释译文,供大家学习参考。
欢迎更多的学者参与到“三全本”的注译工作中,也欢迎广大读者来稿发表对三全本的评价、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