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本《道德经》自2021年5月出版以来,销量已达72万册,收获一致好评。相信入手这本书的朋友,已经了解了这个版本的独特优势。而还没入手的朋友,或许会好奇它究竟好在哪里。
这一版《道德经》突破“三全”体例,在大多数章节后增加了解读内容,并且通过列举诸多生动鲜活的事例,使原本晦涩的道理变得浅显易懂。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以“书花”的形式,依照不同主题,为大家全方位展示三全本《道德经》的精彩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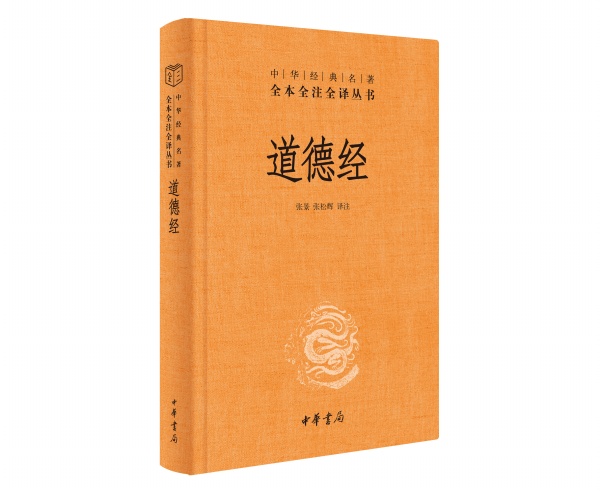
无 为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三十七章》)
【解读】
老子认为,君主如果能效法大道,坚持无为政治,自然也能把国家治理好。西汉中期以前的政治情况类似老子所描述的这一过程。《汉书·食货志四上》记载:
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伯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
从汉初到汉景帝刘启,一直执行无为政策,终于摆脱了“人相食,死者过半”的困境,使国家经济繁荣起来,有吃不完的粮食和花不完的金钱,确实达到了“无不为”的程度。这就是老子说的“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汉武帝凭借这一国富民强的基础,欲望膨胀起来,他对外用兵,对内改制,忙忙碌碌,真可谓“化而欲作”。可惜的是,此时老子早已去世,无人去“镇之以无名之朴”。汉武帝数十年的“多为”,使中国再次陷入“天下虚耗,人复相食”、户口减半、义军蜂起的混乱局面,“无不为”的大好局面被“多为”给葬送了。
武帝晚年面对破败不堪的局面,开始自我反省,认真悔过,颁布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深陈既往之悔。……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汉书·西域传下》)。武帝再次恢复文景时期无为而治的政策,使国家逐渐安定下来。这就是老子说的“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四十八章》)
【解读】
本章提出“无为而无不为”的命题,意思是只有做到了清静无为,才能做成一切事情。“无为”就是要求人们做事时顺应客观规律,不可掺进私心私意而去妄为、多为。到了唐代无能子时,他又赋予这一命题新的解释,这一解释可以作为我们常人的座右铭。无能子认为:“只有那些能够做到清静无为的人,才能够去承担一切事务;主观上有所作为的人,有些事情就不会去做。因此只有那些具备了最真实天性的人才懂得永恒的大道,只有大公无私这种思想才接近清静无为,因为这些人本来就不存在欲望和私心。”无能子的意思很清楚:只有做到了清静无为,才能够去承担一切应该承担的事务(无不为)。所谓的“无为”,就是顺应外物而为。换句话说,就是根据客观情况,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也即无能子说的“宜处则处,宜行则行”。相反,如果需要我们去干某事的时候,而我们不去干,那就是没有做到“无为”了。而“有为”的人就不同了,“有为”的人主观目的性非常明确,与主观目的无关的事情就坚决不会去做。比如以科举考试为目的的人,就不愿去务农经商;反过来,以经商赚钱为目的的人,就不愿去花工夫舞文弄墨了。
人生在世,不可能事事如意。我们想做某一个工作,但这个工作未必就需要我们;我们想做某一件事情,但这件事情未必就一定能够做成功。当我们无法改变客观环境的时候,就应该调整心态,勇敢地改变我们自己。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
【解读】
在中国古代,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一个社会的风气好坏,民众的品德高低,关键取决于领导者。关于这方面的实例,我们仅举一个:
齐桓公喜欢穿紫色衣服,于是全国臣民都跟着穿紫色衣服,结果导致紫色衣服价格飞涨,五匹白色布都换不到一匹紫色布。齐桓公对此忧心忡忡,就对管仲说:“我喜欢穿紫色衣服,紫色衣料就变得特别昂贵,全国民众都喜好穿紫色衣服而且没完没了,该怎么办呢?”管仲说:“您如果想制止这种情况,为什么不试着自己先不穿紫色衣服呢?您就告诉身边人说:‘我非常讨厌紫色衣服的气味。’这时候有穿紫色衣服的侍从走到您的跟前,您一定要对他说:‘你往后退一点,我讨厌紫色衣服的气味。’”齐桓公说:“好。”就在当天,宫中的郎中没有谁再去穿紫色衣服了;到了第二天,都城中就没有人再去穿紫色衣服了;到了第三天,齐国整个境内就没有人再去穿紫色衣服了。
治大国若烹小鲜。(《六十章》)
【解读】
“治大国若烹小鲜”是千古名言,这一治国观念起源很早,《诗经·桧风·匪风》说:“谁能亨(烹)鱼?溉之釜鬵。”意思是说:“谁善于煎鱼,我愿意为他帮忙洗锅。”《毛传》解释说:“亨鱼烦(经常翻动)则碎,治民烦则散。知亨鱼则知治民矣。”《韩非子·解老》说得更为清楚:“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宰,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治大国若烹小鲜”的主旨仍是清静无为,要求统治者保持政令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可朝令夕改。
历史上最不懂得“治大国若烹小鲜”这一道理,以至于把国家折腾灭亡的当属王莽。王莽篡汉当上皇帝后,凭借西汉遗留下来的强大国力,企图通过恢复西周制度来达到平天下的目的,于是开始推行一系列新政,史称“王莽改制”。主要有:将天下土地改名“王田”,以王田制为名恢复远古时代的井田制;奴婢改称“私属”,与王田一起均不得买卖;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把盐、铁、酒、铸钱及山林川泽收归国有,施行五均六筦的经济政策;降低周边异族国家的等级并给予羞辱性的称号,如更名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改高句丽为“下句丽”等。史学家称“王莽‘好’改变制度,政令‘烦多’,朝令夕改,不讲功效,故变得快,吹得也快,花样多,收效小”(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四卷)由于王莽的这些政策只求符合古制,悖逆社会现实,引起国内外民众的一致反对,结果仅仅十多年时间,就把自己辛辛苦苦建立的新朝彻底葬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