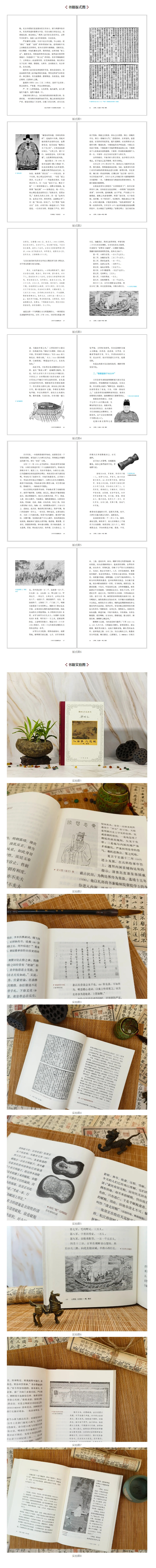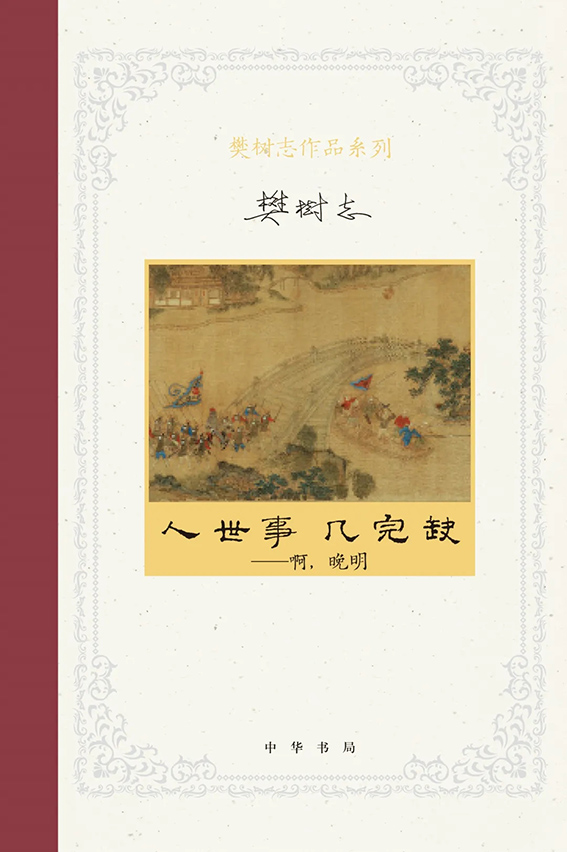
史学名家樊树志教授,用十余篇代表性文章、六十余图,多角度呈现晚明大变局视野下的政治与文化生态,细腻梳理张居正、徐阶、吴伟业等官绅名贤的仕宦与心路历程,是公务员、教师、都市读书人、历史爱好者的优秀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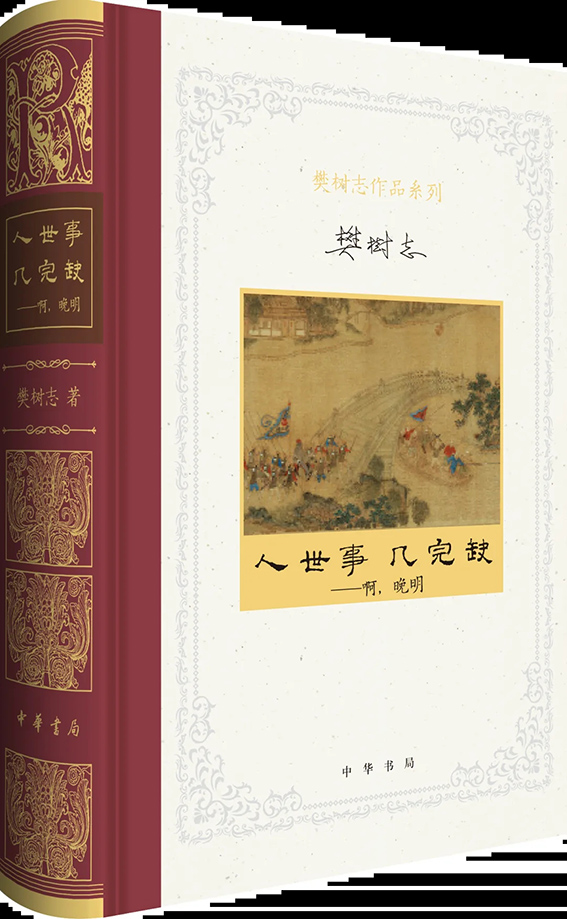
孜孜不倦的耄耋学者。樊树志先生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出版著述甚多,并多次获得大奖,久为社会和广大读者熟知。今年已届米寿,仍孜孜不倦地研究明史,尤其是晚明史,传播新知卓见。
续证晚明大变局。樊教授自2015年以来,破除陈见,首次系统论述“晚明大变局”,将中国卷入全球化的时间提早到晚明,引发学界和社会广泛关注与讨论。本书是继《晚明大变局》等书之后继续解读这一真知灼见的新作,重点从明朝内部、明朝对外战争等多个角度切入,异彩纷呈。
剖析晚明政治生态。本书细腻解读了晚明大变局的内因,尤其是明朝政治生态持续恶化的过程,以及不同政治派别或利益群体之间角逐的荒诞面相。如书中所收《魏忠贤崇拜面面观》长文,层层剥茧式地揭露魏忠贤个人崇拜运动的真相,展现了当时举国若狂的政治腐败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揭示晚明独特的文化生态。文人结社始于嘉靖,在天启、崇祯年间达到高潮。书中从文人结社视角,来探究晚明独特的文化生态。在阳明学引发的思想解放潮流影响下,部分文人在一起磋商学问的同时,更关注现实的政治问题,探寻解决之道。樊教授以最具代表性的几社、复社为例,详述这些文社的成立经过及其主要活动,展示了他们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的经世情怀,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勾勒晚明名贤浮沉群像。书中涉及徐阶、张居正、杨涟、左光斗、魏大中、文震孟、郑鄤、倪元璐、吴应箕、黄道周、刘宗周、吴伟业等官绅名贤,勾勒这些正人君子在时代激流中浮沉,波澜起伏,曲折坎坷,折射出历史的复杂性,显示历史本身的丰富多彩。
本书收录史学名家樊树志教授近十余年间所撰有关晚明史的要文十三篇,既娓娓解读了晚明重要历史事件和社会现象,如万历年间的朝鲜战争、六君子之狱、魏忠贤崇拜运动、文人结社等,又剖析了晚明著名文人士大夫,如徐阶、张居正、文震孟、郑鄤、倪元璐、吴应箕、黄道周、刘宗周、吴伟业等人的仕宦与心路历程,这些主题几乎涵盖了晚明史的重要方面。
书中配有六十余幅图片,包括人物肖像、书画作品、典籍书影、档案资料及其他历史遗物等多种类型,以期形象生动地还原历史场景,图文相彰,是研读晚明史乃至明史的优秀读本。
“人世事,几完缺”,选自清吴梅村《贺新郎·病中有感》,最能代表耄耋学者樊教授数十年研究晚明史的感慨心境。

樊树志,复旦大学教授。代表著作有:《江南市镇的早期城市化》(2023)、《明史十二讲》(2021)、《图文中国史》(2020)、《重写晚明史:王朝的末路》(2019)、《重写晚明史:内忧与外患》(2019)、《重写晚明史:新政与盛世》(2018)、《重写晚明史:朝廷与党争》(2018)、《晚明大变局》(2015)、《明代文人的命运》(2013)、《明史讲稿》(2012)、《张居正与万历皇帝》(2008,2022)、《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2007)、《国史十六讲》(2006)、《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2005)、《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2004)、《晚明史(1573—1644年)》(2003)、《国史概要》(1998)、《崇祯传》(1997,2021)、《万历传》(1993,2020)、《明清江南市镇探微》(1990)、《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1988)等。其中,《晚明史(1573—1644年)》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晚明大变局》入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新华网、新浪网等二十余家媒体2015年度好书。
王阳明与晚明思想解放潮流
高处不胜寒
——内阁倾轧中的徐阶
一、从夏言“弃市”说起
二、谨事严嵩,虚与委蛇
三、潜移帝意,扳倒严嵩
四、天下翕然想望风采
五、新郑鱼肉华亭
“好申韩法”的张居正
一、“经术”与“法术”
二、“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
三、“今之从政者大抵皆然,又不独学校一事而已”
四、“不加赋而上用足”
五、“威权震主,祸萌骖乘”
1590年代的朝鲜战争
一、“假道入明”的“大东亚构想”
二、“朝暮望救于水火中”
三、“爰整六师,大彰九伐”
四、“就其请贡行成之机,可施调虎离山之术”
五、“秀吉妄图情形久著,封贡亦来”
六、“授册封贡,可保十年无事”?
七、“战端再起,戛然而止”
六君子之狱
一、杨涟:“生杀予夺岂不可以自主,何为受制幺麽小竖?”
二、臣工“先后申疏”,“无不危悚激切”
三、叶向高调停弥缝,进退失据
四、官场大清洗
五、杨涟:“仁义一生,死于诏狱”
六、左光斗:“辱极苦极,污极痛极,何缘得生”
七、魏大中:“臣子死于王家,男儿常事”
八、“虎狼之肆威,狗彘之不食”
魏忠贤崇拜面面观
一、“奢侈性成,服色僭制”
二、无上名号:“九千九百岁爷爷”
三、“遍地立祠,设像祝釐”
四、“九千九百岁”之死
文人结社与晚明文化生态
一、关于文人结社之风
二、“济世安邦”的几社
三、作为文社联合体的复社
四、对复社的“谤”
五、“朝廷不以语言文字罪人”
悲情的骨鲠之士
——文震孟与郑鄤
一、“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
二、“当为朝阳之鸣凤,不当为抱叶之寒蝉”
三、“正直而遭显戮,文士而蒙恶声”
为正人增华,为文人吐气
——倪元璐的才情与气节
一、引言
二、持论侃侃,中立不阿
三、力陈销毁《三朝要典》
四、“三做堂”:实做、大做、正做
五、君亡与亡,以身殉国
“半世文章百世人”
——复社名士吴应箕
一、“朝廷不以语言文字罪人”
二、触及时事的史论与策论
三、《留都防乱公揭》始末
四、“半世文章百世人”
“朝廷舍臣,非臣舍朝廷”
——黄道周的坎坷仕途
一、讥刺阁臣周延儒、温体仁,削籍为民
二、与皇帝当廷辩论,降六级调外任
三、贬谪·囚禁·廷杖·流放
四、“有殒自天,舍命不渝”
“一代完人”刘宗周
一、“奈何以天下委阉竖”
二、“八年之间谁秉国成而至于是”
三、“厂卫是朝廷私刑”
四、“决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
“人世事,几完缺”
——读《梅村家藏稿》札记
一、“福过其分,实切悚栗”——权臣倾轧中的复社才子
二、“立朝以正直忠厚为本”——从翰林院到南京国子监
三、“山川之胜,文章之乐,生平所未有”——红颜知己卞玉京
四、“通侯青史姓名高”——缅怀杀身成仁的瞿式耜
五、“草间偷活”,“一钱不值”
后记
崇祯四年(1631),二十三岁的吴伟业,以会试第一名、殿试第二名的佳绩,获得皇帝御批“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嘉奖,钦赐假期,归乡婚娶,一时荣耀至极。康熙十年(1671) 病危时,回顾六十三年生涯,感慨中透着凄凉:“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实为天下大苦人。”名闻遐迩的梅村先生为什么要说自己是“天下大苦人”呢?晚年有一所颇具江南园林风格的别墅,生活并不艰苦。其实是内心痛苦,灵魂煎熬之苦,一再写诗感叹:“憔悴而今困于此,欲往从之愧青史。”他在临终前要再三叮嘱,给他穿上僧装,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不要写墓志铭。后辈顾湄为他写“行状”至此,感叹:先生之心事可悲也!这又是为什么呢?
《梅村家藏稿》向后人透露的信息丰富多彩,既要面对金戈铁马的腥风血雨,又要面对进退出处的艰难抉择,透过这样的视角洞察明清鼎革之际江南的政治氛围与文化生态,或许别有一番意味。
一、“福过其分,实切悚栗”—权臣倾轧中的复社才子
1. 张溥的入室弟子
吴伟业天资聪明,少年即有才名,张溥见到他十四岁所写的文章,大为惊叹,“文章正印,在此子矣”,随即收他为入室弟子。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说:“先生有异质,少多病,辄废学,而才学辄自进,迨为文,下笔顷刻数千言。时经生家崇尚俗学,先生独好三史。西铭张公溥见而叹曰:‘文章正印,其在子矣。’因留受业,相率为通经博古之学。”陈廷敬提供了一个细节:“(吴梅村) 先生少聪明,年十四能属文。里中张西铭先生以文章提倡后学,四方走其门,必投文为贽,不当意即谢弗内。有嘉定富人子,窃先生塾中稿数十篇,投西铭。西铭读之大惊,后知为先生作,固延至家。同社数百人,皆出先生下。”
此处所说的“同社”云云,指应社与复社。应社成立于天启四年(1624),创立者是杨廷枢和张溥等文士,宗旨是提倡尊经复古。张溥后来回忆道:“应社之始立也,所以志于尊经复古者,盖其志也。是以五经之选,义各有托,子常杨彝、麟士顾梦麟主《诗》,维斗杨廷枢、来之吴昌时、彦林钱旃主《书》,
简臣周铨、介生周钟主《春秋 》,受先张采、惠常王启荣主《礼》,溥与云子朱隗则主《易》。”之后张溥创建复社,影响远超应社,由一个地域性文社,发展为全国性文社。因此,复社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是指众多文社之一,后者是指众多文社的联合体。朱彝尊说“复社始于戊辰,成于己巳”,就是这个意思,亦即复社作为众多文社之一,始于崇祯元年(1628) ;作为众多文社的联合体,成于崇祯二年。

吴伟业作为张溥的及门弟子,追随老师参加复社活动,研习经学,奠定坚实的学问基础。复社的早期名单中,年轻的吴伟业赫然在列。崇祯二年(1629)的尹山大会、崇祯三年的金陵大会,他都躬逢其盛。关于尹山大会,《复社纪略》写道:“吴江令楚人熊鱼山开元,以文章经术为治,知人下士,慕天如名,迎至邑馆……于是为尹山大会,苕、 霅之间,名彦毕至。
未几,臭味翕集,远自楚之蕲、黄,豫之梁、宋,上江之宣城、宁固,浙东之山阴、四明,轮蹄日至。”张溥在大会上针对“士子不通经术”的习气,提出“规条”与“课程”,以期达到“兴复古学”“务为有用”之目的,道出了之所以命名为复社的原因。吴伟业在《复社纪事》中说:
初,先生起里中,诸老生颇共非笑其业以为怪。一时同志,苏州曰杨维斗廷枢,曰徐九一汧,松江曰夏彝仲允彝,曰陈卧子子龙;而同里最亲善曰张受先采,读书先生七录斋,海内所目为娄东两张者也。受先举戊辰会试第三人,九一进史馆,是为崇祯改纪之初年。先生以贡入京师,纵观郊庙辟雍之盛,喟然太息曰 :“我国家以经义取天下士,垂三百载,学者宜思有表章微言,润色鸿业。今公卿不通六艺,后进小生剽耳佣目,幸弋获于有司……诗书之道亏,而廉耻之途塞也。新天子即位,临雍讲学,丕变斯民。生当其时者,图仰赞万一,庶几尊遗经、贬俗学,俾盛明著作,比隆三代,其在吾党乎?”乃与燕、赵、卫之贤者为文言志,申要约而后去。
参加尹山大会的人数之多,一般文社难以与之比肩。日本学者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统计,一共有六百八十人。崇祯三年(1630),适逢应天乡试,江南士子前往金陵参加科考,复社成员吴伟业和杨廷枢、张溥、吴昌时、陈子龙等高中举人,复社声誉一时高涨。在这种背景下,张溥在金陵召开第二次大会。吴伟业写道:“三年庚午省试,胥会于金陵,江淮宣歙之士咸在,主江南试为江西姜燕及(曰广) 先生。榜发,维斗褒然为举首,自先生以下,若卧子及伟业辈,凡一二十人,吴江吴来之昌时亦与焉,称得士。”
2. 天子门生 :“正大博雅,足式诡靡”
荣耀接踵而来。崇祯四年(1631) 辛未会试,吴伟业考取第一名,座主是内阁首辅周延儒和内阁次辅何如宠。接下来的殿试,获得了一甲第二名(第一名是陈于泰)。他的答卷自然引人注目,这篇《辛未廷试策》确实不同凡响。
一则说:“臣闻之:人主之立法也,知明意美,道高德厚,设诚于内,而制行之,仁义礼乐皆其具也。然非选温良上德之士,以因能而责治,经常何自而修焉?”
再则说:“人主之立法也,事为之制,曲为之防,随俗之宜而通变之政,文章皆其效也。然非举通道进善之人,以分职而效官,典章何自而备焉?”
三则说:“故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使教化自内以达外,道法自略以及详,则智者献明,能者效力,皆从此始也。”
四则说 :“君之所以养士者禄也,厚其爵予以彰有德,则冀念不生,所以成养廉之德至矣。而风气未更,其何以劝焉?惟以贵谊贱利为先,而见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廉法所自见也。”用科举考试的标准来衡量,堪称言之有物的佳作,录取为会试第一名、殿试一甲第二名,应在情理之中。由于内阁中排名第四的温体仁与内阁首辅周延儒的权力倾轧,引出了麻烦。温体仁的亲信党羽薛国观在朝廷中散布流言蜚语:周延儒意欲收罗名士,秘密叮嘱各分房考官,在阅卷时拆封窥探考生姓名。分房考官李明睿录取旧交吴禹玉之子吴伟业,周延儒也喜欢吴伟业,因此录取。御史袁鲸根据流言蜚语,准备向朝廷揭发。周延儒抢先一步,把吴伟业的考卷呈送皇帝御览,朱由检阅后批示 :“正大博雅,足式诡靡。”皇帝明白无误的赞誉,令温体仁、薛国观、袁鲸之流哑口无言,一场波澜始告平息。
看似平淡的事件,内中却大有玄机。按照惯例,内阁首辅政务繁重,主持会试之事应由内阁次辅担任,周延儒以首辅身份主持会试是破例的行为。科举考试与官场人事关系密切,考生与主考官之间原先并无师生关系,一旦跃登龙门,就构成门生与座主的关系,进而发展成政坛的派系。周延儒亲自出马,意图搜罗名士作为门生,巩固自己在朝廷的权力基础。温体仁抓住把柄大做文章,意在攻倒周延儒取而代之。因此之故,陆世仪《复社纪略》把此事定性为“温周相轧之第一事”:
崇祯庚午(三年, 1630) 乡试,诸宾兴者咸集,天如又为金陵大会。是科主裁为江右姜居之曰广,榜发,解元为杨廷枢,而张溥、吴伟业皆魁选。陈子龙、吴昌时俱入彀,其他省社中列荐者复数十余人。明年辛未会试,伟业中会元,溥与夏曰瑚又联第。江西杨以任,武进马世奇、盛德,长洲管正传,闽中周之夔,粤东刘士斗并中式。主试为周延儒首相也。旧例,会试主裁,元老以阁务为重,应属次辅。乃周以越例得之,大非次辅温体仁意,是以会元几挂吏议。盖延儒诸生时,游学四方,曾过娄东,与伟业之父禹玉相善;而伟业本房师乃南昌李明睿,李昔年亦游吴,馆于邑绅大司马王在晋家,曾与禹玉相善。是科延儒欲收罗名宿,密嘱诸分房于呈卷前,取中式封号,窃相窥视。明睿头卷即伟业也。延儒喜其为禹玉之子,遂欲中式。明睿亦知为旧交之子,大喜悦,取卷怀之,填榜时至末而后出以压卷。伟业由此得冠多士,为乌程(温体仁) 之党薛国观泄其事于朝,御史袁鲸将具疏参论。延儒因以会元卷进呈御览,烈皇帝亲阅之,首书“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八字,而后人言始息。此温周相轧之第一事也。
3. “人间好事皆归子”
这一波折对于初出茅庐的吴伟业而言,吃惊不小。他去世前写给长子吴暻的遗书,提及此事仍心有余悸 :“吾少多疾病,两亲护惜,十五六不知门外事。应童子试,四举而后入彀。不意年逾二十,遂掇大魁,福过其分,实切悚栗。时有攻宜兴(周延儒) 座主,借吾为射的者,故榜下即多危疑。赖烈皇帝保全,给假归娶先室郁氏。”初涉政坛就体验到政治的险恶,温体仁把他当作攻击周延儒的箭垛,他自己则有“福过其分”之感,因而悚栗不已。令他转忧为喜的是皇帝钦赐假期,回乡婚娶,士人以为无上荣耀。同时高中进士的张溥,也沾到喜气,写诗祝贺:
“人间好事皆归子”,连他这位老师也自叹不如。然而吴伟业一生都对老师尊敬有加,高度评价老师的学问 :“西铭先生以教化兴起,云间夏彝仲、陈卧子从而和之,两郡之文遂称述于天下。人止见其享盛名、掇高第,奉其文为金科玉条,不知西铭之书,羽翼经传,固非沾沾于一第已也。”奉旨归娶,是吴家的莫大喜事,举行了盛大的婚礼,那一年祖母汤太夫人七十四岁,父亲吴禹玉四十九岁。张溥描述道:“骏公试南宫第一,时未娶妇,告之,天子赐驰节还里门。太夫人拥孙襕笏甚欢,为问都中起居,龋然而笑,于是绾其发,饮以醇酒。明年(崇祯五年, 1632),骏公成婚礼,一城聚送致贺。太夫人凭高轩望新妇入门,灯火夹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