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多年来,我们经常收到读者来信,对我们出版的图书提出意见和建议,也向我们的作者提出与图书有关的问题。为此,我们开设“作者访谈”专栏,就读者关心的话题采访我们的作者。今天刊出的是我们和“三全本”《长短经》注译者刘子立老师的访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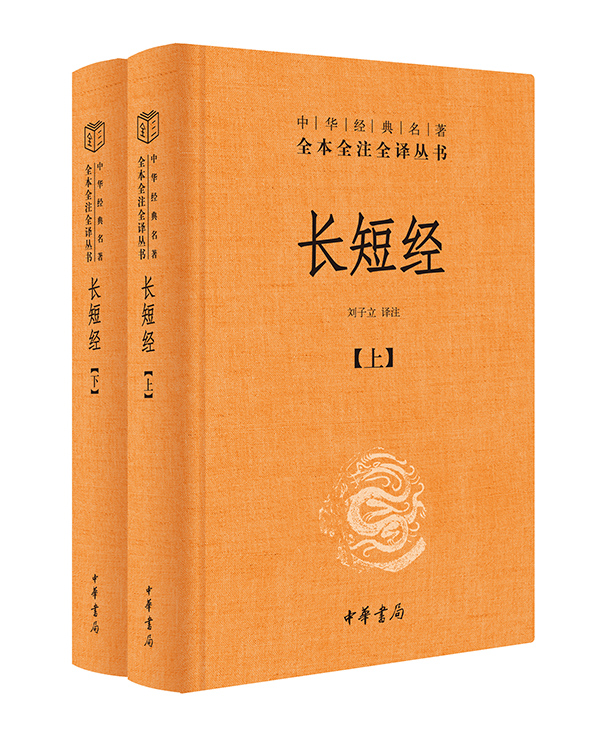
《长短经》作者

刘子立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师,古典文献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先唐文学文献。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汉书》史料构成与历史书写研究”,并在《文史哲》《文史》《史学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1
Q:看到《长短经》的读者朋友们,都惊喜地发现,几乎每一条原文都找到了原典出处,请问您是怎么做到的?
A:赵蕤所引的书,绝大部分是经、史、子三部中的经典。来自经、史二部中的引文,今天基本都能看到(隋唐之际相关史事的记载略有例外,其与《隋书》、新旧《唐书》《大唐创业起居注》等史书存在着不少出入);子部中的某些引文,虽然原书已经散佚,但在《群书治要》等类书中还能看到。
在“经典古籍库”等数据库的帮助下,要找出原文并不算困难。按照我进行注译时的感受,真正困难的反而是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由于《长短经》系“抄撰”成书,所以如要较好地进行注译,不仅需要注意《长短经》的本文,还需要对引文出自的文献有较为透彻的了解。
如《长短经》的《大体》《任长》《品目》《量才》《知人》《德表》等篇章,不仅大幅引用了刘劭《人物志》中的文字,而且深度借鉴了《人物志》的人物理论。如《任长》篇强调“偏材”问题,《品目》篇强调人物的才性既有等级的不同(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又有类型的区别(英、俊、豪、杰),其文字未必均来自《人物志》,但其核心思想却毫无疑问借鉴自刘劭。要将这几章注好,就不能仅看《长短经》原文,还必须对《人物志》全书有较为通透的理解。
读者在阅读《长短经》时,其实也会遇到这个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长短经》也可以成为我们通向经典文献的津梁。
其二,《长短经》涉及了一些较为专门的天文、方术等知识。
如《察相》篇中,充斥着具体且繁琐的相术知识。又如《三国权》中这一段文字,涉及到古代天文学方面的知识:
天帝布政房、心,致理参、伐。参、伐则益州分野,以东井南股距星为界。东井南股距星,连钺者是也。觜星度在参右足,玉井所衔星是。西距星即参中央三星,西第一星是。
再如卷九《兵权》中,多处涉及“兵阴阳”之学。如《结营》篇“背建向破”涉及到古代方术中的建除术,《天时》篇“能知三生”,“从孤击虚”涉及到遁甲术与孤虚术,“必观风气之气”以下一段文字及注文,涉及到观云气术。由于相关知识的欠缺,我在进行注释时颇费了一番功夫。但注译得是否妥当,还得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2
Q:《长短经》约十九万字,只有一万字是赵蕤自己写的,其余都是引用前人的著述,请问他自己写的这部分是怎么确定的呢?
A:在引用前人著作前后,赵蕤会以一些简明的文字,或连缀上下文,或总结说明。有一些地方,还冠以“臣闻”或“赵子曰”。只要一一核对原典,明确了引文的上下限,赵蕤自著的部分并不难找出。赵蕤引用原典,有些是原文整段摘录,改动较少,注中就用“出自”。有些削删很多,乃至调动原文次序,重新组织,注中就用“抄撮”,以示区别。
3
Q:为什么赵蕤拒绝出来做官,却给皇上献上这样一部成就王霸之业的巨著?在您心中,赵蕤是什么形象?
A:由于文献记载的缺乏,赵蕤的生平行事已难确切考知。不过,唐代的隐士是一个类型多样的群体,其中不乏有身在江湖、心怀魏阙,甚至以退为进,走终南捷径的人。赵蕤的学生(或曰好友)李白,正有着这样的经历。就此而言,赵蕤“征君”的身份,与他积极著述之间并不矛盾。若从更高的层次说,中国古人向来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赵蕤或不愿涉足仕途,但醉心于名山事业,也是很有可能的。
在我的心目中,赵蕤首先是一位博极群书,且抱负极高的人。宋代之前,书籍以手抄本为主要载体,复制、流传皆非常不易。赵蕤以一介布衣的身份,却能够出入经史、融会诸子,展现出极其广博的知识储备,这实在令人惊叹。在这些知识中,重点又在于能够“扶颠定倾”、“革易时弊”的治国之术,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经验,这也充分显示出了赵蕤的高自标置与远大抱负。
不过,如《长短经》自序所言,这套“经纶通变”的治国术,主要是为了应付“诸侯之变”、“风尘之会”的特殊局面,以纠正儒者的短处。在唐初那样一个相对承平的年代,这难免沦为难以施展的屠龙之术。故在我的想象中,像赵蕤(乃至李白)这样的人物,知识广博、才气纵横、抱负极高,但由于身份、见闻所限,对政权在分官设职、典章制度等现实层面的运行却未必有深刻的了解,故《长短经》有着比较明显的务虚色彩。
4
Q:人们都称《长短经》为“谋略奇书”,有很多管理学和处世学方面的内容,您在注译过程中印象最深或者说对您最有启发的是哪部分?
A:印象最深的还是《是非》篇,非常精彩。赵蕤从经史典籍中挑选了53对正反命题,让不同时代、不同学派的先贤们站在同一个辩论场上,以“是曰”为正方,“非曰”为反方,彼此间展开激烈的交锋。如儒家与法家之间,对待“逸民”(或曰“处士”)这一类人物有着迥然不同的态度:
是曰:《论语》曰:“举逸民,天下之人归心焉。”
非曰:韩子曰:“夫马似鹿,此马直千金。今有千金之马,而无一金之鹿者,何也?马为人用,而鹿不为人用。今处士不为人用,鹿类也。所以太公至齐而斩华士,孔子为司寇而诛少正卯。”
儒家主张“举逸民”,而法家则针锋相对地认为,这类人物无益于用,不可被其虚名所迷惑。赵蕤敏锐地察觉到了儒、法之间的这种差别,将其放在一处进行比较。
值得注意的是,赵蕤在此处并不对某一方观点进行批判,完全不表现自己的倾向。正如赵蕤在本篇篇末所云,这些不同的观点“其言虽殊,譬犹水火”,但相灭相生,相反相成,经过考虑权衡之后,均能在恰当的情境下发挥其作用。这显示了赵蕤并不盲从于任何一个学派或经典,而是以“通变”为基本原则,展现出了思想的高度自主性与创造性。所以《长短经》虽然是“抄撰”而成的著作,但著作权却毫无疑问地属于赵蕤。
5
A:《反经》是《长短经》卷三《文下》中的一篇。《文下》中的四篇(《反经》《是非》《适变》《正论》),是一个层层深入,首尾呼应的整体。
所谓“反经”,指对于经典或某些一般性原则的批判。儒家有“反经为权”的说法,《公羊传·桓公十一年》说:“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本篇名为“反经”,正是从这一典故中脱胎而出。
为何要反经?赵蕤认为仁、义、礼、乐、名、法、刑、赏,乃至文书、尊贤、明罚、明察、忠孝等等道德规范与施政方式,都存在着负面作用,若“用失其宜”,反而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如赵蕤引用《尹文子·大道下》中的言论:
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私;
义者所以立节行,亦所以成华伪;
礼者所以行谨敬,亦所以生惰慢;
乐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
因此,“仁义礼乐”这些原则,皆不可盲从。事实上,紧接着《反经》的《是非》篇,正是对这一观点的进一步深化——赵蕤指出,即便在经典之中,也存在着众多截然相反的观点。若盲信盲从,究竟要追随那一家?如此一来,便自然地引申出了进一步的结论:君主必须根据时势的不同,“不法古,不修今”,“当时而立法度,临务而制事”,这便是《适变》篇的内容。所谓“适变”,也就是《公羊传》所说的权道。所以这一部分的内容,又与《长短经》卷七《权议》遥相呼应。在最后的《正论》篇中,赵蕤曲终奏雅,指出不可一味权变,否则将“流遁漫羡无所归”。
经过这一番“否定之否定”后,作者提出了一套相当完善的“反经为权”的理论体系与操作方法。这一部分篇章,很能见出赵蕤的巧妙用心,是《长短经》中尤为精彩的一个部分。
就我目前所见,大概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有一些出版者将《长短经》改名为《反经》出版,以便引起购书者的兴趣。但这样改名,不仅毫无依据,而且难免让人将“反经”理解为“反面的经典”,反而混淆了赵蕤的本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