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元稹才华横溢,风流倜傥,人生充满传奇色彩。他自撰《莺莺传》,叙述张生与崔莺莺始乱终弃的曲折故事,经宋人解读,张生即他本人,后来学者反复论证,应该已经可以做结论,至于说崔莺莺的真实身份及其家族世系,则学者多有争议,至今难有结论。对此我想补充的证据是,《元氏长庆集》今存六十卷本,其中涉及早年这段经历的内容很少,偶也有孑遗,而五代后蜀韦縠编《才调集》,多存集外诗,很多皆与早年情事有关,当别有所本。
本文只想谈确实可知的事实。近代以来,学者治元稹者颇多,对元稹与韦丛、裴淑的两段婚姻,已经基本梳理清楚,而在两段婚姻之间,曾纳妾安仙嫔。本文考虑写作,除拟对前人研究加以归纳,结合元稹存诗加以分析,还因近期见到 2023年陕西咸阳洪渎原出土韦绚撰裴淑墓志,以及韦绚本人墓志,可以在学界共知事实外谈出一些新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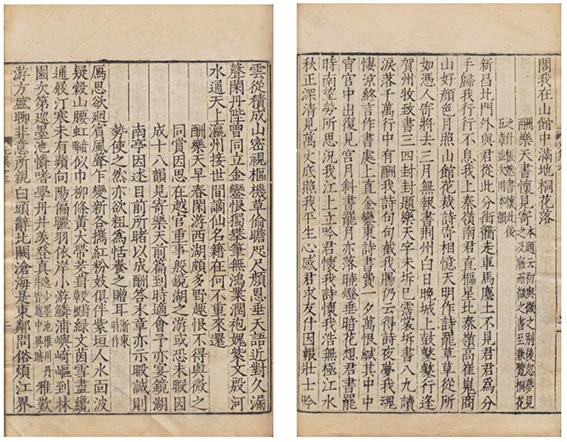
▲ 元稹《元氏长庆集》卷六、卷十三,明嘉靖董氏翻宋本(日本内阁文库藏)
一 初婚韦丛
元稹初婚于韦丛,韩愈撰《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夫人墓志铭》(宋蜀本《昌黎先生文集》卷二五)记录了韦丛生平的基本情况:韦丛,字茂之,世出京兆韦氏龙门公房,为德宗朝名臣韦夏卿的幼女。元和四年( 809)七月九日卒,得年二十七,即当生于德宗建中四年( 783)。元稹较韦丛年长四岁,这一年三十一岁,二月得宰相裴垍提携为监察御史,三月充剑南东川详覆使,调查泸州监官任敬仲赃案,七月五日即归京不久,分务东台,即在东都洛阳的御史台,二十三日到任。也就是说从韦丛病重到去世,元稹几乎都不在她身边。十月,遣家人葬韦丛于咸阳奉贤乡洪渎原,他也没有到场。但请大名家韩愈撰墓志,请沈传师正书,规格很高。这方墓志在宋代已经出土,见《宝刻丛编》卷八引《诸道石刻录》,后不知所在,也无拓本存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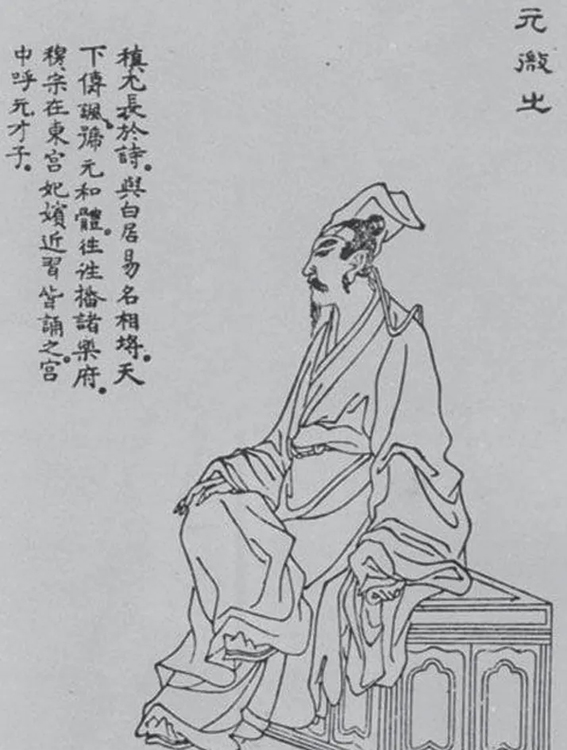
▲ 元稹像
这里首先要说的是韦丛的家世。龙门公房是韦氏中显赫的一支,韩愈志称“龙门之后世,率相继为显官”,也属于事实。韦丛曾祖父韦伯阳,“自万年令为太原少尹、副留守北都”;祖父韦迢,“以都官郎为岭南军司马”,皆属中层文官。其中韦迢,大历四年( 769)赴任韶州刺史,曾与杜甫有两次唱和。先在长沙,杜甫作《潭州送韦员外迢牧韶州》为他宠行,有“炎海韶州牧,风流汉署郎”,知韦以郎衔出牧。迢作《潭州留别杜员外院长》,有“大名诗独步,小郡海西偏”之句,这里“大名”是称赞杜甫诗名,“小郡”指自己将要赴任的韶州。分别以后,迢于路有《早发湘潭寄杜员外院长》,有“相忆无南雁,何时有报章”句,知两人交谊颇密。杜甫以《酬韦韶州见寄》作答,有“深惭长者辙,重得故人书”,韦迢实际年龄可能长于杜甫。就目前所知,韶州任后,韦迢以检校都官郎中,充岭南节度行军司马,卒,即韩愈所称“都官郎”只是虚衔。在此特别说到韦迢,是要说明杜甫孙杜嗣业后来找元稹为杜甫撰墓系铭,除元稹名气足够,更因他是杜甫旧友的孙婿。
韦丛父韦夏卿,两《唐书》皆有传,吕温《故太子少保赠尚书左仆射京兆韦府君神道碑铭》记载更详。夏卿( 743—806),德宗时任吏部侍郎、京兆尹、东都留守,官至太子少保,地位崇高,且交际广泛,名重一时。韩愈志称韦丛母为给事中裴皋女,皋则为玄宗相裴耀卿子,是另一高门。不过元稹另撰《有唐武威段夫人墓志铭》(翰墨堂藏拓本),载韦丛出生未匝月母亲即卒,鞠养于韦妾段氏:“始余亡妻生不月而先夫人殁,免水火之灾,成习柔之性,用至于妆栉、针组、书诫、瑟琴之事无遗训,诚有以赖焉。是以余妻之言于余曰:‘离则思,思则梦,梦则悲,疾则泣。’恋恋然,余不知其异所亲矣。决余之际,且以始终于敬为托焉。”段氏与韦丛卒于同年,晚三个月,年四十,是韦丛对段氏感情最深,临终也将后事相托段氏。
元稹与韦丛结婚时间,卞孝萱《元稹年谱》考在贞元十九年( 803),元稹前一年冬应吏部试,本年授秘书省校书郎,时年二十五,韦丛年二十一。此年韦夏卿自京兆尹改太子宾客,十月为东都留守、东都畿汝防御使,新婚的元氏夫妇随侍往洛阳,归住韦氏履信坊宅。元稹作《陪韦尚书丈归履信宅因赠韦氏兄弟》:“紫垣驺骑入华居,公子文衣护锦舆。眠阁书生复何事,也骑羸马从尚书。”前两句写韦氏父子,华居、锦舆写出居第之奢华,服饰之精致,自己位卑身贫,相随有荣幸之感。又《韦居守晚岁常言退休之志因署其居曰大隐洞命予赋诗因赠绝句》:“谢公潜有东山意,已向朱门启洞门。大隐犹疑恋朝市,不如名作罢归园。”韦夏卿的最后两年,身居洛阳,名为留守,其实近于退休。这里已称韦为谢公,以谢安退居东山为比。另作《梦游春七十韵》,有一节写韦府全盛时期的景况:“韦门正全盛,出入多欢裕。甲第涨清池,鸣驺引朱辂。广榭舞萎蕤,长筵宾杂厝。青春讵几日,华实潜幽蠧。”正是歌舞楼台,鸣驺引鸾,宾客盈门,出入欢喜。其《追昔游》:“谢傅堂前音乐和,狗儿吹笛胆娘歌。花园欲盛千场饮,水阁初成百度过。醉摘樱桃投小玉,懒梳丛鬓舞曹婆。再来门馆唯相吊,风落秋池红叶多。 ”这是晚年所写,颇多盛衰之感。在这样的氛围中,元稹结识了许多杰出的朋友,包括刘禹锡、柳宗元、元宗简、樊宗师等。也是在这期间,元稹写了《莺莺传》(原题或作《传奇》),表达与崔莺莺决绝之意。
韩愈在《韦丛墓志》中叙述元稹夫妇生活言:“夫人于仆射为季女,爱之,选婿得今御史河南元稹。稹时始以选校书秘书省中,其后遂以能直言策第一,拜左拾遗,果直言失官;又起为御史,举职无所顾。夫人固前受教于贤父母,得其良夫,又及教于先姑氏,率所事所言,皆从仪法。”这里说韦丛在家受教于父母,其实其生母在她出生未满月即去世了,她似乎也并不会以段氏为母;韦夏卿生前,元稹似乎来往京洛间较频繁,大约因韦丛多从父居。元和元年,元稹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起落。年初,岳父韦夏卿去世。元稹应制举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中第者十八人,元稹冠首。不久除左拾遗,因上疏论证,言辞激切,又赞同裴度论权幸的议论,与裴度一起贬官,元为河南县尉,裴为河南府功曹参军。没过多久,元稹即因母卒而归西京守丧三年,直到元和三年末方丁忧除服。
元稹与韦丛婚姻存续的五六年间,从元稹的诗文中所保存的夫妻生活内容较少。目前知道韦丛生有一女保子,成年后嫁故相韦执谊之子韦绚。西安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藏独孤霖撰《韦绚墓志》,载绚卒于乾符己亥( 879),年七十九,其妻即元稹长女,“先公亡廿二年矣”,即卒于大中十一年( 857),得年应在五十以上。
韦丛去世后,元稹写过大量悼亡诗。其中部分是写对故居故物而怀人的悲伤。如《夜闲》:“感极都无梦,魂销转易惊。风帘半钩落,秋月满床明。怅望临阶坐,沉吟绕树行。孤琴在幽匣,时迸断弦声。”是对潘岳《悼亡诗》的模仿,风帘、秋床、临阶、绕树,皆是以往共同生活的回忆。孤琴是说夫妻琴瑟谐和,妻亡则有孤琴断弦之感。再如《醉醒》:“积善坊中前度饮,谢家诸婢笑扶行。今宵还似当时醉,半夜觉来闻哭声。”前两句回忆当年在韦家饮后之欢快,眼前则借酒解愁,半夜醒来,依稀听到哭声,更添悲伤。当然更著名的是元稹为韦丛写了后代广为传诵的《三遣悲怀》,全录如下: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
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
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愧。
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皆到眼前来。
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
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
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
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
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以韦夏卿为谢公,自称黔娄,是相对而言。至于说顾我无衣,拔金钗沽酒,野蔬充膳,落叶添薪,都不免夸张其辞。韦家之富有,元稹前有诗屡称之,何至穷迫如此乎?两人婚姻的近半时间,是在韦夏卿去世,元稹居母忧期间,当时确实有一些困难。元稹在《祭翰林白学士太夫人文》中说白居易曾用自己母亲的名义,多方给以接济:“太夫人推济壑之念,悯绝浆之迟,问讯残疾,告谕礼仪。减旨甘之直,续盐酪之资,寒温必服,药饵必时。”第二首说夫妻言及身后之事,知因果之有报,因此而多行善事,最后以“贫贱夫妻百事哀”为结,结合生前二人之戏言,更增感伤之哀恸。第三首更因悲妻而自哀,自己命中无子如邓攸,而潘岳悼亡更能体会其间切肤之感。后几句有些发誓的意思,似乎要以不婚来报答对韦丛的情感。类似情况恰如白居易在元稹去世后,有发誓不再作诗而来悼念亡友,很快发现几乎无法做到。这里特别要说到“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对此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和卞孝萱《元稹年谱》皆有详尽讨论,较倾向于卞说三诗皆作于韦丛去世后不久,元稹任职东台御史时。至于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认为韦丛缺乏才情,能力亦稍逊,皆或属实。当然夫妻之间主要是情感相投,互相尊重理解,才情、能力皆属其次。
二 纳妾安仙嫔
元稹于元和五年春,因得罪宦官,贬江陵府士曹参军。次年,因李景俭作介,纳妾安仙嫔。卞孝萱《元稹年谱》因元和六年寒食后作《六年春遣怀八首》,尚是鳏居口气,认为纳妾为此后之事。其实,唐人娶妻须看门第,妾侍则多为身份卑微之人,纳妾并非婚姻。元稹在任江陵期间,元和九年安氏卒后,元稹撰《葬安氏志》,既说安氏侍己已四年,更云安氏所生子元荆,时已四岁,则纳妾应早于元和六年。《葬安氏志》前半云:“予稚男荆,母曰安氏,字仙嫔,卒于江陵之金隈乡庄敬坊沙桥外二里妪乐之地焉。始辛卯岁,予友致用悯予愁,为予卜姓而授之,四年矣。供侍吾宾友,主视吾巾栉,无违命。近岁婴疾,秋方绵痼,适予与信友约浙行,不敢私废。及还,果不克见。”其中“约浙行”,四库本《元集》及《全唐文》皆同,周相录《元稹集校注》据蜀本、卢本改“浙”作“淅”,是。卞孝萱《元稹年谱》谓元在此年闰八月曾从事唐州,淅阳地近邓州,安氏即卒于其时,是她服侍元稹,其实只有三年半时间。从元稹的叙述来看,他称安氏为“予稚男荆,母曰安氏”,即是孩子他妈,但非我妻。致用为李景俭,“为予卜姓而授之”,其实应为转让或购买性质。安氏对元稹,是“供侍吾宾友,主视吾巾栉,无违命”,即替自己招待宾朋,照顾起居,皆能听从吩咐。在这期间,安氏为元稹生了一子二女,即子荆,女樊和降真。元稹更说明:“稚子荆方四岁,望其能念母亦何时?幸而立,则不能使不知其卒葬,故为志且铭。”即他为安氏营葬事,是虑及其子若能成立,应让他有机会知道母亲的葬地。但安氏位微,不能入葬元氏家族墓地,故仍留葬江陵。对安氏的命运和不幸,元稹有一段堪称难得的议论:
大都女子由人者也,虽妻人之家,常自不得舒释,况不得为人之妻者,则又闺衽不得专妒于其夫,使令不得专命于其外,礼仪不得以尊卑长幼之序加于人,疑似逼侧,以居其身,其常也。况予贫,性复事外,不甚知其家之无,苟视其头面无蓬垢,语言不以饥寒告,斯已矣。今视其箧笥无盈丈之帛,无成袭之衣,无帛里之衾,予虽贫,不使其若是可也。彼不言而予不察耳,以至于其生也不足如此,而其死也大哀哉!
妻妾仅是名分之不同,所谓“不得为人妻者”,即因出身卑微而不得与士人为婚配,这是由唐代社会区分良贱的法规所决定,元稹当然无力加以改变。在安氏亡故后,方发现她没有像样的个人财产和衣服被衾,如果自己多加关心,本来是可以稍加改善的。这里有一些同情,但在礼法面前,他也无从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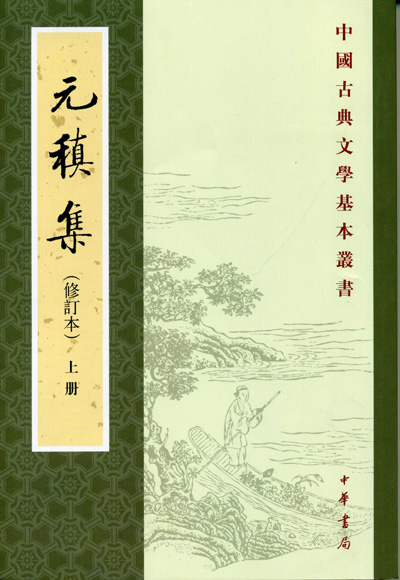
▲ 中华书局版《元稹集》(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三 再娶裴淑
元稹存世作品与相关史料皆极其丰富,他在通州司马任上娶妻裴淑,虽然时间有元和九年、十一年、十二年之差异,但大端情况已经基本清楚。卞孝萱《元稹年谱》认为是元和十一年从通州到涪州成婚,后同归通州,时间可为结论。此后直到元稹去世之十五六年,两人共同生活,从未分开,细节记录亦多。新出裴淑墓志,题作《唐故武昌军节度使丞相元公夫人河东郡君裴氏墓志铭》(后简称《裴淑志》),署“大中大夫权知太府卿上柱国赐紫金鱼袋韦绚撰”,绚为元稹长女婿,所述也极其详尽,多前人所不知者。试分别述之。
有关裴淑的家世,《裴淑志》云:“皇考讳好古,河东人也。母新野庾氏。两家其先祖世伯叔,皆卿族大官,郁为轩冕之望,独皇考终于滁州永阳宰,昆仲悉州郡郎署之显人。”裴氏为北朝末崛起的河东大姓,世多显宦。其母家庾氏,则为东晋以来的高门。二姓在唐多高官,皆属事实。淑父官仅至滁州永阳令,不算发达,韦绚叙述中稍有遗憾。
裴淑的生卒年。《裴淑志》载元稹卒时,“夫人年甫卅七。后元公之殁,寡居凡卅二年,寿至六十八”。于咸通“三年四月九日,终于安仁里之私第焉”,用公元记载,其生卒年为 795—862,即较元稹年轻十六岁,元稹去世后孀居三十二年,安仁里仍为元稹旧宅。
裴淑的早年经历。《裴淑志》载:“迨永阳即世,圣善岿然,有遗孤一男一女,惸独靡依,尚书怜之,乃命挈其属入家而长养之,皆成人焉。故夫人与其母兄不识稼穑之苦,所以世称庾公为厚德矣。宜其出入清列,负重价于时哉。”裴好古卒年不详,估计应在裴淑十岁以前。此处所称尚书,为裴淑母庾氏之长兄庾承宣。墓志称其为“故天平军尚书”,是他大和九年( 835)的终职,元稹不及见。承宣为贞元八年登进士第,与韩愈、李绛等为同年,即世称龙虎榜者。今知承宣元和初,为殿中侍御史,十三、十四年,以中书舍人两次权知礼部贡举。是元和间其官已显。裴淑母在夫亡,子女尚幼时,携归裴淑舅家,类似情况唐时甚多。裴淑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受苦,且知诗书,知琴乐,与在舅家生活安定大有关系。
裴淑出嫁元稹的过程。《裴淑志》记载较详:“元公丧偶,负谴在通州为司马。是际,庾公见夫人及笄,历视族中曰:‘吁,无可与此女为夫者。’盖心奇外甥,质此令淑,不偶然也。会庾公之季故左丞讳敬休,与元公友善。乃佥话此女曰:‘唯通川元九微之可以为对。’庾公信然之。左丞曰:‘元九名人,久居谪宦,势不可遏矣,宜即其窜所而妻之,怵人我先也。’庾公乃谓其孀妹曰:‘吾与若得良女夫矣,勿以官微栈险;亟辇其女径抵汉中,吾俾其乞假于公府,而合二姓之好焉。’”裴淑成婚时,年二十二,唐人说及笄,仅取其约数。所述庾承宣见本族族人中无合适可婚配者,是按唐人择婿的一般考虑。承宣季弟敬休( 781—835),元和八年为右拾遗、集贤直学士。历右补阙,转起居舍人。十三年,为礼部员外郎,入为翰林学士。这是元稹再婚前后他的历官。元稹有《寄庾敬休》:“小来同在曲江头,不省春时不共游。今日江风好暄暖,可怜春尽古湘州。”是两人是少年时朋友,交谊尤深。元稹于元和十年贬通州,遭遇政治上重大挫折。庾氏兄弟不以为意,毅然将甥女相嫁,可谓对元有深切的认知与关心。从“官微栈险”,“径抵汉中”来看,裴淑由其母陪同,从京城出发,经汉中入蜀,元稹也从通州北上迎娶。以往根据元稹《祭礼部庾侍郎太夫人文》,即祭悼庾敬休母亲之文,说“稹也幼妇,时惟外孙,合姓异县,谪任遐藩”,及元稹答裴淑诗“嫁时五月归巴地”,认为元稹亲迎之地在涪州,是不对的,涪州近今重庆,裴淑母女不是乘舟泝江入蜀的。
裴淑必为宰相妻的两段传闻。《裴淑志》记载了两段传闻,一是仍在庾家时,“初,长安中有无目龙待诏者,善听人语音,虽謦咳之声,亦知休咎。庾公尝于家聚庠序群小,杂以家僮,各令语言,命龙生听之。阅数辈,默至夫人,曰:‘此儿若是女子,必为宰相妻。’诸亲见夫人母子孤幼,依倚外家,闻其言皆哂之。”一位寄居舅家的孤女,被这位目盲的龙待诏认定将为宰相妻,故闻其言者皆不信。又云:“又元公在汉中,有城固青师,亦好相人,人皆出妻子求其言。见夫人曰:‘面如满月,此将相之妇也。’”这应该是元稹到汉中亲迎时的事情。韦绚说这两段故事,是他宝历中到越州迎娶元宝子,听闻裴淑在宴席上所言,似非出于编造。
元稹的时来运转与裴淑之显耀。元稹在通州四年,艰难备尝,其中包括与裴淑婚后的两年半。元和十三年冬,元稹内迁为虢州长史,其地在两京之间。次年春,沿江东下以赴任,曾与白居易在峡州停舟三日会聚。此年秋因赦,入为膳部员外郎。十五年初,宪宗去世,宰相令狐楚为山陵使,元稹为其判官。不久,以祠部郎中知制诰。长庆元年( 821)二月,元稹为翰林学士。十一月,罢学士,为工部侍郎。二年二月,元稹同平章事,即为宰相。六月,元稹罢相,出为同州刺史。其实,元稹任宰相仅四个多月,其间且经历较多风波,涉及其与宦官之交往,及党争中的是非。就目前所知看,他之入相原因,一是穆宗赏识,二是裴度再度秉政,三也包含宦官中有为他美言者。《裴淑志》有一节特别讲到裴淑以宰相妻入内朝贺之荣光:“及是际遇元日大朝会,身为命妇之长,又宰相独元公有夫人,礼合悬珠,翠拖绣襦,朝贺皇太后于南宫,宿备车舆,夜施庭燎,亲族皆来集,未明绛骝秉烛,前引缇骑,持杖呵街而出。”应该指出的是,元稹二月入相,故裴淑参加的不可能是元日朝会。当时宰相为裴度、李夷简、王播、杜元颖和元稹,元稹时年四十四岁,最为年轻。而裴淑此时二十八岁,与元稹成婚方五年,即能享受如此荣耀,确实可称盛事。
裴淑与元稹相知颇深契。还在通州期间,元稹有诗《景申秋八首》,景申即丙申,元和十一年,二人成婚当年,诗中说:“啼儿冷秋簟,思妇问寒衣。”又说:“婢报樵苏竭,妻愁院落通。”即裴淑已承担了家中主妇的责任。他在通州作《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序云:“通之人莫可与言诗者,唯妻淑在旁知状。”是裴淑知诗,可为他的红颜知己。他写收到白居易在江州寄来的诗,《得乐天书》:“远信入门先有泪,妻惊女哭问何如?寻常不省曾如此,应是江州司马书。”得友人消息,自己激动到落泪,妻女也相陪惊哭,可谓同欢共悲。途出峡中时,元诗有《黄草峡听柔之琴二首》:“胡笳夜奏塞声寒,是我乡音听渐难。料得小来辛苦学,又应知向峡中弹。”“《别鹤》凄清觉露寒,离声渐咽命雏难。怜君伴我涪州宿,犹有心情彻夜弹。”黄草峡在涪州,柔之为裴淑字,在东下船上,裴淑弹琴以遣兴,元稹于其间听到了如蔡文姬出塞胡笳般的哀怨之声,也听闻了中原的乡音。所谓“小来辛苦学”,是说裴淑从小有很好的音乐学习。而《别鹤》是古琴曲,借鹤言男女之分别,元稹听懂了琴声中妻子的心声,更感谢她相陪,彻夜弹奏。白居易另有诗,题作《和微之听妻弹别鹤操因为解释其义依韵加四句》,其中既说“义重莫若妻,生离不如死”,又说:“无儿虽薄命,有妻偕老矣。”则是另一次弹奏,元诗不存。
元稹罢相后,在同州、越州、武昌任刺史或观察、节度使,三处皆大镇,是虽远离京城,朝廷对他还是颇多倚重。其中将赴越州时,元有赠妻诗,题作《初除浙东妻有阻色因以四韵晓之》:“嫁时五月归巴地,今日双旌上越州。兴庆首行(自注:平声)千命妇(自注:予在中书日,妻以郡君朝太后于兴庆宫,猥为班首),会稽旁带六诸侯。海楼翡翠闲相逐,镜水鸳鸯暖共游。我有主恩羞未报,君于此外更何求?”越州即今浙江绍兴,乃东南重镇,风物名区,也是元稹首度出为镇帅。大约因裴淑生长中原,对南方远行,颇有畏惧之感,元稹作此诗相劝勉,回顾初婚时之艰难,今日拥旌中荣光,说到朝廷之恩荣,更说到越中景物之瑰丽。最后说朝廷对我恩重如山,你还希望得到什么呢?夫妻之间,是有如此之沟通。
大和三年九月,元稹入为尚书左丞,岁末回到京城。其间曾购入韦夏卿洛阳履信坊宅,作退归之居。但仅月馀,获命为武昌军节度使。《云溪友议》卷下载:“是时,中门外构缇幕,候天使送节次,忽闻宅内恸哭。侍者曰:‘夫人也。’乃传问:‘旌钺将至,何长恸焉? ’裴氏曰:‘岁杪到家乡,先春又赴任。亲情半未相见,所以如此。’”对裴淑来说,亲人都在京城,孰料来去匆匆,又要随夫出守。在别人看来授以重镇节旄的欢庆时刻,她却不免悲从中来,放情大哭。元稹作《赠柔之》劝慰云:“穷冬到乡国,正岁别京华。自恨风尘眼,常看远地花。碧幢还照曜,红粉莫咨嗟。嫁得浮云婿,相随即是家。”自己也觉得仓促了一些,但王命在身,也是不能自己决定去留。“嫁得浮云婿,相随即是家。”有深深的检讨,不是我不理解你的伤感,自己人生就如同浮云般飘忽不定,只能难为你相随天涯了。裴淑答云:“侯门初拥节,御苑柳丝新。不是悲殊命,唯愁别是亲。黄莺迁古木,珠履徙清尘。想到千山外,沧江正暮春。”这是裴淑唯一的存诗,《云溪友议》撰者范摅云:“元公与柔之琴瑟相和,亦房帷之美也,余故编录之。 ”应该较可靠。裴淑云初春时节,柳丝新绿,你也初拥节度。浙东是观察使,武昌是节度使,两者还是有些不同。裴淑说自己的悲痛,不是感叹命运不公,而是遗憾与亲人别多聚少。这时对她恩重如山的大舅庾承宣、小舅庾敬休都还健在,她确实希望多多追陪游赏。后面四句,显示她的豁达。春回大地,黄莺欢鸣,游人如织,何处不是如此呢?千山之外,也有更美好的景色。
裴淑为元家克尽妇职。裴淑为元稹的续弦,她有为元稹养育子女的责任,更要面对元稹前此娶妻纳妾留下来的子女,更要为家庭继嗣考虑,接受丈夫的婚外情。《裴淑志》讲到裴淑本人的生育:“有儿女数人,皆不育。唯一女聪慧强明,适进士李柷。琴瑟不合,迨今在家,李亦不亲迎,天使然也,人皆叹之。六亲以夫人福履不为不盛矣,而使元公有邓攸之叹,形于歌诗,惜哉,不成全福。”是裴淑与元稹婚后约十五六年,生有儿女数人,皆未长成。又说一女已许配进士李柷,但性格不合,李亦不来迎亲,因此耽搁在家。这时元稹去世已久,此女很可能近四十岁而未嫁。此外,韦丛留一女宝子,嫁韦绚,前已述及宴会上裴淑之快谈往事,看来对此她也没多操心。安仙嫔留下一子二女,其中女樊卒于虢州,降真卒于稍前,皆甚年幼。元稹分别作《哭小女降真》《哭女樊》,对女樊用情尤深,更作《又哭女樊四十韵》以述哀。而一子元荆,安氏卒时已四岁,到元稹任翰林学士的长庆元年夭亡,算来有十多岁了,元稹作《哭子十首》,心情坏到极点。
《裴淑志》载:“初,丞相在武昌,侍人李氏有一子,始绝伯道之叹,幼字有中,亦曰道护。今仕名谟,前家令寺丞,好诗书,壮可室矣。迨此东璧虽累然,绰有保家之势。”元稹在武昌仅一年半,道护是此时出生。白居易撰元稹墓志称“子曰道护,三岁”,卞《谱》以为裴淑所生,不确。前引裴淑未生男子,致元稹有“邓攸之叹”,是指绝嗣。而这里又说有一子,“始绝伯道之叹”,伯道即邓攸。二者看似矛盾,其实唐代士族习惯认为正妻所生子方有继嗣资格,非婚生或母亲身份卑微者所生子,没有祭祀或继嗣的资格。韦绚撰《裴淑志》铭文先云:“孝女哀哀,椎髻如蓬。荆钗不挂,褐帔待终。”是主持丧事者为孝女,即裴淑所生女。又云:“嗣子承嫡,茕茕惕息。”“赵孤不绝,天道的的。”是此子虽称“嗣子承嫡”,但并不主持家务,地位也较低。
元稹身后,裴淑守护元氏家族三十二年。《裴淑志》云:“寡居凡卅二年,寿至六十八,居大第,为二百口之长,资产不耗于前,善心计,虽黠吏狡仆,不敢面谩及舞文于簿书之间。或曰,富于旧时,则善治生,干于事,可知也。 ”此处所云大第,即元稹安仁旧居。其家连族人婢仆,多达二百人,元稹留下的资产经此漫长岁月,不仅没有耗竭,可能还略有增加。韦绚赞扬裴淑“善心计”,即不为吏、仆之人所侵夺,也防止了在簿书之间的舞弊行为,又“善治生”,即能理财,有增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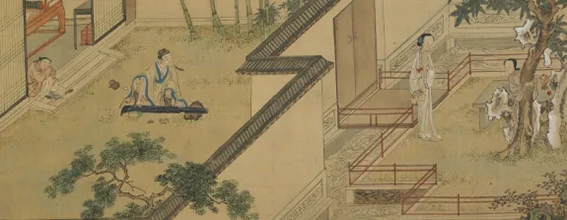
结语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金人元好问的这两句,用在元稹身上并不恰当,因为他的一生,似乎始终在爱情之冲动与婚姻之理性间徘徊。他在与韦丛结婚后饱含情感地回忆与崔莺莺的冲动爱情,但又在君子知过的借口下及时抽身。他与韦丛的婚姻,似乎更多着眼于韦氏家族的社会地位,但就他的仕途来说,获得的帮助并不多。与后来的裴淑相比较,韦丛的才情显然要逊色一些,虽然我们可以被元稹悼亡诗中的贫贱夫妻人设所打动,但其间真实情况似乎被放大了很多倍。裴淑对元稹来说,其知书达理,奏琴理家,皆出色当行,在元稹存诗中,可以不断读到他对裴的赞赏与认可。更可贵的是在元稹死后,裴淑维持这一家族三十多年的生存发展,实在不容易。同时,我们也不必以今日之婚姻道德要求古人。唐代是士族社会,也存在贱人阶级,本文提到的安仙嫔与“侍人李氏”,即属于这一身份。在元稹与前后成婚的两位妻子身边,可能还有不少这样身份的女子。白居易也是如此。不过元白写诗,白居易更喜欢提到他身边的莺莺燕燕,元稹则稍收敛一些。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5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