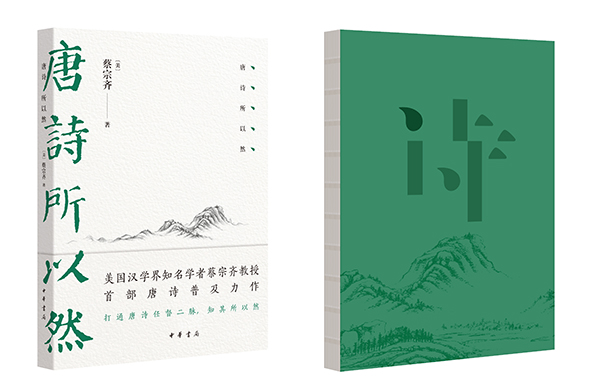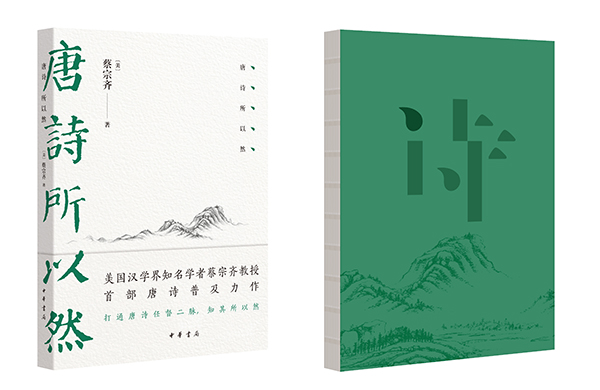
程羽黑评《唐诗所以然》|唐诗何以然?
评论内容:
读蔡宗齐先生这本书,极为畅快。首先,它不像很多同类著作,纠结于唐诗“写什么”——对诗来说,“写什么”恰恰是不重要的,关键在“怎么写”,蔡先生此书则更进一步,讨论“所以然”——唐诗为什么这么写?作者天元落子,起手便高,开篇说明本书由纵横两线构成,“纵”是时间上的形式演变,“横”是空间上的类型比较。在这一框架下,七十二首唐诗名作分属十三个主题,章法严谨,奇正相生,显示出蔡先生高超的写作技巧。
十三个主题皆富新意,益人神智。如作者讲到诗体和题材的关系,表现禅意的诗适合用五言律绝写,而咏史诗宜用七言律绝写。合书细想,这个判断真是精到,禅意和咏史都讲究滋味,不过两者相反,前者是字越少越有味,后者是字若少不够味。在第八个主题“怀古绝句:为何五言无法PK七言”中,作者认为杜甫《八阵图》写得不够好,“五绝怀古,诗圣难为”,不迷信名人名篇,极见识力。我觉得《八阵图》就是首庸作,历来关于此诗诗意的讨论极多,有人认为这是好诗的证明,在我看来正好相反——一首二十字的五绝本当以简明见长,引起这么多争议,要么是没把意思写清楚,要么就是必须由读者注入微言大义才能维持名作的地位。
进一步说,很多五言律绝咏史名作其实都写得不够好。如收入《唐诗三百首》的刘禹锡《蜀先主庙》:“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我早年读到,便觉乏味:这不就是把刘备父子的一生复述一遍么?当时有崇拜名作的心理,所以也不敢说,总觉得是自己鉴赏水平不够,而整部《唐诗三百首》,我最喜欢的七律是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干净利落的开头,颔联是绝佳的电影镜头,颈联极沧桑,一结虽是凑韵,却也不失自然。同一个作者,同样是咏史诗,为何差距这么大?
读了蔡先生的书,我似乎悟到了“所以然”——我想是因为,咏史的感情需要流露、摇曳,这是五言律绝难以胜任的。比如《西塞山怀古》颔联里的“几回”“依旧”,都是句眼,读者的心就在这几个字间飘荡,如果是五言就插不进去了。五言的感情是没有摇曳余地的,就像狭窄的空间拉不开一条横幅。它能不能安置情感?能,但这个情感是凝固的,不是摇荡的,“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凄凉”就定调了,像一个特写镜头,不会再有变化。
那么五言能不能咏好史?也不是不可以,需要把篇幅拉长,变成五古,像陶渊明《咏荆轲》:“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何等跌宕。“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又何等摇曳。越发觉得陶公是五言圣手,李杜不及。
凡事两面,五言律绝的这份含蓄正好用来书写禅意。反过来说,把表现禅意的诗写成七言如何?举个例子,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七言中类似的作品如张旭(作者有争议,不赘)《桃花溪》:“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乍看也像回事,但后者实际上仍然是情感的荡漾,最后来个问句,如山歌问答,音乐性十足。前者则极幽寂,是无声境界。《桃花溪》算是含蓄的,庸手还容易把诗写成偈,因为七言易露,禅意之诗无“情”可露,便会露出“理”来,而禅理恰恰是不可露的,“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就像香水打开盖子就会挥发。露了禅理,诗便不成其为诗,而成了“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疑”这样的宗门偈子。
说唐诗,李白自然是重头戏。蔡先生对李白也有极为精彩的见解,让我看得很激动,每看两句,就要合上书,去院子里走一走,消化一下蔡先生的思维火花。比如蔡先生讲《与夏十二登岳阳楼》,“拟人只为找玩伴”,一语点破李白的妙处。这首诗其实一般,但蔡先生所论颔联“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确实能代表李白的一种特质。我觉得长久以来对李白有个误解,认为他的特点是豪放,豪放又被片面理解为说大话。这种说法很有问题:说大话谁不会啊?如果这就是李白,微信群里话最多口气最大的那位也是李白了。遗憾的是,很多诗人是按照这个思路去学李白的。比如清代诗人黄仲则,明明诗里到处是“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这样的寒酸之语,偏要学李白做大言无忌状,让人看着很难受。
清代南薰殿藏李白画像
蔡先生揭出了李白真正的特点——以万物为玩伴。正因他以万物为友,所以显得逍遥恣肆,不受羁勒,给人以豪放之感。最具代表性的是尽人皆知的名句:“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一句话的功夫就多出两个朋友。这种热爱朋友、无中生“友”的心态,使李白非常善用拟人手法——这里的“拟人”还不只是像人,更是赋予万物以生命,正如蔡先生所引“山衔好月来”,其实是把山当成了鸟。有时李白甚至会让自己的器官飞起来:“南风吹归心,飞堕酒楼前。”“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这类极致的拟人化,是李白诗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
这是从哪儿学的?我想大概是受了屈原的启发。《楚辞》里有很多驱遣神灵的情节,比如《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吾令帝阍开关兮”“吾令丰隆乘云兮”,《九章》:“令五帝以折中兮”“吾使厉神占之兮”,《九歌》:“令飘风兮先驱”;等等,仿佛整个天地围着作者转。不过屈原驱策万物,有一种现实中过得很压抑而在幻想世界里为所欲为的报复性快感,写法也比较单一,李白则挥洒得多。他是真把万物当成了朋友——问题来了,既然是朋友,为什么还会像对待奴仆一样呼来喝去?我觉得李白的想法是,好朋友亲密无间、无所不可,不必客客气气、瞻前顾后。史书记载李白让高力士脱靴,说他蔑视权贵,我想李白一生追求功名,不至于这么矫情。他应该就是天生洒脱,不把使唤人当回事儿,对朋友也一样——如果连这都要计较,还算什么朋友?
蔡先生讲李白,还提到了一重著名公案。唐人徐凝的《庐山瀑布》“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常被视为对李白《望庐山瀑布》的效颦,东坡评之为“恶诗”,骂名流传千古。蔡先生没有人云亦云,认为徐诗虽不及李诗,“但也不是那么糟糕”,并以五十年前的亲身经历作证。我同意蔡先生——徐凝的不幸在于对手过于强悍。
徐凝的诗为什么平庸?众说纷纭。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他的比喻没有“增量”。瀑布远看像条白练,这是很贴切的。单论“像”,李白的“疑是银河落九天”反而是夸张的,不及徐诗准确。但比喻的目的并不是准确——否则不用比了,古人有云“以弹喻弹”,最符合物体形象的就是该物本身——徐诗的问题恰恰是太像了,喻体比起本体没有增加什么,比喻的意义何在?
李白的比喻好在完全是作者的主观感觉。一般认为他擅用夸张手法,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换个角度说,“夸张”未尝不是作者在某一情境中的真实感受,好比“情人眼里出西施”,外人看来是夸张,情人看来则是实情。“白发三千丈”夸张,但老人梳发而叹,觉得白发多得不得了,“三千丈”确实反映了这一刻的心理印象。“疑是银河落九天”也是如此,令人身临其境,诚如蔡先生所说,“让我们领略飞流瀑布所释放那种宇宙级的力量”,喻体比起本体,增加的正是诗人的实感。
说到比喻,蔡先生对李商隐的名作《锦瑟》之喻也有新见。他反对将《锦瑟》归为爱情诗,认为其中间二联的比喻反映的是李商隐信奉佛道的情怀。蔡先生释“沧海月明珠有泪”,引《送臻师》“昔去灵山非拂席,今来沧海欲求珠。楞伽顶上清凉地,善眼仙人忆我无”为证,说明此句是李商隐在反思自己的奉佛之情。这一见解非常精彩,值得申说。此句的意象还让人想到《碧城》的尾联“若是晓珠明又定,一生长对水晶盘”。“珠”是珍贵的象征,情人可以称“珠”,如“掌上明珠”(这一典故出自傅玄《短歌行》:“昔君视我,如掌中珠。何意一朝,弃我沟渠。”本指情人,后世多指女儿);修行的证悟见地也可称“珠”,如“心珠”(如梁简文帝《释迦文佛像铭》:“心珠可莹,智流方普。永变身田,长无沙卤。”)两者还可互通,如《五灯会元》:“贪观天上月,失却掌中珠。”这里的“掌中珠”显然与修行有关,指众生本具的佛性。
那么,李商隐诗中的“珠”究竟何指?应该两说。《送臻师》的“珠”明确是指后者;《锦瑟》《碧城》则两者皆可。在大量无题诗(《锦瑟》《碧城》取头二字为题,相当于无题)中,李商隐利用同一意象的多重内涵制造诗之复义(ambiguity)。“沧海月明珠有泪”指修行,有《送臻师》为据;指情人(亡妻?),则可从“珠有泪”一语得到证明——不是人的话怎么会有泪呢?而此句又让人联想“鲛人泣珠”的典故,在字面上也可解为珠上带泪。总之,正是通过语义的模棱,李商隐构造了“碧城十二曲阑干”般繁复多层的理解空间。
《晩笑堂竹庄画传》中的李商隐画像
李商隐诗有三大主题:政治、爱情、修行。三者的共通点是不宜直说——政治有忌讳,爱情要含蓄,修行需隐秘;而它们之间本身就有交汇。以爱情与修行为例,李商隐可能是后世所谓“泥水丹法”的修炼者,诗中多有暗示,如《碧城》“紫凤放娇衔楚佩,赤鳞狂舞拨湘弦”,下笔狂放,当代学者钟来茵指出其中典故出自房中术著作《交接经》;而李商隐诗中的女子,很可能既是情人,也是同修,如《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偷桃窃药事难兼,十二城中锁彩蟾。应共三英同夜赏,玉楼仍是水精帘。”“偷桃窃药”云云,语甚暧昧,既可指修炼,也可指交接,依“泥水丹法”奥义,两者是一回事。
李商隐常用无题诗表达这些隐秘而互有交汇的主题。无题的传统可以上溯到《诗经》,不同之处在于,“《诗》无达诂”是因为书阙有间、文献不足,李商隐则是有意隐去主旨,达到迷离惝恍的效果。这些作品就像著名的鸭兔图形,可以看成鸭头,也可以看成兔头,只是角度不同,不存在孰是孰非。蔡先生揭出其中的“修行”面相,正可打破单一化解读的局限。
李贺是对李商隐影响最大的诗人,蔡先生根据诗体分类,将李贺的七古《金铜仙人辞汉歌》放在书的最后一章。他说怀古诗一般按照“感物写情”的模式来写,李贺此诗“却借鬼神故事、奇幻的传说来怀古,通过叙事写物的细节,抽出一丝丝伤感和无法言传的情感移入神秘诡谲、鬼魅出没的意象世界之中”。此论独具慧眼,于我心有戚戚焉。
李贺怀古诗的特点,是尽量隐去历史的名相,营造现场的氛围。“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这是怀古诗的通常写法,工拙不论,叙事都离不开史书的记载。李贺则不然,他会借史书的片段,将自己的想象注入其中,使历史成为充满可感细节的场景。《金铜仙人辞汉歌》中,李贺在小序里交代了历史背景,但在正文中几乎不再提及史事,所有的描写都集中在师心独造的意象和感觉上。《公莫舞》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此诗的主题鸿门宴是咏史俗套,但李贺是这样开篇的:“方花古础排九楹,刺豹淋血盛银罂。华筵鼓吹无桐竹,长刀直立割鸣筝……”没有《史》《汉》熟典,全是想象的细节,呈现出青铜般的质感。
我觉得李贺是一个感官主义者,他无法容忍抽象的历史名相,必须要将之具体化、可感化,这使他的怀古诗风格与他人迥然不同。唯一的例外是《白虎行》,全诗充满历史名词,相当于把秦汉之际的历史复述一遍。此诗与李贺通常的风格相差过大,古人已疑其为伪作(如南宋吴正子说:“显然非长吉手笔”)。那么究竟哪种写法更好呢?很难说。有人可能会认为,既然全是想象,那还有什么“怀古”可言?但换个角度看,历史的名相只是一个个可以互相交换的标签,诗意的想象才能让“古”活过来,呈现出独一无二的特色——正如西哲所说,“诗比历史更真实”。
蔡先生此书胜义纷呈,可供发掘者甚多,限于篇幅,只能略举数例。行文至此,忽然想起去年香港棋会上聂卫平老师的一番话。有人问聂老,人类永远下不过AI,下棋还有什么意义?聂老说,有了AI,更能看清人类思维的特点。换言之,人类虽然永无战胜AI的可能,但可以转而探究棋之“所以然”。年初deepseek横空出世,所作诗词已可乱真,尽管很多诗人坚持自己写得更好,但在旁人看来,他们这么说的唯一底气来自诗歌不能像围棋一样分出明确的胜负。但人类写不过AI,并不意味着诗歌失去了意义。我们反而可以超越具体的创作之域,去探究诗歌作为一种思维的特质。其实诗性思维人人皆有,潜力巨大,开发出来对人类、对社会有极大的益处,远比诗人写诗重要。套用禅宗的话,此书探究诗之“所以然”,正是“向上一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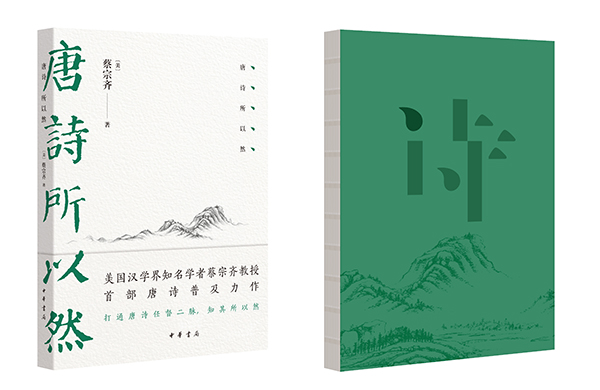
《唐诗所以然》,[美]蔡宗齐著,中华书局,2025年4月出版,312页,48.00元
读蔡宗齐先生这本书,极为畅快。首先,它不像很多同类著作,纠结于唐诗“写什么”——对诗来说,“写什么”恰恰是不重要的,关键在“怎么写”,蔡先生此书则更进一步,讨论“所以然”——唐诗为什么这么写?作者天元落子,起手便高,开篇说明本书由纵横两线构成,“纵”是时间上的形式演变,“横”是空间上的类型比较。在这一框架下,七十二首唐诗名作分属十三个主题,章法严谨,奇正相生,显示出蔡先生高超的写作技巧。
十三个主题皆富新意,益人神智。如作者讲到诗体和题材的关系,表现禅意的诗适合用五言律绝写,而咏史诗宜用七言律绝写。合书细想,这个判断真是精到,禅意和咏史都讲究滋味,不过两者相反,前者是字越少越有味,后者是字若少不够味。在第八个主题“怀古绝句:为何五言无法PK七言”中,作者认为杜甫《八阵图》写得不够好,“五绝怀古,诗圣难为”,不迷信名人名篇,极见识力。我觉得《八阵图》就是首庸作,历来关于此诗诗意的讨论极多,有人认为这是好诗的证明,在我看来正好相反——一首二十字的五绝本当以简明见长,引起这么多争议,要么是没把意思写清楚,要么就是必须由读者注入微言大义才能维持名作的地位。
进一步说,很多五言律绝咏史名作其实都写得不够好。如收入《唐诗三百首》的刘禹锡《蜀先主庙》:“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我早年读到,便觉乏味:这不就是把刘备父子的一生复述一遍么?当时有崇拜名作的心理,所以也不敢说,总觉得是自己鉴赏水平不够,而整部《唐诗三百首》,我最喜欢的七律是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干净利落的开头,颔联是绝佳的电影镜头,颈联极沧桑,一结虽是凑韵,却也不失自然。同一个作者,同样是咏史诗,为何差距这么大?
读了蔡先生的书,我似乎悟到了“所以然”——我想是因为,咏史的感情需要流露、摇曳,这是五言律绝难以胜任的。比如《西塞山怀古》颔联里的“几回”“依旧”,都是句眼,读者的心就在这几个字间飘荡,如果是五言就插不进去了。五言的感情是没有摇曳余地的,就像狭窄的空间拉不开一条横幅。它能不能安置情感?能,但这个情感是凝固的,不是摇荡的,“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凄凉”就定调了,像一个特写镜头,不会再有变化。
那么五言能不能咏好史?也不是不可以,需要把篇幅拉长,变成五古,像陶渊明《咏荆轲》:“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何等跌宕。“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又何等摇曳。越发觉得陶公是五言圣手,李杜不及。
凡事两面,五言律绝的这份含蓄正好用来书写禅意。反过来说,把表现禅意的诗写成七言如何?举个例子,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七言中类似的作品如张旭(作者有争议,不赘)《桃花溪》:“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乍看也像回事,但后者实际上仍然是情感的荡漾,最后来个问句,如山歌问答,音乐性十足。前者则极幽寂,是无声境界。《桃花溪》算是含蓄的,庸手还容易把诗写成偈,因为七言易露,禅意之诗无“情”可露,便会露出“理”来,而禅理恰恰是不可露的,“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就像香水打开盖子就会挥发。露了禅理,诗便不成其为诗,而成了“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疑”这样的宗门偈子。
说唐诗,李白自然是重头戏。蔡先生对李白也有极为精彩的见解,让我看得很激动,每看两句,就要合上书,去院子里走一走,消化一下蔡先生的思维火花。比如蔡先生讲《与夏十二登岳阳楼》,“拟人只为找玩伴”,一语点破李白的妙处。这首诗其实一般,但蔡先生所论颔联“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确实能代表李白的一种特质。我觉得长久以来对李白有个误解,认为他的特点是豪放,豪放又被片面理解为说大话。这种说法很有问题:说大话谁不会啊?如果这就是李白,微信群里话最多口气最大的那位也是李白了。遗憾的是,很多诗人是按照这个思路去学李白的。比如清代诗人黄仲则,明明诗里到处是“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这样的寒酸之语,偏要学李白做大言无忌状,让人看着很难受。
清代南薰殿藏李白画像
蔡先生揭出了李白真正的特点——以万物为玩伴。正因他以万物为友,所以显得逍遥恣肆,不受羁勒,给人以豪放之感。最具代表性的是尽人皆知的名句:“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一句话的功夫就多出两个朋友。这种热爱朋友、无中生“友”的心态,使李白非常善用拟人手法——这里的“拟人”还不只是像人,更是赋予万物以生命,正如蔡先生所引“山衔好月来”,其实是把山当成了鸟。有时李白甚至会让自己的器官飞起来:“南风吹归心,飞堕酒楼前。”“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这类极致的拟人化,是李白诗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
这是从哪儿学的?我想大概是受了屈原的启发。《楚辞》里有很多驱遣神灵的情节,比如《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吾令帝阍开关兮”“吾令丰隆乘云兮”,《九章》:“令五帝以折中兮”“吾使厉神占之兮”,《九歌》:“令飘风兮先驱”;等等,仿佛整个天地围着作者转。不过屈原驱策万物,有一种现实中过得很压抑而在幻想世界里为所欲为的报复性快感,写法也比较单一,李白则挥洒得多。他是真把万物当成了朋友——问题来了,既然是朋友,为什么还会像对待奴仆一样呼来喝去?我觉得李白的想法是,好朋友亲密无间、无所不可,不必客客气气、瞻前顾后。史书记载李白让高力士脱靴,说他蔑视权贵,我想李白一生追求功名,不至于这么矫情。他应该就是天生洒脱,不把使唤人当回事儿,对朋友也一样——如果连这都要计较,还算什么朋友?
蔡先生讲李白,还提到了一重著名公案。唐人徐凝的《庐山瀑布》“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常被视为对李白《望庐山瀑布》的效颦,东坡评之为“恶诗”,骂名流传千古。蔡先生没有人云亦云,认为徐诗虽不及李诗,“但也不是那么糟糕”,并以五十年前的亲身经历作证。我同意蔡先生——徐凝的不幸在于对手过于强悍。
徐凝的诗为什么平庸?众说纷纭。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他的比喻没有“增量”。瀑布远看像条白练,这是很贴切的。单论“像”,李白的“疑是银河落九天”反而是夸张的,不及徐诗准确。但比喻的目的并不是准确——否则不用比了,古人有云“以弹喻弹”,最符合物体形象的就是该物本身——徐诗的问题恰恰是太像了,喻体比起本体没有增加什么,比喻的意义何在?
李白的比喻好在完全是作者的主观感觉。一般认为他擅用夸张手法,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换个角度说,“夸张”未尝不是作者在某一情境中的真实感受,好比“情人眼里出西施”,外人看来是夸张,情人看来则是实情。“白发三千丈”夸张,但老人梳发而叹,觉得白发多得不得了,“三千丈”确实反映了这一刻的心理印象。“疑是银河落九天”也是如此,令人身临其境,诚如蔡先生所说,“让我们领略飞流瀑布所释放那种宇宙级的力量”,喻体比起本体,增加的正是诗人的实感。
说到比喻,蔡先生对李商隐的名作《锦瑟》之喻也有新见。他反对将《锦瑟》归为爱情诗,认为其中间二联的比喻反映的是李商隐信奉佛道的情怀。蔡先生释“沧海月明珠有泪”,引《送臻师》“昔去灵山非拂席,今来沧海欲求珠。楞伽顶上清凉地,善眼仙人忆我无”为证,说明此句是李商隐在反思自己的奉佛之情。这一见解非常精彩,值得申说。此句的意象还让人想到《碧城》的尾联“若是晓珠明又定,一生长对水晶盘”。“珠”是珍贵的象征,情人可以称“珠”,如“掌上明珠”(这一典故出自傅玄《短歌行》:“昔君视我,如掌中珠。何意一朝,弃我沟渠。”本指情人,后世多指女儿);修行的证悟见地也可称“珠”,如“心珠”(如梁简文帝《释迦文佛像铭》:“心珠可莹,智流方普。永变身田,长无沙卤。”)两者还可互通,如《五灯会元》:“贪观天上月,失却掌中珠。”这里的“掌中珠”显然与修行有关,指众生本具的佛性。
那么,李商隐诗中的“珠”究竟何指?应该两说。《送臻师》的“珠”明确是指后者;《锦瑟》《碧城》则两者皆可。在大量无题诗(《锦瑟》《碧城》取头二字为题,相当于无题)中,李商隐利用同一意象的多重内涵制造诗之复义(ambiguity)。“沧海月明珠有泪”指修行,有《送臻师》为据;指情人(亡妻?),则可从“珠有泪”一语得到证明——不是人的话怎么会有泪呢?而此句又让人联想“鲛人泣珠”的典故,在字面上也可解为珠上带泪。总之,正是通过语义的模棱,李商隐构造了“碧城十二曲阑干”般繁复多层的理解空间。
《晩笑堂竹庄画传》中的李商隐画像
李商隐诗有三大主题:政治、爱情、修行。三者的共通点是不宜直说——政治有忌讳,爱情要含蓄,修行需隐秘;而它们之间本身就有交汇。以爱情与修行为例,李商隐可能是后世所谓“泥水丹法”的修炼者,诗中多有暗示,如《碧城》“紫凤放娇衔楚佩,赤鳞狂舞拨湘弦”,下笔狂放,当代学者钟来茵指出其中典故出自房中术著作《交接经》;而李商隐诗中的女子,很可能既是情人,也是同修,如《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偷桃窃药事难兼,十二城中锁彩蟾。应共三英同夜赏,玉楼仍是水精帘。”“偷桃窃药”云云,语甚暧昧,既可指修炼,也可指交接,依“泥水丹法”奥义,两者是一回事。
李商隐常用无题诗表达这些隐秘而互有交汇的主题。无题的传统可以上溯到《诗经》,不同之处在于,“《诗》无达诂”是因为书阙有间、文献不足,李商隐则是有意隐去主旨,达到迷离惝恍的效果。这些作品就像著名的鸭兔图形,可以看成鸭头,也可以看成兔头,只是角度不同,不存在孰是孰非。蔡先生揭出其中的“修行”面相,正可打破单一化解读的局限。
李贺是对李商隐影响最大的诗人,蔡先生根据诗体分类,将李贺的七古《金铜仙人辞汉歌》放在书的最后一章。他说怀古诗一般按照“感物写情”的模式来写,李贺此诗“却借鬼神故事、奇幻的传说来怀古,通过叙事写物的细节,抽出一丝丝伤感和无法言传的情感移入神秘诡谲、鬼魅出没的意象世界之中”。此论独具慧眼,于我心有戚戚焉。
李贺怀古诗的特点,是尽量隐去历史的名相,营造现场的氛围。“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这是怀古诗的通常写法,工拙不论,叙事都离不开史书的记载。李贺则不然,他会借史书的片段,将自己的想象注入其中,使历史成为充满可感细节的场景。《金铜仙人辞汉歌》中,李贺在小序里交代了历史背景,但在正文中几乎不再提及史事,所有的描写都集中在师心独造的意象和感觉上。《公莫舞》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此诗的主题鸿门宴是咏史俗套,但李贺是这样开篇的:“方花古础排九楹,刺豹淋血盛银罂。华筵鼓吹无桐竹,长刀直立割鸣筝……”没有《史》《汉》熟典,全是想象的细节,呈现出青铜般的质感。
我觉得李贺是一个感官主义者,他无法容忍抽象的历史名相,必须要将之具体化、可感化,这使他的怀古诗风格与他人迥然不同。唯一的例外是《白虎行》,全诗充满历史名词,相当于把秦汉之际的历史复述一遍。此诗与李贺通常的风格相差过大,古人已疑其为伪作(如南宋吴正子说:“显然非长吉手笔”)。那么究竟哪种写法更好呢?很难说。有人可能会认为,既然全是想象,那还有什么“怀古”可言?但换个角度看,历史的名相只是一个个可以互相交换的标签,诗意的想象才能让“古”活过来,呈现出独一无二的特色——正如西哲所说,“诗比历史更真实”。
蔡先生此书胜义纷呈,可供发掘者甚多,限于篇幅,只能略举数例。行文至此,忽然想起去年香港棋会上聂卫平老师的一番话。有人问聂老,人类永远下不过AI,下棋还有什么意义?聂老说,有了AI,更能看清人类思维的特点。换言之,人类虽然永无战胜AI的可能,但可以转而探究棋之“所以然”。年初deepseek横空出世,所作诗词已可乱真,尽管很多诗人坚持自己写得更好,但在旁人看来,他们这么说的唯一底气来自诗歌不能像围棋一样分出明确的胜负。但人类写不过AI,并不意味着诗歌失去了意义。我们反而可以超越具体的创作之域,去探究诗歌作为一种思维的特质。其实诗性思维人人皆有,潜力巨大,开发出来对人类、对社会有极大的益处,远比诗人写诗重要。套用禅宗的话,此书探究诗之“所以然”,正是“向上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