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文化教师素养读本
楼宇烈,傅首清主编
¥58.0
中华文化教师素养读本
楼宇烈,傅首清主编
¥58.0
-
 辽史--全五册(精)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
脱脱著 刘浦江整理
¥280.0
辽史--全五册(精)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
脱脱著 刘浦江整理
¥280.0
-
 南明史(精装本)
钱海岳撰
¥980.0
南明史(精装本)
钱海岳撰
¥980.0
-
 宋书(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平装本)
(梁)沈约 撰
¥360.0
宋书(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平装本)
(梁)沈约 撰
¥360.0
-
 魏书—(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精装)
魏收著 何德章,冻国栋修订
¥510.0
魏书—(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精装)
魏收著 何德章,冻国栋修订
¥510.0
-
 史记--全五册(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精
[汉]司马迁撰 陈曦、王珏、王晓东、周旻译
¥298.0
史记--全五册(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精
[汉]司马迁撰 陈曦、王珏、王晓东、周旻译
¥298.0
-
 全元词(全三册)--中国古典文学总集
杨镰主编
¥298.0
全元词(全三册)--中国古典文学总集
杨镰主编
¥298.0
-
 金史(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精)
[元]脱脱等撰
¥540.0
金史(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精)
[元]脱脱等撰
¥540.0
-
邹鲁文化研究 贾庆超等 ¥0.0
-
 明实录 附校勘记(183册)布面精装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 黄彰健校勘
¥45000.0
明实录 附校勘记(183册)布面精装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 黄彰健校勘
¥45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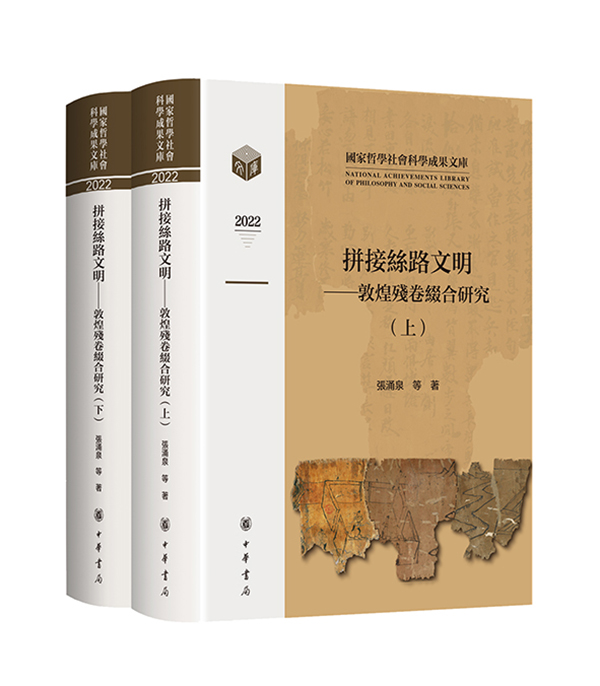
浙江大学张涌泉教授组织实施的敦煌残卷系统性缀合研究,是近年敦煌学界广受瞩目的一项大规模的学术工程。2021年3月上线的纪录片《穿越时空的古籍》,其中一期名为《拼接撕裂的文明》,即以张涌泉教授与敦煌残卷缀合为主题,播出以来广受好评。
广泛的关注源于这项工程的重要意义与突出成就。从2006年起,经过近20年的不懈努力,张涌泉教授及其学术团队在敦煌残卷缀合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缀合成果犹如火山喷发一样,一篇篇、一组组地陆续发表,提供了大量缀合实例,刷新了研究者对敦煌文献的看法,从而深化了对敦煌文化乃至中古中国的认识。2025年4月,张涌泉等著《拼接丝路文明——敦煌残卷缀合研究》由中华书局出版,对这一工程进行了阶段性总结。
一、系统性缀合取得丰硕成果
敦煌残卷的缀合工作,很早就起步了,这和敦煌文献大多为残卷、残片的特点是分不开的。一百余年前,也就是敦煌学的发端阶段,前辈们在整理研究敦煌文献、编纂敦煌文献目录的时候,就开始了零星的缀合工作。后来,很多学者都从事过这项工作。但这些缀合工作都是零星的、偶发的,都是单件文献、小专题的缀合,缺乏系统性。大规模、系统性、穷尽式的敦煌残卷缀合,始于张涌泉教授。张教授采用系统性的工作方法,首先开展文献普查,逐一摸清某一种文献的所有卷号及其特点,然后开展缀合工作。这样,就把某一文献所有可缀合的残卷、残片一网打尽,没有遗漏,所得结果就比以往更加全面完整、扎实准确。
对这一点,我个人深有体会。《拼接丝路文明》封面彩印了一件孟姜女变相,其正面为孟姜女变文,背面为变相,是一件非常典型的变文写本。它由三个残片缀合而成,分别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国图、法图的两块,我曾在2008年做过拼缀,当时和林世田老师合作撰写了一篇文章(刘波、林世田:《〈孟姜女变文〉残卷的缀合、校录及相关问题研究》,《文献》2009年第2期)。当然,我们的工作是经验式的,是凭印象完成的缀合,没有拼上俄藏那一块。随后,张涌泉教授的学生张新朋,系统地开展调查和缀合工作,拼上了俄藏部分,找齐了现存所有残片,并且依据更丰富的文本信息,发现它是从左向右读的,在文本解读方面更准确、更深入(张新朋:《〈孟姜女变文〉、〈破魔变〉残片考辨二题》,《文献》2010年第4期)。我们读到张新朋兄的论文,感到非常佩服。
这个小例子说明,系统性的工作方法非常重要,只有系统地开展缀合,才能得到完整而准确的结果。系统性缀合的成绩,无疑也远超零星的经验式工作。这是张教授主持的敦煌残卷缀合工程的最大特点,也是其突出成就的源泉。
通过《拼接丝路文明》我们看到,系统性工作的成绩是惊人的,目前缀合总量近万件三千余组,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数量。每一组缀合,都需要大量精致细密乃至繁琐枯燥的文献工作作为基础,张教授及其团队为此付出巨大努力和无穷耐心,是不难想象的。在如此大量的缀合工作的基础上,张教授得出了对敦煌文献的很多新认识,比如认为藏经洞文献的性质是道真修补佛经的材料,藏经洞是三界寺的故经处,藏经洞的封闭则与道真去世及其修补工作结束有关。这一系列观点基于大量残卷缀合并有文献记载的支持,说服力非常强,现在日益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
二、方法论意义上的启示
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张涌泉教授对敦煌残卷缀合作了方法论的总结,归纳出十二种缀合方法,即内容相邻、碴口相合、字体相同、书风近似、抄手同一、持诵者同一、藏家同一、行款近同、校注类似、残损相似、版本相同、装帧相同。此外,还提炼了缀合的操作程式,即全面普查、汇聚内容相邻写卷、考察行款书迹等各方面,最后完成缀合。这些方法和程式,来自于大量实践的总结,又经过大量实践的检验,是行之有效、可以复制的工作方法,对后续继续完成敦煌文献的系统缀合事业,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不仅如此,这套工作程式和方法,对其他文献的缀合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知道,出土文献如甲骨、简帛、吐鲁番文书,传世的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客家文书、太行山文书,甚至石刻文献及其拓片,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残损问题,竹木简还存在次序散乱需要重新编连的问题。不同文献的缀合和编连,各有其特点,不过基本的方法是相通的。张涌泉教授总结的敦煌残卷缀合程式和十二种方法,足供其他各类文献缀合参考。
三、新技术的应用
张涌泉教授主持的敦煌残卷缀合工程,还有一个方面值得称道,那就是新技术的应用。张教授和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合作,通过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和自然语言等多种高新技术,建设了敦煌残卷缀合自动缀合算法工具箱和平台。虽然计算机的工作只是提高效率的辅助手段,其结果必须要经过学者的进一步检验和研究才能确认,不过在人工智能高度发达的今天,如何结合新技术推进人文学科的研究,恐怕是未来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张教授团队是这方面的先行者,他们的探索富有参考价值。
张涌泉教授担任学术负责人的“中国写本文献数字资源库”,收录了大量敦煌文献缀合的成果。这个数据库2022年上线,从标题看贯彻了张老师大力弘扬的“写本文献学”,它收录敦煌文献3.9万余件,用数据库的形式面对全社会公布缀合研究成果,发布缀合图版,在现在主流的五六种敦煌文献数据库中,特色鲜明,学术参考价值突出。
四、一点建议
阅读本书,我常常惊叹缀合的精审无误,也常常被其中精辟的论述所打动。不过有个别看法,与本书的论述略有不同。比如关于李盛铎、刘廷琛等盗窃所得的缀合,与他们撕裂长卷以充数的卑劣做法的证据,似乎有重新考虑的必要。本书上编第四章《敦煌残卷缀合的意义》中,缀合BD03243与BD14486,认为它们“不像自然脱落(缀接处上端有人工撕裂的痕迹),很可能是刘廷琛故意撕裂而盗取有题记的部分所致”(第179页)。第一章《问题的提出》中,也谈到杏雨书屋所藏李盛铎旧藏有不少可与国 图藏卷缀合,比如羽348+BD06510、羽 261 + BD2609、BD11548+羽136等,认为“衔接处所有裂痕皆呈竖直向下之势,带有人为撕裂的痕迹”(第24页)。
众所周知,李盛铎、刘廷琛在敦煌遗书运京后,利用押运者是其亲属的便利条件,大肆盗窃,并撕裂长卷以充数,所作所为令人发指。国图所藏多有这类人为撕裂的写卷,最多的甚至撕裂为二十余段,是他们盗窃劣迹的证据。不过,对于李盛铎、刘廷琛本人所存的写卷,是否存在盗窃时人为撕裂的现象,我想还可以再考虑。他们当日盗窃写卷,时间从容,可以细加拣择,因而所获多精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未必放弃整车的较好的长卷,而自留撕裂的写卷。从犯罪心理角度分析,我想他们无疑更愿意留下更长更完整的写卷,而把撕裂充数的部分留给公藏。因此,李盛铎、刘廷琛撕裂写卷的证据,应当主要留存在国图藏卷中,公藏与私藏的缀合样例,恐怕不宜作为讨论他们盗窃行为的证据。这一点建议,请张教授团队加以考虑。
敦煌残卷的缀合,犹如愚公移山,道阻且长。《拼接丝路文明》是张涌泉教授及其团队系统工作的初步成果,也是后续进一步工作的基础。我们相信,以本书为先导,这项学术工程将会加速进行、早日完成。我们祝贺张涌泉教授及其团队的不朽成就,也期待张教授主持的《敦煌残卷缀合总集》尽快出版,更广泛地沾溉学林。
(作者为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古籍馆副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