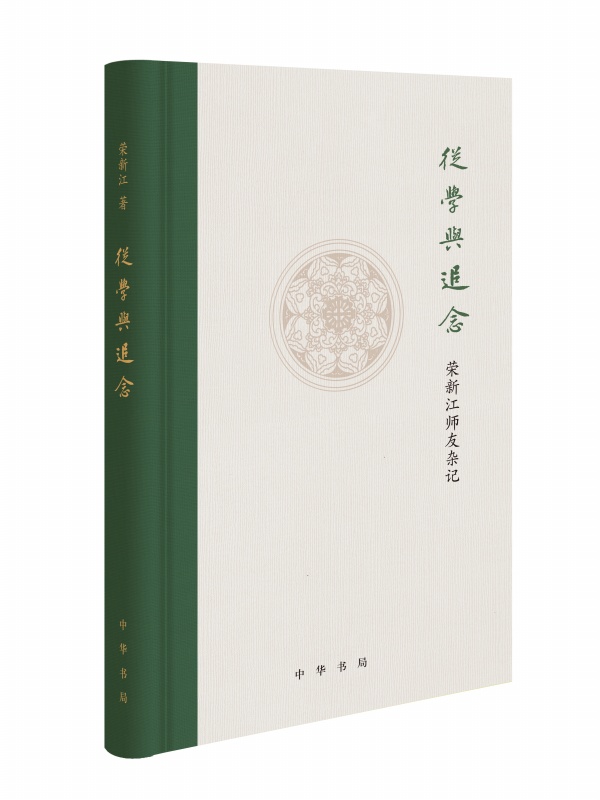
一位学者的成长史与一个时代的学术史
评论内容:
作为新三级学人(1977、78、79年入学的大学生),荣新江先生是很有代表性的。他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1982年大学毕业后又考上本系研究生,师从张广达先生学习隋唐史和中外关系史,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一直身处全国的学术中心,得到了北京大学张广达、邓广铭、季羡林、周一良、王永兴、宿白、田余庆、叶奕良等先生的指导和帮助。由于在北京工作,能够向京城及周边地区科研院所的先生们,如冯其庸、杨志玖、宁可、王尧、沙知等请益和问学。再加上他是我辈学人中赴欧美、日本及台港地区访学最多的学者之一,所以与国际学界的著名学者,如日本的藤枝晃、香港的饶宗颐、俄罗斯的李福清、马尔沙克等学者也有交流。最近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从学与追念:荣新江师友杂记》,就是他与这些学者及友朋交往的记录,既是个人从学的回忆,又有对逝者的追念;既是荣新江从一个青年学子成长为学术大家的记录,又是一个时代敦煌学学术史的珍贵史料。
一位学者的成长史
作为“新三级”学人的代表,荣新江是幸运的。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科学的春天”到来时,敦煌学方兴未艾,当时北大的一些先生们开始大力推动敦煌学研究,并成立了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辑出版了五卷《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奠定了北大在国际敦煌学界的地位。当年,王永兴、张广达先生在北大历史系开设“敦煌文书研究”课程的同时,还由他们倡导,并在他们周围慢慢“形成了一个敦煌研究的圈子,包括东语系的季羡林先生、历史系的周一良先生和宿白先生、中文系的周祖谟先生等等”(《从学与追念:荣新江师友杂记》第114页。下面引用本书只注明页码)。“北大图书馆对于王先生为主导的这个敦煌研究小组给予很大的支持,特别把图书馆的219房间,作为并没有正式名称的这个敦煌小组的研究室”,将图书馆新购进的法藏、英藏和北图的敦煌缩微胶卷,全部放在这个研究室里,同时从图书馆的书库中调集了五百多种中外文敦煌学方面的图书,包括《西域文化研究》等。因为荣新江是学习委员,也负责这个研究室,拿着这个房间的钥匙,“所以除了上课的时间,我都在这个屋子里‘值班’,这既给我浏览全部敦煌文书缩微胶卷的机会,也使我得以饱览集中到这个研究室中的敦煌学著作。不论是老师还是研究生来,都是我帮他们找到要看的那卷缩微胶卷,或者是相关的图书”(第115页)。“如果哪位老师需要找缩微胶卷中哪个号的文书,我就事先把胶卷摇到哪个号的位置,等老师来看。”(第254页)这在今天的许多青年学子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也会被认为是额外的负担。新江君却能长期坚持下来,既能方便其浏览全部敦煌文书缩微胶卷和这里的敦煌学著作,又能在帮助老师们准备缩微胶卷和图书时,获得教益,向老师们学得更多的知识。
从荣新江的论著可知,他不仅对敦煌吐鲁番汉文文书非常熟悉,而且在敦煌、西域的民族历史研究中也比较得心应手。原来一直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读了本书,才知道他还在藏文文字的学习上下过功夫。如1980年代中期跟随王尧先生学习古藏文的经历就很有启发。
为了利用敦煌藏文文献,新江君先参加了一个藏文的速成班,“一年下来,非常见效,学会了基本的文字、语法知识,翻着《藏汉大辞典》,可以读一些简单的藏文了”。但他“学藏文的目的是想看敦煌的藏文文书,这些文书是古藏语写成的,只有现代藏语的知识还无法上手。而当时对敦煌古藏文文书进行释读并翻译的学者,主要就是王尧先生和他的合作者陈践老师”。在这种情况下,他又“插班去听王尧先生的古藏语课,向他学习如何解读敦煌藏文文书”(第216页)。同时购买了王尧和陈践先生的《吐蕃金石录》《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吐蕃文献选读》《敦煌本藏文文献》《吐蕃简牍综录》等。“对照藏汉两种文本,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和学习。这样做,一方面是积累古藏文的词汇,另一方面也是把一些最基本的敦煌藏文文献熟悉起来。”(第217页)通过古藏文的学习,荣新江不但利用古藏文文献和归义军时期的敦煌汉文文书,探讨了通颊部落作为吐蕃王国在东北边境设置一级军政组织,到归义军时期又演变为部落的全过程,完成了《通颊考》一文,在《文史》和英文本《华裔学志》(德国出版)同时发表。而且对他“后来研究敦煌吐蕃时期、归义军时期的历史,以及研究于阗历史,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帮助”(第219页)。这样我们也就理解了新江君在敦煌、西域民族历史研究方面取得成绩的原因了。除了《通颊考》外,他还有《龙家考》《据史德语考》(与段睛合著)《甘州回鹘成立史论》《所谓图木舒克语中的“gyazdi-”》等文及于阗、吐火罗语研究的论著。
上世纪80年代,学生与老师的关系比较密切,学生们可以经常到老师家中去聊天、问学,而且还常常帮老师跑腿。如王永兴先生给历史系学生开设“敦煌文书研究”课程时,王先生都是用一个包裹皮兜着一堆书去教室。荣新江作为中国史班的学习委员,也就成了这门课的课代表。所以王先生每次上课时,他“就骑车先到健宅(王先生住处)去接王先生,把他要带到课堂上的书挂在车把上或驮在后座上,和王先生一起,一边聊一边走向教室,上完课再送他回去。记得冬天下雪时,我也不敢骑车,就一手提着那个大包裹,一手搀扶着王先生”(第112—113页)。当王先生来研究室看书时,“我经常把他从图书馆借的书送到他健宅的家里,因为他那时一个人住,所以后来连换煤气罐、到邮局送信发电报之类的活,都是我来帮他做的了”(第115页)。这可能是我们那个时代特有的一道风景吧!也只有与老师这样密切的近距离交流和来往中,老师才会无意中将自己的看家本领毫无保留地教给学生。人文学科的学人并不是在教室里教出来的,而是在导师的书房中聊天聊出来的。
敦煌学术史的珍贵史料
人生的许多事,大部分都是在实施过程中逐渐创造条件,或不断改善条件而完成的,很少有将所有条件准备充分才开始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著作出版非常困难的境况,今天的年青学子绝对无法想象。如《敦煌吐鲁番研究》的创办就是一例。此前,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资助饶宗颐先生,每年出版一期《九州学刊》的敦煌学专号,荣新江曾帮饶先生组稿编辑。当编辑了两期专号后,他认为这笔钱可以支持在大陆办一个专刊。1994年3月,当新江兄再次到香港后,就“与饶公商定,把原本由中华文化促进中心资助《九州学刊》敦煌学专号的经费,转到北京,单独办一份《敦煌吐鲁番研究》专刊。这就是1995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吐鲁番研究》,由季羡林、周一良、饶宗颐三位先生主编,我负责具体编务,前六卷的具体工作就是我来做的。”(第267页)但出版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甚至差点夭折的情况,一般的学人是不可能知道的。即《敦煌吐鲁番研究》到第四卷出版时,香港的资金没有到位。“几位老先生也是一筹莫展。于是,我们想到冯其庸先生,由柴剑虹出面,向冯先生汇报了情况。冯先生一口答应帮忙解决,不久就安排了一位企业家与我们编委的几个同仁开会,那位企业家听了情况说明后,溜之大吉。冯先生听说后很生气,随即自己掏腰包,给了我们出版一卷的全部经费……如果没有冯先生的雪中送炭,《敦煌吐鲁番研究》恐怕到第3卷就会夭折,那样就应了日本学者在我们创办刊物时说的一句话,‘有很多三期刊物’,就是办了三期就办不下去了。好在我们有冯先生,让我们渡过了难关。”(第247页)
作者笔下的宁可先生,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宁先生为了主编完成《英藏敦煌文献》S.6981以后的部分,让新江君协助第11—13卷的标目,当时宁先生正在住院,不顾身体,在医院每天讨论,因为探视时间的限制,宁先生让荣新江从楼房的后面翻进阳台,在病房里一天一天地工作。“我们不必用赞扬焦裕禄的话语去表彰宁先生,他其实是秉承了中国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锲而不舍,学术高于一切。”(第177页)宁可先生在学术上有许多建树,但他发表的敦煌学论文并不多。作为敦煌吐鲁番学会的领导人,“他对敦煌学的贡献,更多地体现在他参与编纂的《敦煌学大辞典》《英藏敦煌文献》等敦煌吐鲁番学会主持的大型图书成果当中”(第178—179页)。这正体现了一位学术领导人和学术组织者的责任与担当,也是值得今天的青年学子学习的。
宿白先生是考古学的大家,他的文献功夫非常深厚,对石刻文献也是烂熟于心。对莫高窟的早期营建史来说,最重要的文献就是原立于第332窟前室南侧的《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即《圣历碑》)。可惜的是该碑在1921年被流窜在莫高窟的白俄军人折断,上截碑石已佚,下截残碑现存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宿先生却在北大图书馆收藏的数万张拓本中,找到刘喜海、缪荃孙递藏的碑石未断时拓本,再利用法藏P.2551敦煌抄本,复原出原碑形式,并整理出完整的碑文。在此基础上,宿先生利用碑文所记从乐僔、法良,到东阳王、建平公,在相关的系列文章中,对莫高窟早期的营建史,做出自成体系的解说。”(第258—261页)这类学术史的重要资料,如果不是荣新江将其记录下来,可能就会湮没无闻了。
新江君是我们这代学人中走访海外敦煌吐鲁番文书收藏机构最多的学者,本书中也提供了许多这方面的信息。在《怀李福清》一文中披露,在莫斯科的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东方中心,“里面有满铁和大连图书馆的藏书。这些应当是1951年苏联红军从东北撤出时转移过来的‘战利品’,但这类图书到底有多少,值得再来仔细调查”。
敦煌文献被为是中国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敦煌壁画又被法国人称为“墙壁上的图书馆”,所以敦煌学与许多学科都有交叉。本书中的多篇文章都涉及到了相关的问题,虽然都是寥寥数语,却是画龙点睛,给人启发。如敦煌文献数量庞大,内容博杂,而且以佛典居多,“所以要从中拣选出最具学术价值的文书,除了要有雄厚的学养外,还要独具慧眼”(2页)。“东汉以来,梵书胡语流入中国,对汉语影响至巨。但自陈寅恪先生以后,治汉语史且谙梵文者不多。”(12页)现在,“敦煌学界虽然有人在研究佛典和俗文学作品时可以广泛使用汉译佛典,却很少能够熟练运用梵汉对证的方法,追本溯源”(第53页)。
我从事敦煌研究后,一直比较关注敦煌学学术史,近年又重点研究学术史,但许多学术史的信息,我还是从新江君的书中第一次知道。如沙知先生的《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是我们的案头必备书,但不知道沙先生后来利用在俄罗斯调查敦煌写本的收获和《俄藏敦煌文献》中公布的图版,“将俄藏敦煌契约文书校录补充一过,作为《补遗》,印入再版本中”(第280页)。由季羡林先生主编的《敦煌学大辞典》,自然是敦煌学子们常用的工具书,但“最主要的实际主持人是宁可和沙知先生,而催稿人则主要是沙先生”(第281页)。另外,荣新江编的《向达先生敦煌遗墨》所收向达致曾昭燏的信,因为与原件图版进行了校对,比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编《文教资料简报》上的更加可靠。沙知先生请美国友人帮忙找到曾昭燏的后人,“获得向达敦煌考察期间致曾昭燏信的所有图版”(第284页),这才有了校对精良的本子。
饶宗颐先生的学问非常广博,成果非常突出。但没有正式上过大学的饶先生,如何能产生这样巨大的学术成果,确实是一个难解之谜。本书强调的一点是,饶先生于1949年移居被认为是“文化沙漠”的香港后,“当时也很担心这里能否做学问。但后来发现,此时的香港,可以说是三国时期的荆州,在各地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某个地方如荆州,居然暂获安稳,聚集了一批天下英才,一时间学术文化也达到一定的高度。他说50年代以来的香港,正是如此,大量的人才、资金、图书都汇聚在这里,为这里的学人,提供了相当好的治学条件”(第271页)。例如,1950年代英藏敦煌缩微胶卷“一开始出售,香港一位有钱人就买了一套,提供给他做研究”,“饶公敦煌学研究首先受益于伦敦所藏敦煌缩微胶卷,然后才是到法国讲学期间系统整理敦煌曲和敦煌白画”(第272页)。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敦煌学学术史信息。
《从学与追念:荣新江师友杂记》所收各文,在当初发表时,我在不同的时期基本上都读过,现在又集中起来,全部重读一遍,印象更加深刻。以上我仅从自己比较熟悉的学术史角度予以介绍,实际上本书所涉及的知识面很广,信息量很大,值得重视,值得推荐给更多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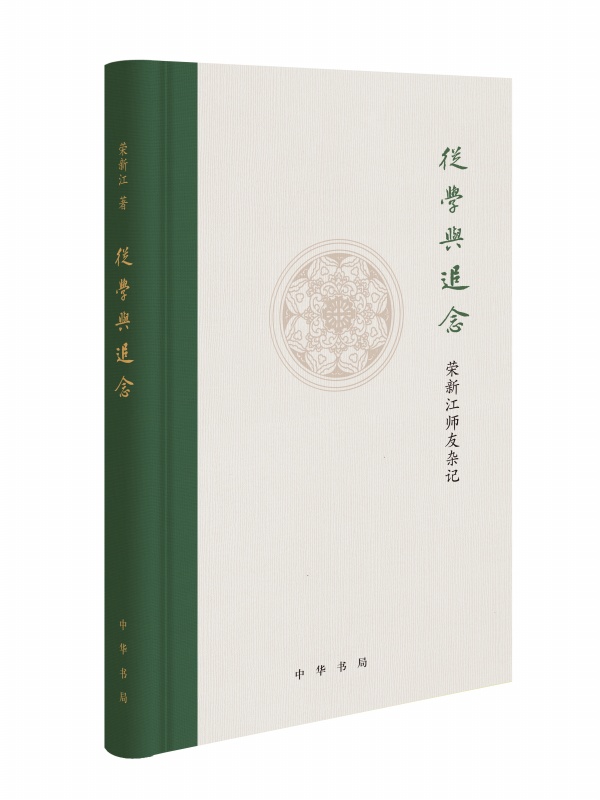
《从学与追念:荣新江师友杂记》,荣新江著,中华书局2020年9月第一版,69.00元
作为新三级学人(1977、78、79年入学的大学生),荣新江先生是很有代表性的。他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1982年大学毕业后又考上本系研究生,师从张广达先生学习隋唐史和中外关系史,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一直身处全国的学术中心,得到了北京大学张广达、邓广铭、季羡林、周一良、王永兴、宿白、田余庆、叶奕良等先生的指导和帮助。由于在北京工作,能够向京城及周边地区科研院所的先生们,如冯其庸、杨志玖、宁可、王尧、沙知等请益和问学。再加上他是我辈学人中赴欧美、日本及台港地区访学最多的学者之一,所以与国际学界的著名学者,如日本的藤枝晃、香港的饶宗颐、俄罗斯的李福清、马尔沙克等学者也有交流。最近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从学与追念:荣新江师友杂记》,就是他与这些学者及友朋交往的记录,既是个人从学的回忆,又有对逝者的追念;既是荣新江从一个青年学子成长为学术大家的记录,又是一个时代敦煌学学术史的珍贵史料。
一位学者的成长史
作为“新三级”学人的代表,荣新江是幸运的。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科学的春天”到来时,敦煌学方兴未艾,当时北大的一些先生们开始大力推动敦煌学研究,并成立了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辑出版了五卷《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奠定了北大在国际敦煌学界的地位。当年,王永兴、张广达先生在北大历史系开设“敦煌文书研究”课程的同时,还由他们倡导,并在他们周围慢慢“形成了一个敦煌研究的圈子,包括东语系的季羡林先生、历史系的周一良先生和宿白先生、中文系的周祖谟先生等等”(《从学与追念:荣新江师友杂记》第114页。下面引用本书只注明页码)。“北大图书馆对于王先生为主导的这个敦煌研究小组给予很大的支持,特别把图书馆的219房间,作为并没有正式名称的这个敦煌小组的研究室”,将图书馆新购进的法藏、英藏和北图的敦煌缩微胶卷,全部放在这个研究室里,同时从图书馆的书库中调集了五百多种中外文敦煌学方面的图书,包括《西域文化研究》等。因为荣新江是学习委员,也负责这个研究室,拿着这个房间的钥匙,“所以除了上课的时间,我都在这个屋子里‘值班’,这既给我浏览全部敦煌文书缩微胶卷的机会,也使我得以饱览集中到这个研究室中的敦煌学著作。不论是老师还是研究生来,都是我帮他们找到要看的那卷缩微胶卷,或者是相关的图书”(第115页)。“如果哪位老师需要找缩微胶卷中哪个号的文书,我就事先把胶卷摇到哪个号的位置,等老师来看。”(第254页)这在今天的许多青年学子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也会被认为是额外的负担。新江君却能长期坚持下来,既能方便其浏览全部敦煌文书缩微胶卷和这里的敦煌学著作,又能在帮助老师们准备缩微胶卷和图书时,获得教益,向老师们学得更多的知识。
从荣新江的论著可知,他不仅对敦煌吐鲁番汉文文书非常熟悉,而且在敦煌、西域的民族历史研究中也比较得心应手。原来一直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读了本书,才知道他还在藏文文字的学习上下过功夫。如1980年代中期跟随王尧先生学习古藏文的经历就很有启发。
为了利用敦煌藏文文献,新江君先参加了一个藏文的速成班,“一年下来,非常见效,学会了基本的文字、语法知识,翻着《藏汉大辞典》,可以读一些简单的藏文了”。但他“学藏文的目的是想看敦煌的藏文文书,这些文书是古藏语写成的,只有现代藏语的知识还无法上手。而当时对敦煌古藏文文书进行释读并翻译的学者,主要就是王尧先生和他的合作者陈践老师”。在这种情况下,他又“插班去听王尧先生的古藏语课,向他学习如何解读敦煌藏文文书”(第216页)。同时购买了王尧和陈践先生的《吐蕃金石录》《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吐蕃文献选读》《敦煌本藏文文献》《吐蕃简牍综录》等。“对照藏汉两种文本,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和学习。这样做,一方面是积累古藏文的词汇,另一方面也是把一些最基本的敦煌藏文文献熟悉起来。”(第217页)通过古藏文的学习,荣新江不但利用古藏文文献和归义军时期的敦煌汉文文书,探讨了通颊部落作为吐蕃王国在东北边境设置一级军政组织,到归义军时期又演变为部落的全过程,完成了《通颊考》一文,在《文史》和英文本《华裔学志》(德国出版)同时发表。而且对他“后来研究敦煌吐蕃时期、归义军时期的历史,以及研究于阗历史,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帮助”(第219页)。这样我们也就理解了新江君在敦煌、西域民族历史研究方面取得成绩的原因了。除了《通颊考》外,他还有《龙家考》《据史德语考》(与段睛合著)《甘州回鹘成立史论》《所谓图木舒克语中的“gyazdi-”》等文及于阗、吐火罗语研究的论著。
上世纪80年代,学生与老师的关系比较密切,学生们可以经常到老师家中去聊天、问学,而且还常常帮老师跑腿。如王永兴先生给历史系学生开设“敦煌文书研究”课程时,王先生都是用一个包裹皮兜着一堆书去教室。荣新江作为中国史班的学习委员,也就成了这门课的课代表。所以王先生每次上课时,他“就骑车先到健宅(王先生住处)去接王先生,把他要带到课堂上的书挂在车把上或驮在后座上,和王先生一起,一边聊一边走向教室,上完课再送他回去。记得冬天下雪时,我也不敢骑车,就一手提着那个大包裹,一手搀扶着王先生”(第112—113页)。当王先生来研究室看书时,“我经常把他从图书馆借的书送到他健宅的家里,因为他那时一个人住,所以后来连换煤气罐、到邮局送信发电报之类的活,都是我来帮他做的了”(第115页)。这可能是我们那个时代特有的一道风景吧!也只有与老师这样密切的近距离交流和来往中,老师才会无意中将自己的看家本领毫无保留地教给学生。人文学科的学人并不是在教室里教出来的,而是在导师的书房中聊天聊出来的。
敦煌学术史的珍贵史料
人生的许多事,大部分都是在实施过程中逐渐创造条件,或不断改善条件而完成的,很少有将所有条件准备充分才开始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著作出版非常困难的境况,今天的年青学子绝对无法想象。如《敦煌吐鲁番研究》的创办就是一例。此前,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资助饶宗颐先生,每年出版一期《九州学刊》的敦煌学专号,荣新江曾帮饶先生组稿编辑。当编辑了两期专号后,他认为这笔钱可以支持在大陆办一个专刊。1994年3月,当新江兄再次到香港后,就“与饶公商定,把原本由中华文化促进中心资助《九州学刊》敦煌学专号的经费,转到北京,单独办一份《敦煌吐鲁番研究》专刊。这就是1995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吐鲁番研究》,由季羡林、周一良、饶宗颐三位先生主编,我负责具体编务,前六卷的具体工作就是我来做的。”(第267页)但出版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甚至差点夭折的情况,一般的学人是不可能知道的。即《敦煌吐鲁番研究》到第四卷出版时,香港的资金没有到位。“几位老先生也是一筹莫展。于是,我们想到冯其庸先生,由柴剑虹出面,向冯先生汇报了情况。冯先生一口答应帮忙解决,不久就安排了一位企业家与我们编委的几个同仁开会,那位企业家听了情况说明后,溜之大吉。冯先生听说后很生气,随即自己掏腰包,给了我们出版一卷的全部经费……如果没有冯先生的雪中送炭,《敦煌吐鲁番研究》恐怕到第3卷就会夭折,那样就应了日本学者在我们创办刊物时说的一句话,‘有很多三期刊物’,就是办了三期就办不下去了。好在我们有冯先生,让我们渡过了难关。”(第247页)
作者笔下的宁可先生,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宁先生为了主编完成《英藏敦煌文献》S.6981以后的部分,让新江君协助第11—13卷的标目,当时宁先生正在住院,不顾身体,在医院每天讨论,因为探视时间的限制,宁先生让荣新江从楼房的后面翻进阳台,在病房里一天一天地工作。“我们不必用赞扬焦裕禄的话语去表彰宁先生,他其实是秉承了中国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锲而不舍,学术高于一切。”(第177页)宁可先生在学术上有许多建树,但他发表的敦煌学论文并不多。作为敦煌吐鲁番学会的领导人,“他对敦煌学的贡献,更多地体现在他参与编纂的《敦煌学大辞典》《英藏敦煌文献》等敦煌吐鲁番学会主持的大型图书成果当中”(第178—179页)。这正体现了一位学术领导人和学术组织者的责任与担当,也是值得今天的青年学子学习的。
宿白先生是考古学的大家,他的文献功夫非常深厚,对石刻文献也是烂熟于心。对莫高窟的早期营建史来说,最重要的文献就是原立于第332窟前室南侧的《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即《圣历碑》)。可惜的是该碑在1921年被流窜在莫高窟的白俄军人折断,上截碑石已佚,下截残碑现存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宿先生却在北大图书馆收藏的数万张拓本中,找到刘喜海、缪荃孙递藏的碑石未断时拓本,再利用法藏P.2551敦煌抄本,复原出原碑形式,并整理出完整的碑文。在此基础上,宿先生利用碑文所记从乐僔、法良,到东阳王、建平公,在相关的系列文章中,对莫高窟早期的营建史,做出自成体系的解说。”(第258—261页)这类学术史的重要资料,如果不是荣新江将其记录下来,可能就会湮没无闻了。
新江君是我们这代学人中走访海外敦煌吐鲁番文书收藏机构最多的学者,本书中也提供了许多这方面的信息。在《怀李福清》一文中披露,在莫斯科的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东方中心,“里面有满铁和大连图书馆的藏书。这些应当是1951年苏联红军从东北撤出时转移过来的‘战利品’,但这类图书到底有多少,值得再来仔细调查”。
敦煌文献被为是中国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敦煌壁画又被法国人称为“墙壁上的图书馆”,所以敦煌学与许多学科都有交叉。本书中的多篇文章都涉及到了相关的问题,虽然都是寥寥数语,却是画龙点睛,给人启发。如敦煌文献数量庞大,内容博杂,而且以佛典居多,“所以要从中拣选出最具学术价值的文书,除了要有雄厚的学养外,还要独具慧眼”(2页)。“东汉以来,梵书胡语流入中国,对汉语影响至巨。但自陈寅恪先生以后,治汉语史且谙梵文者不多。”(12页)现在,“敦煌学界虽然有人在研究佛典和俗文学作品时可以广泛使用汉译佛典,却很少能够熟练运用梵汉对证的方法,追本溯源”(第53页)。
我从事敦煌研究后,一直比较关注敦煌学学术史,近年又重点研究学术史,但许多学术史的信息,我还是从新江君的书中第一次知道。如沙知先生的《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是我们的案头必备书,但不知道沙先生后来利用在俄罗斯调查敦煌写本的收获和《俄藏敦煌文献》中公布的图版,“将俄藏敦煌契约文书校录补充一过,作为《补遗》,印入再版本中”(第280页)。由季羡林先生主编的《敦煌学大辞典》,自然是敦煌学子们常用的工具书,但“最主要的实际主持人是宁可和沙知先生,而催稿人则主要是沙先生”(第281页)。另外,荣新江编的《向达先生敦煌遗墨》所收向达致曾昭燏的信,因为与原件图版进行了校对,比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编《文教资料简报》上的更加可靠。沙知先生请美国友人帮忙找到曾昭燏的后人,“获得向达敦煌考察期间致曾昭燏信的所有图版”(第284页),这才有了校对精良的本子。
饶宗颐先生的学问非常广博,成果非常突出。但没有正式上过大学的饶先生,如何能产生这样巨大的学术成果,确实是一个难解之谜。本书强调的一点是,饶先生于1949年移居被认为是“文化沙漠”的香港后,“当时也很担心这里能否做学问。但后来发现,此时的香港,可以说是三国时期的荆州,在各地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某个地方如荆州,居然暂获安稳,聚集了一批天下英才,一时间学术文化也达到一定的高度。他说50年代以来的香港,正是如此,大量的人才、资金、图书都汇聚在这里,为这里的学人,提供了相当好的治学条件”(第271页)。例如,1950年代英藏敦煌缩微胶卷“一开始出售,香港一位有钱人就买了一套,提供给他做研究”,“饶公敦煌学研究首先受益于伦敦所藏敦煌缩微胶卷,然后才是到法国讲学期间系统整理敦煌曲和敦煌白画”(第272页)。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敦煌学学术史信息。
《从学与追念:荣新江师友杂记》所收各文,在当初发表时,我在不同的时期基本上都读过,现在又集中起来,全部重读一遍,印象更加深刻。以上我仅从自己比较熟悉的学术史角度予以介绍,实际上本书所涉及的知识面很广,信息量很大,值得重视,值得推荐给更多读者。

©2002-2027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12931号
www.zhbc.com.cn zhbc@zhbc.com.cn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邮编: 100073
www.zhbc.com.cn zhbc@zhbc.com.cn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邮编: 1000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