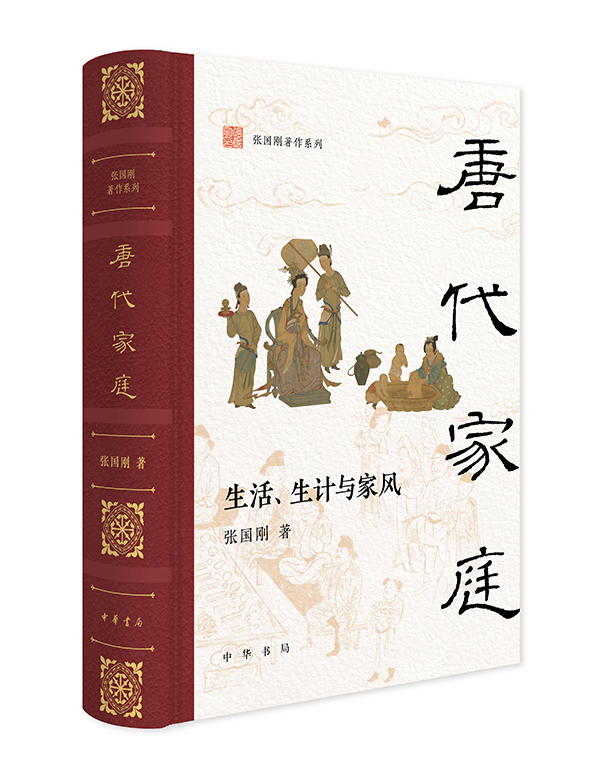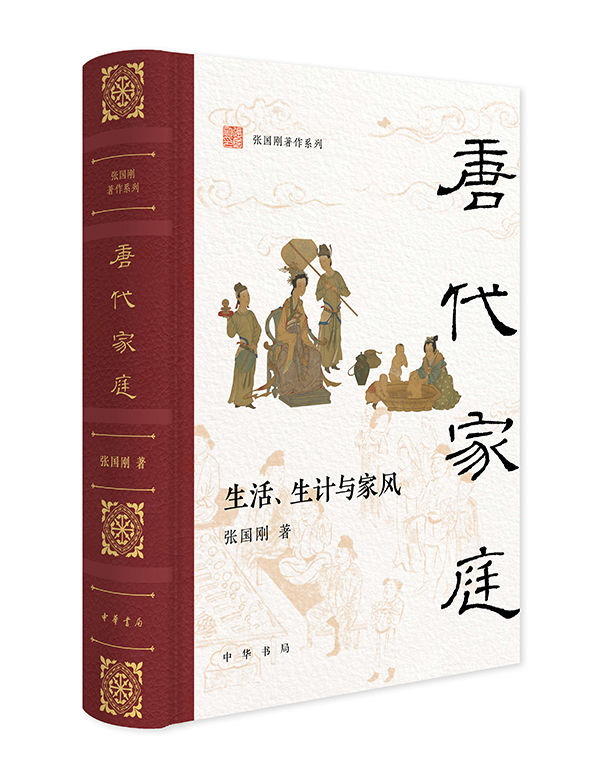
特别值得注意是,在胡人和武人家族里,符合儒家伦理的家法门风在唐代逐渐形成,这是儒家礼法文化下移的重要表现。唐代前期的武人家族以李勣家族为代表。李勣是瓦岗寨出来的武人,《旧唐书》卷六十七有一段论及其为人,前面一段说其统帅一方,行军打仗,极具领导力、亲和力,既忠且义,深得部下爱戴;后面一段是家教部分:
与弟弼特存友爱,闺门之内,肃若严君。自遇疾,高宗及皇太子送药,即取服之;家中召医巫,皆不许入门。子弟固以药进,勣谓曰:“我山东一田夫耳,攀附明主,滥居富贵,位极三台,年将八十,岂非命乎?修短必是有期,宁容浪就医人求活!”竟拒而不进。忽谓弼曰:“我似得小差,可置酒以申宴乐。”于是堂上奏女妓,檐下列子孙。宴罢,谓弼曰:“我自量必死,欲与汝一别耳。恐汝悲哭,诳言似差可,未须啼泣,听我约束。我见房玄龄、杜如晦、高季辅辛苦作得门户,亦望垂裕后昆,并遭痴儿破家荡尽。我有如许豚犬,将以付汝,汝可防察,有操行不伦、交游非类,急即打杀,然后奏知。又见人多埋金玉,亦不须尔。惟以布装露车,载我棺柩,棺中敛以常服,惟加朝服一副,死倘有知,望著此奉见先帝。明器惟作马五六匹,下帐用幔布为顶,白纱为裙,其中著十个木人,示依古礼刍灵之义,此外一物不用。姬媪已下,有儿女而愿住自养者,听之;余并放出。事毕,汝即移入我堂,抚恤小弱。违我言者,同于戮尸。”此后略不复语,弼等遵行遗言。
这里特别提到房玄龄等前高官“辛苦作得门户,亦望垂裕后昆,并遭痴儿破家荡尽”。他嘱咐弟弟李弼三条遗训:一、严格教育子孙:“汝可防察,有操行不伦、交游非类,急即打杀,然后奏知。”二、简葬:“又见人多埋金玉,亦不须尔。惟以布装露车,载我棺柩,棺中敛以常服,惟加朝服一副,死倘有知,望著此奉见先帝。明器惟作马五六匹,下帐用幔布为顶,白纱为裙,其中著十个木人,示依古礼刍灵之义,此外一物不用。”三、还有官宦人家特有的遣散遗留的姬妾:“姬媪已下,有儿女而愿住自养者,听之;余并放出。”李勣的这一套家教具有代表性。

这里面提到打杀教训不肖子孙之后,上奏朝廷,本来就是历史的典故。汉武帝时金日磾曾经因为儿子在宫中行为不检点而杀之,连汉武帝都“心敬”之。现实生活则是因为儿女的行为会连累到整个家族的兴衰。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房遗直兄弟不睦,被牵连进一场政治事变中,被素来不和的长孙无忌除掉。这是李所亲见之事。官宦人家的家教不仅是家族的事情,也牵涉到国家的兴亡。这个叫作“居官治家之法”。
唐代后期武人势力壮大,胡人家族以及武人家族却倾慕儒风,如濮阳杜氏家族。唐代濮阳杜氏出自北朝独孤浑氏的后裔,是唐代胡族儒家宗族化的代表性家族。杜暹曾任开元时宰相,“自暹高祖至暹,五代同居,暹尤恭谨,事继母以孝闻”,为官清廉,为婺州参军,“秩满将归,州吏以纸万余张以赠之,暹惟受一百,余悉还之。时州僚别者,见而叹曰:‘昔清吏受一大钱,复何异也。’俄授郑尉,复以清节见知”。杜暹“常以公清勤俭为己任,时亦矫情为之。弱冠便自誓不受亲友赠遗,以终其身”。其子取名杜孝友,谨守家法。父亲死后,玄宗谥以“贞孝”。除了皇帝的赠予外,“尚书省及故吏赙赠者,其子孝友遵其素约,皆拒而不受”。
唐代后期的武人家族以李晟为代表。李晟,陇右临洮人,“代居陇右为裨将”。他本人自幼为孤儿,却“事母孝谨”。李晟是皇室危难时节,挺身而出的大英雄,官至宰相。《旧唐书·李晟传》记载其忠贞事迹,令人动容,其中有一段云:
初,晟在凤翔,谓宾介曰:“魏徵能直言极谏,致太宗于尧、舜之上,真忠臣也,仆所慕之。”行军司马李叔度对曰:“此搢绅儒者之事,非勋德所宜。”晟敛容曰:“行军失言。传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备位将相,心有不可,忍而不言,岂可谓有犯无隐,知无不为者耶!是非在人主所择耳。”叔度惭而退。故晟为相,每当上所顾问,必极言匪躬,尽大臣之节。性沉默,未尝泄于所亲。
临下明察,每理军,必曰某有劳,某能其事,虽厮养小善,必记姓名。尤恶下为朋党相构,好善嫉恶,出于天性。尝有恩者,厚报之。初,谭元澄为岚州刺史,尝有恩于晟,后坐贬于岳州;比晟贵,上疏理之,诏赠元澄宁州刺史。元澄三子,晟抚待勤至,皆为成就宦学,人皆义之。
理家以严称,诸子侄非晨昏不得谒见,言不及公事,视王氏甥如己子。尝正岁,崔氏女归省,未及阶,晟却之曰:“尔有家,况姑在堂,妇当奉酒醴供馈,以待宾客。”遂不视而遣还家,其达礼敦教如此。
以上这一段话,体现了李晟为人的三个方面。首先是忠诚于国;其次精明治军,善于待友;再次是持家严格,尊奉礼教。李晟的家法在后来的子孙传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晟十子,宪、愬最仁孝。”

李愬就是元和时期雪夜入蔡州、平定淮西吴元济的那位大将。李愬不仅自幼善于骑射,长大善于治军打仗,而且颇有儒者之风。“始,晟克复京城,市不改肆;及愬平淮蔡,复踵其美。父子仍建大勋,虽昆仲皆领兵符,而功业不侔于愬,近代无以比伦。加以行己有常,俭不违礼,弟兄席父勋宠,率以仆马第宅相矜,唯愬六迁大镇,所处先人旧宅一院而已。”
李愬之弟李宪,“好儒术,以礼法修整”,所历官职,皆有美誉。“宪虽勋伐之家,然累历事任,皆以吏能擢用,所履官秩,政绩流闻。性本明恕,尤精律学,屡详决冤狱,活无罪者数百人。以能入官,官无败事,士君子多之。”做一个合格的官员,应该是官宦人家最重要的传承。
同时具有胡人和武人身份的还有中唐名将李光进、李光颜兄弟。《旧唐书·李光进传》对这个家庭有一段溯源:“李光进,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也。父良臣,袭鸡田州刺史,隶朔方军。光进姊适舍利葛旃,杀仆固玚而事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光进兄弟少依葛旃,因家于太原。”就是这样一个胡人血统的边将,却深度接受儒家伦理。光进的弟弟叫光颜。“光进兄弟少以孝睦推于军中。及居母丧,三年不归寝室。光颜先娶妻,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光进始娶。光颜使其妻奉管籥、家籍、财物,归于其姒。光进命反之,且谓光颜曰:‘新妇逮事母,尝命以主家,不可改也。’因相持泣良久,乃如初。”
对于李光颜,史传留下了一则轶事。攻打淮西之时,统帅韩弘有私心,意欲以一美女歌妓腐蚀李光颜:
(韩弘)举大梁城求得一美妇人,教以歌舞弦管六博之艺,饰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计费数百万,命使者送遗光颜,冀一见悦惑而怠于军政也。使者即赍书先造光颜垒曰:“本使令公德公私爱,忧公暴露,欲进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谨以候命。”光颜曰:“今日已暮,明旦纳焉。”诘朝,光颜乃大宴军士,三军咸集,命使者进妓。妓至,则容止端丽,殆非人间所有,一座皆惊。光颜乃于座上谓来使曰:“令公怜光颜离家室久,舍美妓见赠,诚有以荷德也。然光颜受国家恩深,誓不与逆贼同生日月下。今战卒数万,皆背妻子,蹈白刃,光颜奈何以女色为乐?”言讫,涕泣呜咽。堂下兵士数万,皆感激流涕。乃厚以缣帛酬其来使,俾领其妓自席上而回,谓使者曰:“为光颜多谢令公。光颜事君许国之心,死无贰矣!”自此兵众之心,弥加激励。
李光颜的一番义正辞严,不仅体现了对于朝廷事业的忠诚,也体现了对于将士的激励,更显现了自身所具有儒家伦理的教育产生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宣宗大中年间严厉教训失礼公主要谨遵士族家法门风,也同样反映了时代的趋势。
(摘自《唐代家庭:生活、生计与家风》,为方便阅读,省去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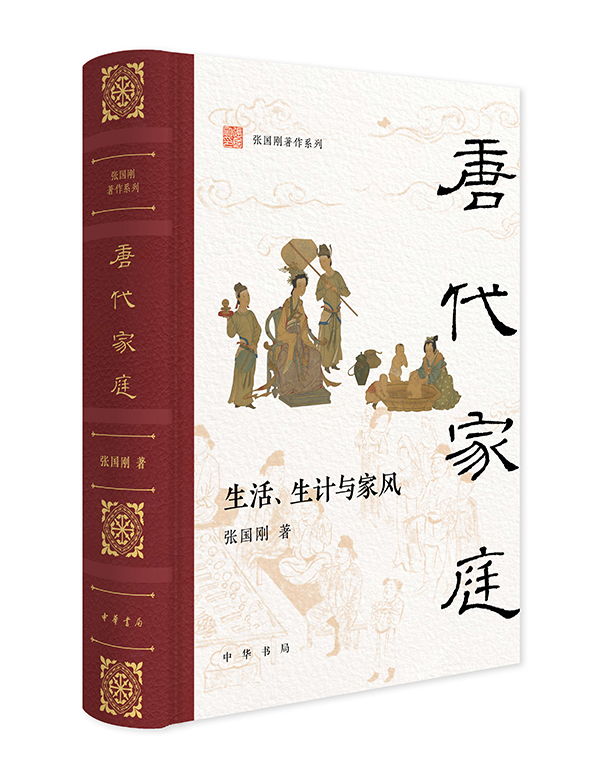


www.zhbc.com.cn zhbc@zhbc.com.cn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邮编: 10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