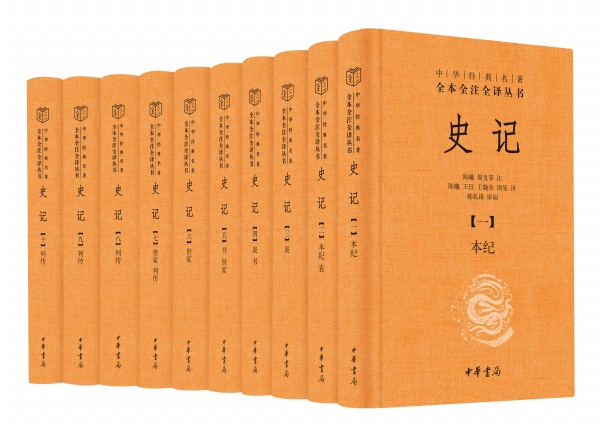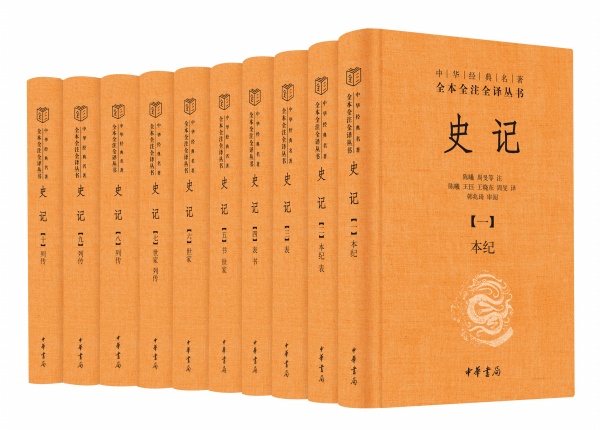
本周共读没有选《史记》完整篇章,而是截取了豫让、田横、贯高三位义士的故事——他们本都能苟活,却都选了从容赴死,核心就是想和大家聊聊:到底什么是“士”,什么是“大义”?
《刺客列传》记载了曹沬、专诸、聂政、荆轲、豫让五人,此次独选豫让,关键在于他的“义”最纯粹,且无半分外力裹挟,更贴合“士”的本真。
豫让是晋人,早年侍奉范氏、中行氏时默默无闻,转投智伯后才得“国士”之礼——智伯对他格外尊宠,这份知遇之恩,成了他后来舍命复仇的根源。智伯伐赵失败,被赵襄子联合韩、魏剿灭,赵襄子因深恨智伯,竟将其头颅漆成饮酒器。豫让遁入山中立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誓言在《汉书》与《古文观止・报任安书》中均作 “士为知己者用”,司马迁在《史记》中保留“死”字,既凸显豫让的决绝,也暗含自身对 “士不遇” 的感慨。
他的复仇从无“捷径”:第一次变名姓为刑徒,入宫涂厕藏匕首,败露后因赵襄子惜其义而获释;第二次更极端,漆身成癞疮、吞炭变哑,在街上要饭时连妻子都认不出。友人劝他“投赵襄子门下再伺机报仇”,他却严词拒绝:“既已委质臣事人,再杀之,是怀二心。我宁肯行极难之事,也要让后世怀二心的臣子羞愧!”
豫让要的从不是赵襄子的性命,而是对知己的交代,对士道的坚守。最终他埋伏桥下仍被发现,面对赵襄子“为何独为智伯报仇”的质问,豫让答:“范、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自知必死,他求赵襄子赐衣,拔剑三跃刺衣,高呼 “可下报智伯矣”后自刎。与其他四位刺客不同:曹沬为鲁国逼还土地,专诸受公子光所托,聂政收严仲子重金,荆轲承燕太子丹之命。唯有豫让,既非受命也非受雇,纯粹为报知遇之恩,这份“义”毫无杂质。
田横是战国齐国诸侯后裔,反秦战争中,他与兄长田儋、田荣共同重建齐国:田儋首称齐王,田荣后自立为王,田荣之子田广被杀后,田横继立齐王,在齐鲁大地上维系着齐国的基业。这份贵族血脉中的气节,成了他后来抉择的底色。
汉朝建立后,田横却因一桩旧怨陷入两难——此前韩信采用蒯通之计,突袭已解除战备的齐国,田横怒而烹杀刘邦派来劝降的说客郦食其,而郦食其的弟弟郦商,正是汉朝手握兵权的大将。为避祸,田横带着五百余部属逃入海岛。刘邦深知田横兄弟“本定齐,齐人贤者多附焉”,恐其日后生乱,便派使者召他回京,一边下诏严令郦商“敢动田横及随从者,灭族”,一边承诺“来则封王,小则封侯”。
可田横过不了自己的“心关”:“我烹人之兄,却与他弟同朝事主,即便他因天子之诏不敢动我,我岂能无愧于心?”行至离雒阳三十里的尸乡驿站,田横对门客说:“我曾与刘邦同为南面称孤的王,如今他为天子,我为逃亡之虏,低头侍奉他,是此生奇耻!”随即自刎,还让门客将自己的头颅献给刘邦,以证无逃亡之意。
刘邦见其头颅,感慨“兄弟三人更王,岂不贤乎”,以王侯之礼葬田横;更令人震撼的是,田横的两位门客在其墓旁挖洞自刭殉葬,海岛上的五百部属闻其死讯,也全部自杀。
田横以“宁死不辱”的骨气,赢得了士人的誓死追随,后来徐悲鸿创作《田横五百士》,正是为推崇这份跨越千年的气节。

贯高是赵国丞相,早年为张耳门客,张耳死后继续辅佐其子张敖。汉七年,刘邦从平城回京路过赵国,张敖以子婿之礼侍奉,亲端饮食、态度谦卑,而刘邦却“箕踞詈,甚慢易之”,叉着腿辱骂,毫无天子对诸侯的礼遇。
年过六十的贯高,一生重气节,见主子受此侮辱,便与赵午等几位老臣密谋:“刘邦无礼,我们替大王杀了他!”张敖急得咬指出血,严词劝阻:“我家先祖亡国,赖高祖才得以复国,今日所有,皆高祖之力,不可忘恩!”贯高当即与同伙约定:“此事我们私自谋划,事成则功归大王,事败则我们独担罪责,绝不能连累大王!”
汉八年,刘邦从东垣回京再经赵国,贯高等人在柏人县驿站将刺客藏于夹墙中,准备伏击刘邦,却因刘邦“心动”问出“柏人者,迫于人也”,察觉异常后未留宿,计划失败。汉九年,贯高的仇家得知此事,向朝廷告发谋反,刘邦下令逮捕张敖与贯高等人。同伙们纷纷欲自杀,贯高怒骂:“你们死了,谁来证明大王未曾参与?”
到长安后,贯高被“吏治榜笞数千,刺剟,身无可击者”,却始终咬定“独吾属为之,王实不知”。刘邦起初不信,吕后也曾为张敖求情,刘邦怒曰:“使张敖据天下,岂少而女乎!”后来廷尉将贯高的供词上报,刘邦叹其为 “壮士”,派中大夫泄公持节前往审问。泄公以旧友之礼慰问,贯高坦言:“人情宁不各爱其父母妻子?今吾三族皆以论死,岂以王易吾亲哉!顾为王实不反,独吾等为之。”
刘邦得知真相后,赦免了张敖,也因欣赏贯高坚守诺言而欲免其罪。但贯高却说:“我活着只为证明大王无辜,如今大王已免罪,我身负弑君之名,何面目再事上哉!”随即“仰绝肮”而死。
贯高护主却不越界,以死明臣节,恰是“士”坚守底线的典范。
读这三个人的故事,其实答案很明显:
“士”不是身份,是心里的规矩。豫让守“知遇必报”的规矩,田横守“无愧于心”的规矩,贯高守“不连累主”的规矩。
“大义”也不是大道理,是哪怕死,也不丢这些规矩。
他们本都能活:豫让能投靠赵襄子,田横能接受封侯,贯高能接受赦免,但他们都选了死——因为在“士”的眼里,苟活比死更难,无愧于心比活着更重要。这就是司马迁想通过他们告诉我们的“士之大义”。而我们今日的共读,正是在与古人的对话中,重新理解这份精神的重量。
它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坚守道义、无愧于心,永远是人格的底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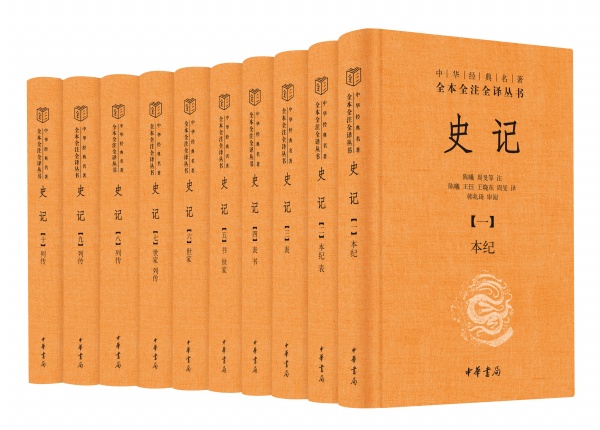

www.zhbc.com.cn zhbc@zhbc.com.cn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邮编: 10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