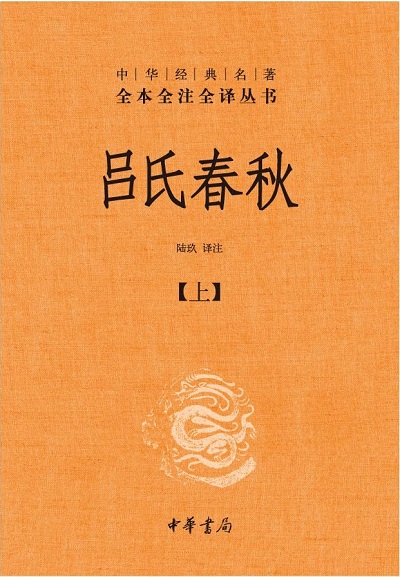
战国末年至西汉初年,天下刚从诸子百家各执一词的纷乱局面中走出——诸侯征战日久,统一王朝亟需确立治理规矩,读书人不再局限于闭门论学,开始思索如何以学识助力治国。就在这一转折期,两个人分别推动了两场大规模的著书工程:秦国宰相吕不韦,召集门客编撰《吕氏春秋》;淮南王刘安,汇聚宾客著成《淮南子》。
同为“主事者统筹、众人合力”的集体著作,二者结局却判若云泥:《吕氏春秋》随吕不韦失势而被束之高阁,《淮南子》虽因刘安涉谋反而遭禁,其思想却流传两千年而不辍。
两部书之间有何共性,又有何差异?
先说共性:皆为应运而生的治国思想集成
吕不韦与刘安,都跳出了诸子单打独斗的著述传统——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弟子辑录《论语》是传述师言,老子撰写《道德经》是独抒己悟,而这两位却选择集结众人之力著书,且目标一致:为治国者提供一套可行的治理思路。
第一,均为汇聚众智而成的鸿篇巨制。
吕不韦本是卫国商人,凭借“奇货可居”的策略扶持秦国公子嬴异人上位,最终官至宰相。他深知,仅靠权位不足以稳固根基,还需一套系统化的治国理念支撑。于是,他召集门客叮嘱:“你们所知所学,皆可著录成书。”数百位门客完成初稿后,吕不韦亲自梳理整合,将内容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纪”对应十二个月的时令,暗含治国需顺天时的逻辑;“览”聚焦天下大事,阐述君臣相处之道;“论”则深入辨析事理,探讨修身与治国的关联。最终形成二十六卷的《吕氏春秋》,体例完备,内容厚重。


战国末年,单一学派的思想已难以适配复杂的治国需求:儒家倡导仁政,却对军事治理着墨不足;法家强调严刑峻法,却易因严苛引发民怨;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却缺乏具体的施政方案。吕不韦编撰《吕氏春秋》时,秉持“兼收并蓄,以备采择”的原则吸纳百家:借鉴道家“天道圆,地道方”的观点,确立治国需循规律的基调;采纳儒家“必务本而后末”的理念,强调优先发展农业、再兼顾其他产业;吸收法家“刑过不避大臣”的主张,提出严格执法的原则。
刘安的整合则更具系统性,他以道家“道”为核心框架,将其他学派思想有序融入。如儒家提倡的仁义,被他界定为“治之本”,且需符合“道”的运行规律;法家重视的法律,被他定位为“天下之公器”,却不可背离“道”所蕴含的仁心;即便阴阳家关于日月星辰运行的学说,也被他纳入《天文训》,视作“道”在自然领域的体现。二人都清醒地认识到:治理大一统的天下,不能拘泥于一家之言,需博采众长方能行之有效。
第三,皆以服务治国实践为根本目标。
吕不韦编撰《吕氏春秋》时,秦国已濒临统一六国,他担忧秦国若仅依赖传统的法家治术——动辄严刑峻法——难以实现长治久安。因此,他希望通过这部书向秦国统治者传递“德刑并用”的理念,为王朝制定长远的治理规矩。书中“一则治,异则乱”的表述,便是暗劝秦始皇需推动思想统一,以稳固统治。
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矛盾尚未完全消解,而汉武帝初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转向,与汉初长期奉行的黄老无为思想形成交锋,单一思想治国的趋势引发担忧。身为宗室诸侯的刘安,为应对时代治理难题,召集门客融合道、儒、法等诸家思想,编撰《淮南子》以提出兼顾稳定与灵活的治国方案。
再看本质差异:从编纂立意到思想体系
吕不韦编书,政治功利性更强,旨在为政绩立言,巩固个人权位;
刘安编书,学术理想色彩更浓,意在为时代立论,留存思想精华。
吕不韦身居宰相之位,内心却始终存有不安:他身为“客卿”,并非秦国宗室,既遭本土贵族轻视,又面临秦始皇亲政后收回权力的压力。对他而言,《吕氏春秋》是巩固权位的双重工具:一方面可向秦国证明自己具备治国远见,另一方面能借这部书招揽天下人才、彰显自身权威。因此,他策划了“一字千金”的举措:将书悬挂于咸阳城门,宣称“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他深知,无人敢轻易改动此书——这并非单纯彰显典籍的严谨,实则是借此举强化自己在秦国的话语权。

刘安的出发点则截然不同,他对学术有着发自内心的热忱。史书记载他“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府中宾客多为潜心治学的士人方术之辈,而非追逐功名利禄的政客。他编撰《淮南子》,一方面是担忧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政策会导致其他学派思想失传,另一方面是想将自己对治国、宇宙的思考系统记录下来。书成之后,他并未像吕不韦那般大肆张扬,仅是作为私藏典籍留存,直至他去世后才被献给朝廷。一个将书视作权力的筹码,一个将书当作思想的载体,二者的立意高下立判。

《淮南子》的“杂”,则是在核心思想统领下的有序整合。它始终以道家“道”为根本:提及“无为”,并非指“无所作为”,而是“循理而举事”——即君主需遵循客观规律,同时让臣子充分发挥才能,这实则融合了道家的自然观、儒家的为政以德与法家的任人唯贤;谈及“法治”,也并非法家主张的“严刑峻法”,而是强调“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为治也”,认为法律是治理的工具,而非根本,需符合“道”的精神。若将思想比作珠子,刘安是以“道”为线,将各家观点串联成完整的项链;吕不韦则未找到主线,仅将珠子随意堆放。
书的命运虽与主事者荣辱紧密绑定,但其思想的内在价值,最终决定了它们能否穿越时空。吕不韦后来因牵涉嫪毐之乱被罢官,最终饮鸩自尽——《吕氏春秋》也随之遭遇冷遇,被秦国朝廷束之高阁。秦朝最终仍选择以法家思想治国,《吕氏春秋》中“德刑并用”的理念未能得以实践,其价值主要局限于学术领域。
刘安的结局更为惨烈,他因被诬告谋反而自杀,《淮南子》也一度被列为禁书。但值得关注的是,这部书的思想并未因此湮没:汉武帝虽推行“独尊儒术”,但汉宣帝后来提及“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时,其中“王道”的内涵,便暗含《淮南子》中“仁政”与“无为”相融合的思想;东汉王充撰写《论衡》,批判谶纬神学的批判精神,也受到《淮南子》的启发;甚至“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神话故事,也因《淮南子》的记载得以流传。一个是“人亡书废”,一个是“人亡书存”,根本差异在于其思想体系是否具有超越时代的生命力。
吕不韦与刘安,都试图通过集体著书为国家探寻治理路径。然而,吕不韦更着眼于当下的政治布局,使《吕氏春秋》难免成为其权力事业的延伸;而刘安则更致力于思想的传承与创新,使《淮南子》最终超越了个人命运,成为不朽篇章。如今重读这两部书,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古人的编书模式,更能领悟到:整合多元思想,需先确立核心主线;践行理想抱负,应少些功利之念。



www.zhbc.com.cn zhbc@zhbc.com.cn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邮编: 1000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