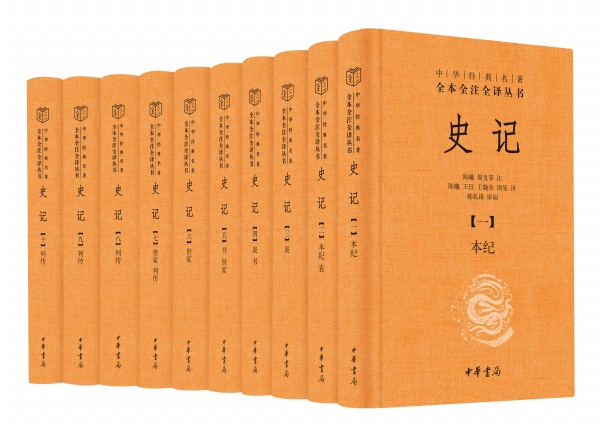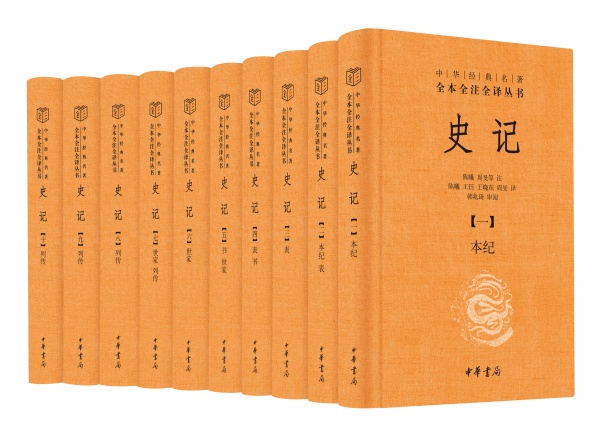
昨日共读《史记・萧相国世家》,我们不仅梳理了文中13段脉络,更学会以《史记》“互见法”解锁更立体的萧何——他的功绩、猜忌与生存智慧,散落在多篇章的勾连中,藏着汉初君臣博弈的深层逻辑。
《萧相国世家》勾勒了萧何一生主线,但要读懂他,需串联《史记》其他篇章:《淮阴侯列传》补充了“荐韩信”的关键细节,世家仅一句“何进言韩信”,列传却显其“月下追贤”的魄力,补全其“识才”底色;《曹相国世家》中“萧规曹随”,印证了“萧何律”的长远性,世家提及的“作律九章”不再单薄;《高祖本纪》则藏着二人早期羁绊——刘邦微末时,萧何“数以吏事护之”,送役卒咸阳时独多赠钱二,沛县起义时因“恐秦灭族”推刘邦为领袖,这些细节解释了刘邦对萧何“既信且疑”的根源。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等补充了萧何封侯、食邑的变迁,让“酂侯”的特殊性更清晰。可以说,世家是“主线”,其他篇章是“支线”,唯有融会贯通,才能见其从“秦吏”到 “汉相”的蜕变。
第二批封侯却居首:“万世之功”胜“一时之勇”
汉初论功行封时,萧何虽非第一批封侯(高祖六年十二月首批,萧何次年正月封),却终列“功臣第一”,核心在其功绩是“定天下之基”,而非武将的“取天下之勇”。
群臣曾质疑:“吾等身被坚执锐,攻城略地,萧何徒持文墨,何以居上?” 刘邦以 “猎狗猎人”喻答:“追杀兽兔者为狗,发踪指示者为人——诸君是‘功狗’,萧何是‘功人’。”关内侯鄂千秋更点破关键:曹参战功是“一时之事”,楚汉相争五年,刘邦屡败,若非萧何从关中“遣军补阙、转漕供粮”,刘邦早已覆亡;即便刘邦“数亡山东”,萧何仍“全关中以待”,此为“万世之功”。反观曹参,少之百数,汉亦无损。
此外,萧何“举宗数十人随汉”的忠诚,远超群臣“独身相随”,这份托付让刘邦动容。正是“万世之功”与“举宗之忠”,让他获 “功臣第一”,享 “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 的殊荣。
同乡相爱相疑:皇权与相权的必然博弈
萧何与刘邦的“相爱相疑”,非个人恩怨,而是封建皇权与相权的博弈底色。
“相爱”源于萧何的“不离不弃”:刘邦微末时他“护持左右”,起义后甘居辅佐,对峙荥阳时守关中、定法令、建宗庙,以“镇后方、固根本”之功成刘邦依赖的“基石”——即便萧何下狱后,刘邦仍需借其“贤名”挽回民心。
“相疑”则源于刘邦的“帝王心术”与萧何的“功高震主”:刘邦出身布衣,极忌“得民心者”,萧何守关中十余年“民皆附之”,让他恐其“倾动关中”。这种猜忌爆发三次:荥阳对峙时,刘邦“数遣使慰劳”探动向,萧何“遣子侄从军”才解疑;韩信死后,刘邦封其为相国加卫队,实则提防,萧何“让封捐财佐军”方安;平黥布时,刘邦又“遣使问其所为”,萧何“买田自污”才获宽心。
最典型的“为民请地”事件更露本质:萧何请开放上林苑给百姓耕种,刘邦却诬其“受贾人财”下狱,直至王卫尉点破“萧何守关中时若反,关以西非汉有,岂会贪贾人金”,才释之。可见“相爱”是因 “需要”,“相疑”是因“惧失权”,这是封建君臣的宿命。
同是“将相和”,廉颇蔺相如故事家喻户晓,萧曹却鲜为人知,核心在“故事张力”与“主题指向”的差异。
从冲突感看,廉蔺之“和”是“对立到和解”的戏剧性转折:廉颇因蔺相位居上“欲辱之”,蔺相如 “先国后私” 避让,终换廉颇 “负荆请罪”,这种 “针锋相对—退让— 悔悟” 的节奏,充满情感碰撞,易共鸣;而萧曹之“和”是“有隙却相知”的默契 —— 二人 “微时善,为将相后有隙”,却无公开冲突,萧何临终荐曹参,曹参闻其死 “即治行赴任”,上任后“一遵萧何约束”(萧规曹随)。这份君子之契,虽显智慧,却无激烈冲突,难成典故。
从主题指向看,廉蔺之“和”关乎“国家存亡”:战国时赵国危在旦夕,将相不和则国灭,其 “牺牲精神” 易被推崇;萧曹之“和”关乎“制度延续”:汉初天下已定,二人默契是为避免政策动荡,这份 “治世智慧”缺“乱世救国”的紧迫感,传播力自然较弱。
汉初封侯者多“传数世而废”,唯独萧何的“酂侯”爵位“四世失侯,天子辄复求其后”,甚至与两汉相终始,核心因萧何是汉室“制度根基”与“功臣标杆”的象征。
其一,他是“立国之本”:收秦律令图书让刘邦知天下虚实,作《九章律》定汉朝法制,守关中建统治秩序,其“万世之功”无人可代,复封酂侯是汉室“不忘奠基者”的宣告;其二,他是 “功臣标杆”:萧何功高却“自污保身”,“置田宅居穷处,不治垣屋”,这份“功高不骄、权重不专”,是汉朝希望后代功臣具备的品质,复封是传递“忠诚者得久安”的信号;其三,他是“稳定工具”:汉初功臣多为同乡或降将,萧何作为“功臣之首”,其后代待遇直接影响集团心态,复封酂侯可安抚功臣,稳固统治根基。
成功偏爱有胆略者:机会人人有,能抓者寥寥。沛县起义时,萧何、曹参因 “恐秦灭族” 避领袖之责,刘邦却以“敢冒险、勇担责” 的胆略,把握住逐鹿天下的机会。
君臣猜忌藏权力本质:放弃做君,便需修 “为臣之道”。萧何守文臣本分,以政务能力立足;曹参从文吏转型武将,二人皆以调整适应君臣规则,避祸安身。
“在其位”与“谋其政”相辅相成:《论语》“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有片面性。萧何 “在其位则谋其政”(守关中、定法令),又 “谋其政而得其位”(因 “镇国家、抚百姓” 之才任丞相),二者互为支撑。
君在外则相易被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反面,是君主亲征时,留守丞相易遭猜忌。刘邦抗楚、征陈豨、平黥布时,三次试探萧何,皆因后方稳定关乎前线胜负,君主恐失权。
萧何的一生,是汉初功臣的缩影:有幸以文吏成开国相,功绩传世;却不幸陷封建皇权猜忌,需步步为营。他的存在,不仅是“功冠群臣”的象征,更藏着汉室“功臣与皇权共生”的理想模式——这或许是司马迁为他作世家,让他“声施后世”的深层原因。
同学们对课代表的领读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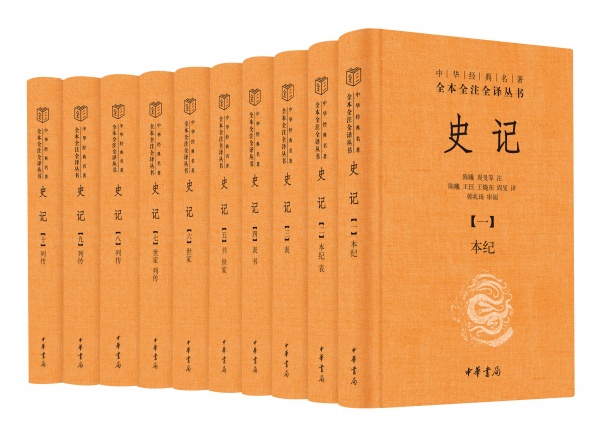

www.zhbc.com.cn zhbc@zhbc.com.cn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邮编: 10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