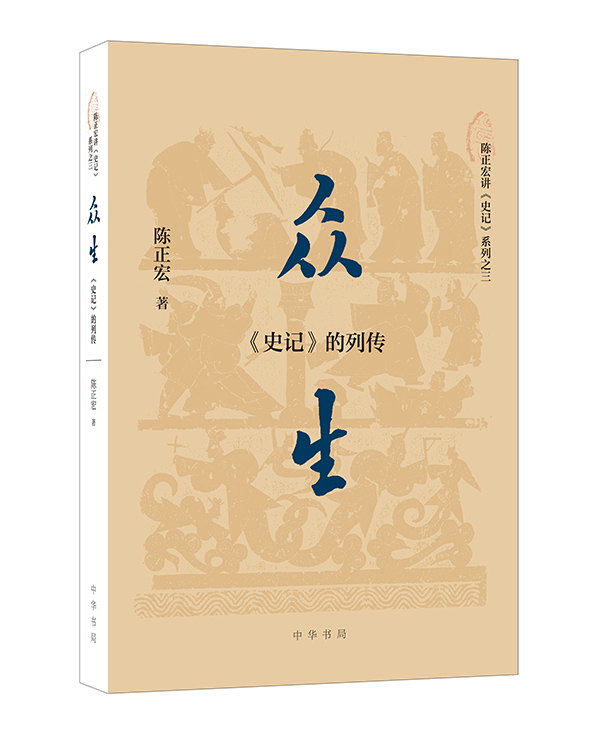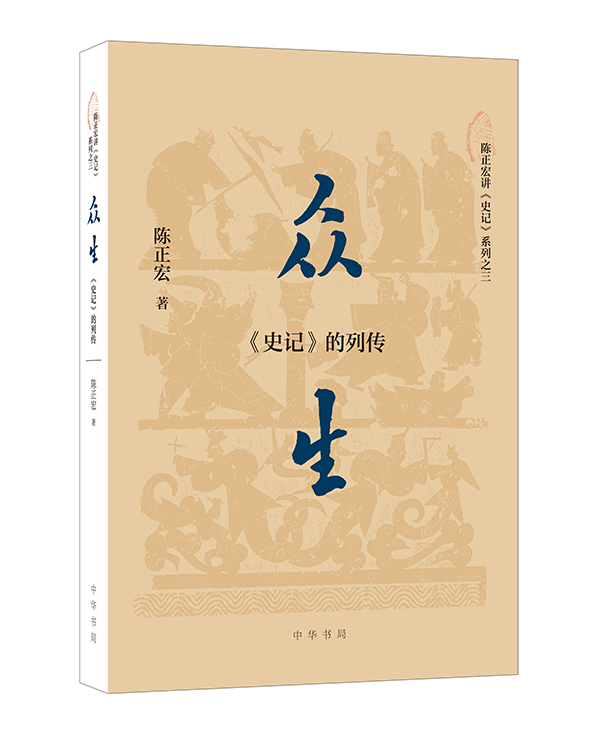
《史记》的《循吏列传》所写的,是“循吏”这样一类特殊的人群。“循吏”的吏,就是官吏的吏。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古代,很长的时间里,官和吏,是两种不同的人,官是官员,吏则是公务员,在传统社会里,那是两个互为关联,却很不相同的阶层。但是,在司马迁的时代,官和吏这两个词,却还没有那样明确的阶层指向,在很多时候,它们指的是同一个阶层,所以《史记》的这篇《循吏列传》,其中的吏,就是官;从篇中所举的例子看,那些吏,还大都是丞相一级的高官。
那么什么是“循吏”呢?《循吏列传》开卷就是一段“太史公曰”,可以看作是司马迁本人对“循吏”的一个基本解释。这段“太史公曰”是这样说的:
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
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法令是用来引导民众的,刑罚是用来禁止奸邪的。即使文的法令和武的刑罚都不具备,善良的民众还是有所畏惧而注重自身修养,是因为官僚阶层还没有乱。官员奉公守职,处事依循常理,也可以成就国家和地方治理,哪里一定要施行威仪严刑才行呢?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司马迁所谓的循吏,就是“奉职循理”的官员,简单地说,也就是守规矩、有底线的官员。
这样的官员,司马迁在《循吏列传》里写了五位,依次是楚国的孙叔敖、郑国的子产、鲁国的公仪休、楚国的石奢和晋国的李离。这五位都是春秋时候的名臣,《循吏列传》所记他们的事迹,有不少跟司马迁之前的一部西汉名著《韩诗外传》所记相似。

这五位循吏中,名气最大的是大家相对熟悉的郑国丞相子产。但在《循吏列传》里排次第一,司马迁花笔墨也最多的,不是子产,而是楚国丞相孙叔敖。
据《循吏列传》记载,孙叔敖原本是楚国的一个普通读书人,碰到了一位贵人,把他引荐给楚庄王,让他接自己的班,做楚国的丞相。结果这位孙叔敖丞相才上任三个月,楚国就出现了举国上下和谐团结的可喜景象,百姓都以生活在楚国而倍感快乐。
接着《循吏列传》的孙叔敖传部分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庄王改革货币制度,百姓不便,商界体验槽糕,很不适应,孙叔敖体察下情,劝楚庄王回归旧制,终于使市场复归平静;另一个是孙叔敖运用迂回战术,帮助楚庄王实现交通运输制度改革。这第二个故事涉及楚国当时的车制和门规,需要作一点解释。
说是楚国老百姓的习俗是喜欢“庳(bì)车”,也就是底盘低矮的车。楚王呢,认为这种底盘低矮的庳车对拉车的马来说很不方便,所以就想发个文件,让全国都把车改成高底盘的车。这个时候丞相孙叔敖就出来劝楚王,说:“文件发了很多,老百姓都不知道走哪条路了,这样不好。大王您要是一定要推行高底盘的车,为臣我向您请求,让我教城乡各处让他们把门梱(kǔn)加高。乘车的人都是君子,君子不会经常下车的。”楚王一听,哎,这主意不错,就同意了。过了半年,孙叔敖的办法果然奏效,老百姓都自个儿把车的底盘加高了。

《循吏列传》里的这个故事,逻辑是很清楚的。但问题还是有,而其中的关键,就在那个“梱”字上。
什么是“梱”?一般的解释,“梱”就是门槛。但是如果“梱”就是门槛,那么门槛增高之后,无论车的底盘增高多少,车还是过不去,因为车是要靠车轮前行的,而在有高门槛的门跟前,除非撤了门槛,车是不可能翻越的。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梱”呢?我们查一查东汉许慎编的著名字典《说文解字》,就可以知道,在汉代,梱、橛、图片(niè),这三个汉字,在指称与门相关一个构件上,意思是相同的;门梱、门橛和门图片,指的都是同一样东西,就是竖在大门中央的短木。
在楚国,这根竖在大门中央的短木,原本应该是很低矮的,所以楚国百姓喜爱的底盘低矮的车,可以畅行无阻;后来楚王采纳孙叔敖的建议,加高了城乡门楼前原本低矮的门梱,这就倒逼楚人的车辆,不得不加高底盘,否则车主人坐车到门前,就不得不下车,由人抬着车过门梱了。
楚庄王时代是春秋中叶,当时低矮的“庳车”,现在已经难觅踪影了。但之后被加高了底盘的高车,今日楚国考古中屡有发现,像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晚期楚墓二号墓二号坑2号车的轮径有118厘米,淮阳马鞍冢战国楚墓出土的车辆轮径有136和146厘米,可见孙叔敖的极具智慧的建议在楚国实现的普遍程度。
而最堪玩味的,是《史记·循吏列传》里所记的孙叔敖的这个故事,背后还有一个一般人不知道的背景,那就是《荀子》的《非相》篇里所写的一段话:“楚之孙叔敖,期思之鄙人也。突秃长左,轩较之下,而以楚霸。”意思是楚国的孙叔敖,是期思这个地方的一个下等人,头上秃发,左臂还比右臂长,人很矮小,比车前的直木和横木都要矮,就是这么一个其貌不扬的人,却让楚国称霸一方。如果《荀子》的这段话是纪实的,那孙叔敖应该是坚持保留“庳车”的低底盘,才是最合乎自身出行特性的逻辑选择,但他居然选择了相反的对自己不利的方向。而如果我们把《荀子·非相》篇里描写孙叔敖长相的那四个字“轩较之下”,跟《循吏列传》所记孙叔敖主动献计增高门梱,改良“庳车”,两者结合起来看,这位小个子的春秋循吏形象,是不是又高大了几分?

所以太史公在《循吏列传》孙叔敖传的末尾,借了传说中孙叔敖的丞相官位三次得到又三次失去的传说,特意发议论,说孙叔敖最大的本事,是“不教而民从其化”,也就是并没有发布什么行政命令,老百姓就自觉地跟随他指引的路线走了——为什么孙叔敖能有如此大的能耐?就是因为他不自私,守规矩,有底线。
《循吏列传》所记的这五位循吏中,最好玩的是鲁国博士公仪休。
公仪休也是一位丞相,鲁国的丞相。按照《循吏列传》的说法,他的为官主张,是“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就是拿国家工资的官员,不能跟下面的老百姓争利;获得了利益大头的一方,不可以再榨取小的一方。
这位公仪休丞相最有意思的故事,是因为喜欢吃鱼,有人拿了鱼来作为礼物相赠,他却不接受。对方纳闷了,说:“我是听说您老特别喜欢吃鱼,才送您鱼的,您干嘛不接受呢?”丞相的回答很有水平,说:“正因为我特别喜欢吃鱼,所以不能接受你的赠品。现在我做着丞相,自个儿就供得起鱼;今天我要是接受你送的鱼,而被免了丞相,那以后还有谁会再来给我供鱼呢?所以我是不能接受你送的鱼的。”
公仪休的话,是说得很轻松的。但他背后的指向,却是十分地严肃。因为它同样显示了个人守规矩、有底线的为官境界。

《循吏列传》所记的五位循吏中,引起后世争议的,是名列最后两位的石奢和李离。
石奢是楚昭王时代的丞相,平时为人刚正廉洁正派,从来不阿谀奉承,也从不回避问题。有一回石丞相到下面视察工作,半路上遇到了个杀人犯,这丞相大人也加入到了追犯人的行列里。犯人最后是逮着了,不过不是别人,就是石丞相他爸。怎么办呢?这位石奢石丞相的做法是:放了老爸,但把自己抓起来;同时派人代他向楚王汇报,自我检讨,说自己不忠不孝,罪该万死。楚王呢,自然是放他一马,说:“你追了犯人,但没追上,不该判罪,你就干你的正事吧。”没想到这石奢回复楚王说:“不隐藏自己父亲的过失,不是孝子;不遵奉君王的法律,不是忠臣。大王您赦免了我的罪责,那是主上的恩惠;但我甘愿伏法而死,是做臣子的职责。”最后他竟然不接受楚王的命令,自己抹脖子自杀了。
李离的故事,跟石奢颇为相似。说这位李先生,是晋文公时代负责司法刑狱的长官。因为误听传闻而错杀了人犯,就把自己抓起来,要判死刑。晋文公得知后,说:“官有贵贱,罚有轻重。下属有过错,不能算是你的罪责。”李离却说:“为臣我是一众司法官员的领导,但并没有让位给下属;工资也很高,但并没有跟下属分享奖金。现在因为误听传闻而错杀人犯,却要把罪责推给下属,这是从未听说过的事。”坚决不接受晋文公的命令。晋文公不高兴了,反问李离:“你既然认为自己有罪,那寡人我是不是也有罪啊?”李离呢,典型的一根筋,说:“理有法,失刑则刑,失死则死。文公您因为臣下我能听微决疑,所以让我做司法刑狱长官。现在误听传闻错杀人犯,罪就该死。”最终还是不接受晋文公的命令,伏剑自杀。
因为《循吏列传》的石奢传和李离传两部分,重点都不在石、李二人的政绩,而是写他们面对两难处境时的选择,所以后代就有学者认为,这两位算不得循吏。像明代的陈仁锡,就说石奢、李离二人“未见为循吏”,也就是没看出来他们二位像是循吏。
那么,在入选人数极为有限的篇幅里,司马迁为什么要把石奢和李离这两位似乎跟“奉职循理”主题有点遥远的官吏选进来呢?
这就要说到《史记》最后的《太史公自序》里,有关《循吏列传》的解题了。在《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是这样写的:“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作《循吏列传》第五十九。”这其中的“奉法循理”,在《循吏列传》的公仪休传里出现过,跟前面引用过的“奉职循理”是同样的意思;“不伐功矜能”,意思是不以自己有功、有能力而骄傲。而其中跟我们读到的《循吏列传》画风最不合的,是“百姓无称,亦无过行”这八个字,它消极地刻画出循吏的一般特征,是他们在百姓口中并不被称颂,但是也没有犯什么过错。不过,如果我们把《循吏列传》的正文,跟《太史公自序》的这一解题结合起来读,其中的意蕴,就颇耐人寻味了。
一面在说循吏可以是“百姓无称”,另一面却把被列入循吏代表的子产,治理郑国二十六年后,死了,引来成年人嚎啕大哭,老人像小孩似的啼哭的悲怆场面,刻画得入木三分,甚至还直接引用了当时人的话:“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意思就是:子产真的离开我们死了吗!老百姓还有谁可以依靠啊?
一面在说循吏应该是“亦无过行”,另一面却特意写了一位有“过行”的司法刑狱高官李离,因为误听传闻错杀人犯,为追求公正,把自己抓了起来,判了死刑,即使有晋文公宽解,依旧不接受君命,而持剑自杀。
《循吏列传》用这种不循常理的写法,尤其是写循吏们对于为官底线的极端重视,底线在他们的眼里甚至高于生命,以此来凸显忠于职守、依循常理的官员难能可贵,应该说是司马迁精心安排的结果,而绝不是选择的不当。
因此就要提到一个历来有不少人已经指出的《循吏列传》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那里面作为循吏代表的,都是春秋时期的官员,司马迁身处的汉朝,是一个官员都没有入选的。与此相应,在《史记》七十列传中,还有一篇《酷吏列传》,那里面写的,却都是汉朝的官员。因此就有人推测,太史公之所以在《循吏列传》和《酷吏列传》里有这样的选择,是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对自己身处的汉武帝时期的官员和官场政治,作鞭辟入里的批判。果真如此吗?我们之后讲《酷吏列传》时再讨论。

《众生》是“陈正宏讲《史记》系列”第三部,按今本《史记》七十列传的序次,分“先秦的隐士、贤达与刺客”“秦汉的功臣、名流与叛徒”“星空下,换几个角度看众生”三卷,对先秦至西汉前期上演种种历史活剧的各色人等进行充满历史智慧的观照与剖析,不仅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史记》“通古今之变”的立意,也体现了作者对于李陵事件前后,司马迁文献整理与历史编纂两阶段工作重心转移的认识与推考。
大家都能读懂的《史记》导读

本书按照《史记》的内容顺序,详细介绍了说帝王故事的《本纪》、穿越时空呈现历史的《表》和记录古代各项制度的《书》,分三部分讲故事、说文化。作者以幽默的文风和三十年从教的经验,用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切入话题:什么叫改朝换代,为什么分分合合总是需要一个王,史上为何大王轮流做,分封与为官的背后又有哪些可说与不可说? 因为《史记》中《表》和《书》文化的深度和难度,即使学者也不容易梳理清晰,而本书作者复旦大学陈正宏教授以研究《史记》三十年的深厚功力,以读者立场深入浅出的呈现能力,“治大国如烹小鲜”,轻松讲解、故事带入后,令读者豁然开朗。
体验先秦、西汉贵族的百样人生
探寻中华民族百转千回的融合之路

书以幽默的文风和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介绍了《史记》的三十篇“世家”,即先秦和西汉时期重要诸侯大姓的家族史。姜太公果真是“偶遇”西伯?“三家分晋”有着怎样的前传?越王勾践破吴归的背后,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史记》里记录的孔子事迹,哪些是在《论语》里看不到的?得了天下的刘邦,如何应对四面八方的威胁?“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诉说着他和韩信怎样的工具人生?靠宫里姐妹上位的兄弟,怎样冲破阴影活出自己?汉武帝的兄弟侄儿,为何出了那么多奇葩?这些古代的贵族为何有着如此奇幻的人生?中华民族又走过了怎样的融合之路?本书将带给你启示。


www.zhbc.com.cn zhbc@zhbc.com.cn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邮编: 10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