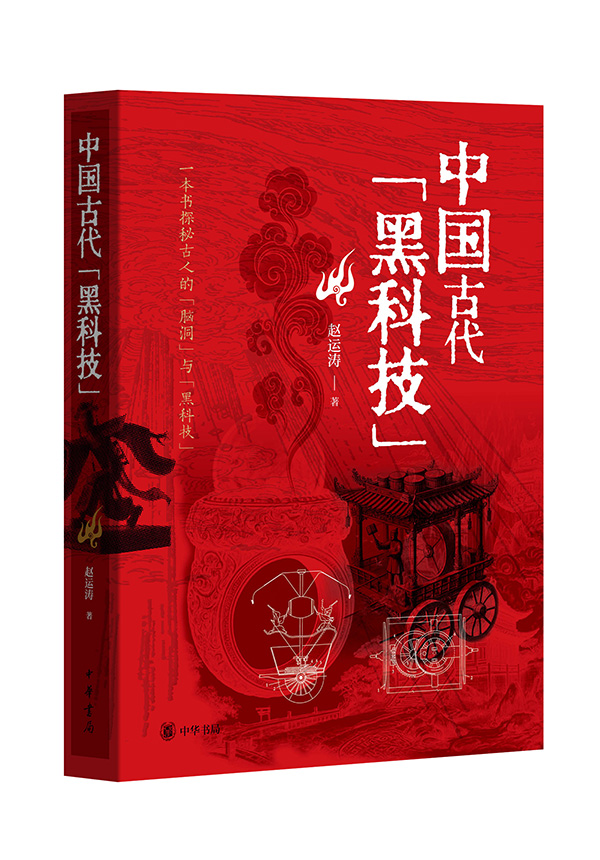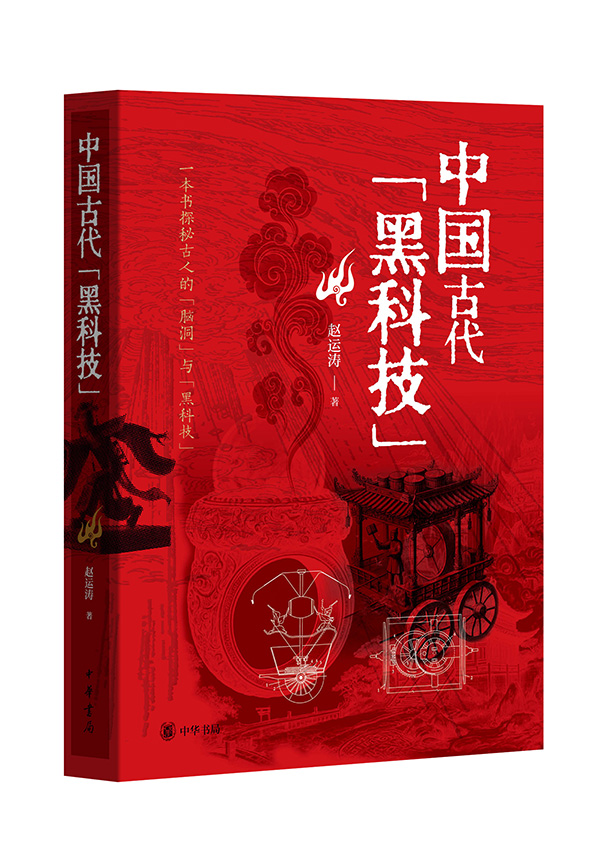
最近电影《聊斋·兰若寺》热映,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古代志怪文学的关注。在传统文化主流叙述中,我们习惯讲经义、礼制与教化,其实还有一条被忽视的传统——那就是古人关于世界的想象。《聊斋志异》正是这种传统的杰出代表。
2025年央视春晚的一大亮点就是机器人表演的赛博秧歌。其实,《聊斋志异》中也有类似的创意。《木雕美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人肩扛竹筐,牵两只大狗,来到一处开始表演。他先从筐中取出约一尺高的木雕美人,将小锦缎鞍垫盖在狗身上,然后把木雕美人放上去。安排妥当后,他呵斥狗快跑。木雕美人便自如地表演各种骑马动作,如脚踩马镫蹲藏在狗肚子一侧,从狗腰向狗尾滑坠,抓住狗尾飞身上狗,或在狗背上跪拜站立,变化灵巧而从未失手。除了杂技,木雕美人还为观众表演了“昭君出塞”的故事。民间艺人先把木雕美人扮成王昭君模样,又从筐中取出一木雕男子,男子帽插野雉尾,身披羊皮袍子,跨在另一只狗身上,跟在木雕美人后面。木雕美人扮演的昭君骑着狗频频回望,男子则扬鞭追赶。整个过程,简直跟真人表演一样。

这种娱乐表演机器人,唐以前就有不少记载。大约作于汉代的《列子》记载说,偃师用革、木、胶、漆等材料为周穆王制造了一个“机器人”,它不仅能够唱歌跳舞,甚至还可以用表情与观看者互动。《晋阳秋》说晋代的区纯制作了一个木房子,又制作一个木妇人在其中,人一敲门,妇人就会开门出来,行完礼又进去,把门带好,这种场景设定,简直像迎宾机器人。
古人关于仿生技术的创意,是技术与想象交织的结晶——它既源于古人对木械机关的精巧掌握,也承载着大量富有未来感的技术幻想。古人不仅在物理构造上大胆尝试(如隋炀帝时的水上自动表演木人),更勇于设想人偶可以模拟人类行为、情感(如《列子》中的偃师机器人、《聊斋志异》中的木雕美人等)。而这不正是当代仿生机器人研发瞄准的方向吗?在偃师木偶的歌舞、抛媚眼与木雕美人的马术、回眸中,我们看到的是人类对生命模拟、智能再造的渴望。
我们现在有各种高科技照相机,《聊斋志异》中也有类似的想象。在《八大王》这个故事中,冯生得到一面镜子:女子只要对镜照一下,影像就可在镜中定格,要是换了装扮,或者换一个人照,那么原来的影像就会消失,新的照片就产生了。
这不是《聊斋志异》的独创,早在明代就有这样的创意。冯梦龙《情史》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北宋大观年间,秀才方乔在街市上偶遇才女紫竹,对其一见钟情,但无缘再见。后来,一个道士给他一面古镜,这个镜子可以留住照镜女子的相貌。方乔把镜子拿到市场的一个摊位找人代卖。终于等到紫竹出来逛街,她看到古镜,就拿起来照了照,惊奇地发现,她的相貌留在了上面。
模仿《聊斋志异》的《益智录》也记载了一面具备性别识别、影像保留、影像更新等功能的镜子。故事中隗俊得到一面神奇的镜子,当女子照镜时,影像会被记录下来,若另一女子再照镜子,前一个影像便会消失。范氏和狐女要帮隗俊找合适的配偶,于是带着镜子到处寻找美貌女子,请她们照镜子,然后将这些影像带回给隗俊查看。隗俊通过镜子最终找到了理想的妻子。
从以上故事可以看出,这种“照相镜”的想象往往与情感有关。在尚无摄影技术的时代,古人通过神化器物等手段,展开了一场关于“视觉记录”“情感投射”与“理想匹配”的幻想实验。
我们现在有智能监控,可以方便家长在外监督孩子学习。《聊斋志异》中的《凤仙》讲了一个古代智能监控的故事:凤仙为了让男友刘赤水专心科举,跟他暂时分开,临行前给他一面镜子。刘赤水发现镜子里存留的是凤仙的背影。他苦读数日后,某天看了一下镜子,发现镜子里的凤仙转过身朝自己笑。随着时间推移,他的学习意志逐渐减弱,开始迷失在游玩中,经常忘记回家。有一次他返回家中,看到镜子中凤仙的影像变得忧伤,仿佛在为他哭泣。又过了一天,再看时,镜中凤仙又变成背影。刘赤水意识到,这种变化可能是自己没有坚持努力学习导致的。于是,他再次投入学习,不再分心。几个月后,镜中的凤仙重新向自己露出了微笑。他终于明白了镜子的魔力:当他不专心学习时,镜中的凤仙便显得忧愁;而当他全力以赴时,镜中的凤仙便会恢复笑容。从此以后,他便坚持学习,并把镜子当作监督自己的老师。两年后,刘赤水考中了举人。得知消息的那一刻,刘赤水看镜子,发现镜子里的凤仙表现得非常高兴。

凤仙镜可以看作古代版的监督学习系统。它不仅能显示人物影像的变化,还能根据使用者的行为状态进行反馈——专心学习时,镜中人微笑鼓励;懈怠荒废时,镜中人背对哀伤。这种“动态感应”的设定,几乎就像一个用情感算法驱动的个性化界面,将情绪和行为绑定在视觉符号中。
古人还有不少关于动图的想象,唐《逸史》记载,有人在墙壁上画了一个女子,然后用酒杯给这个虚拟人物喝酒,结果画中的女子将酒喝得一滴不剩,过一会儿,画中女子的脸变得通红,持续了大约半天;明《西樵野记》记载,明代景泰年间,葛棠晚上喝酒,在亭壁上挂了一张桃花仕女图,这幅古画上的女子能从画上下来唱歌跳舞;明代《三遂平妖传》有一个情节,说女子从画中出来陪员外喝茶。
在尚无屏幕与数字技术的时代,古人已经在神话与小说中预演了“情绪交互”“行为反馈”“虚拟陪伴”等技术概念的雏形。
《聊斋志异·安期岛》讲述了一个古人的冷热两用“饮水机”的故事:刘中堂在安期岛遇到一位神仙,神仙让小僮上茶,小僮来到洞外石壁前,石壁上有一把铁锥,锥尖插入石头中,小僮拔出铁锥,有水出来,小僮用杯子接住,接满后,又把铁锥插回原处。小僮把茶端到刘中堂面前,茶为淡绿色。刘中堂试喝一口,原来是冰绿茶,凉得牙齿打战。神仙示意小僮换一杯,只见小僮仍来到原来的石壁前,拔出铁锥,重新接了一杯回来。刘中堂这次再喝,觉得满口芳香,热气扑面,好像是用烧好的热水沏成的茶。
蒲松龄还描写了两只“智能古瓶”。《聊斋志异·古瓶》说有两人淘井时获得两个古瓷瓶,后被人买走。其中一瓶可预测天气阴晴:如果要下雨了,瓶子上就会出现一个如小米一样大的湿润处,随着湿润处越来越大,雨也就来了,等没有湿润处了,雨也就停了。另一个瓶子上边有个黑点,可以对应月亮的圆缺变化:在朔日(月亮看不见的时候),瓶子上有个像豆子一样大的黑点,随着月亮变圆的过程,这个黑点也越来越大,随着月亮变缺,黑点也就越来越小。这个瓶子还有“附加功能”——在瓶中插花,花跟长在原来的枝条上一样,可以落花结果。

从冷热双出的“石壁饮水机”到会预测天气与显示月相的“智能古瓶”,这些《聊斋志异》中的奇妙设定,展示了古人对于日常生活器物“功能升级”的丰富想象。在没有传感器、触控屏和智能芯片的年代,古人用神话与故事为生活器具赋予灵性,构建起一套以“自然互动”为核心的幻想技术系统。
除了以上故事,我在《中国古代“黑科技”》一书中还搜集了许多古人被低估的真实发明,比如唐代精巧的自动出酒器,明代能逆风而行的先进帆船等,也搜集了其他典籍中记载的一些超前技术构想,如《拾遗记》中描绘的秦始皇时期的“潜艇”,以及《琅嬛记》所构想的类似电脑的“七宝灵檀几”等。从实用机关到神话机器,从历史发明到未来预演,这本书以“技术史”与“幻想学”的双重视角,重新发现古代中国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聊斋志异》等古代典籍告诉我们,古人从来不是只有眼前的现实世界,他们用故事构建虚拟现实,用创意铺设“科技”之路。古人并不完全是实用主义的,他们也有梦想,也有对美好未来的想象。这种源远流长的幻想传统,正是我们今天不该遗忘的文化根脉。我们的文化基因中从来就不缺少创意,古人有着各种脑洞大开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创造不无裨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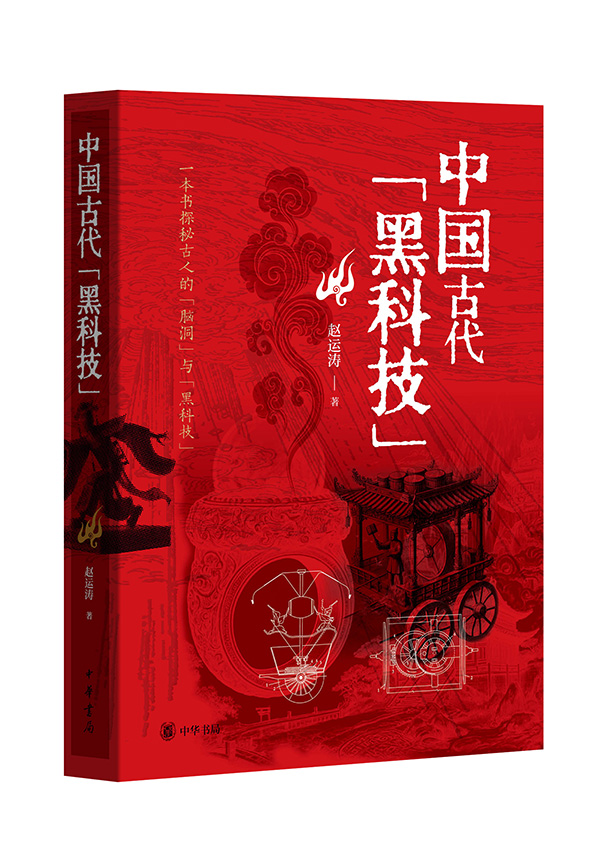


www.zhbc.com.cn zhbc@zhbc.com.cn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邮编: 10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