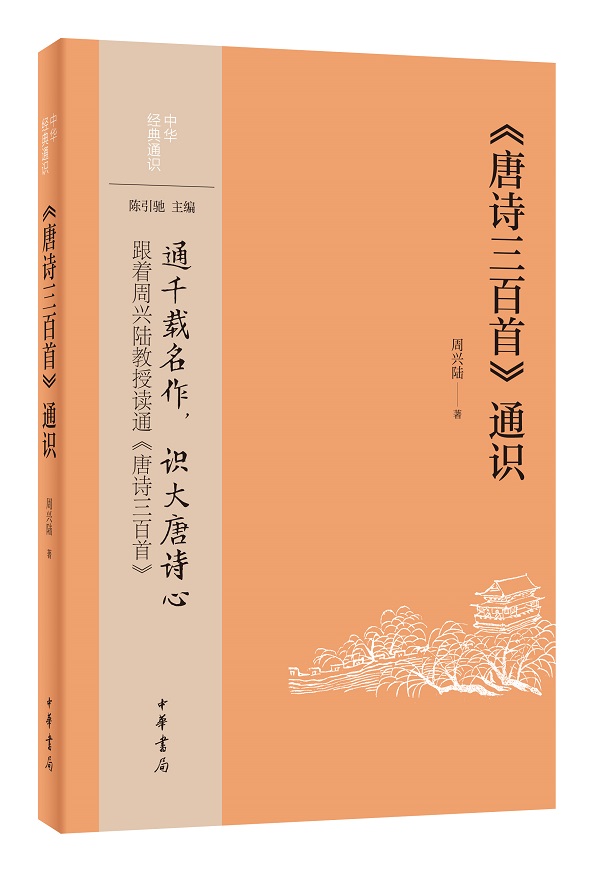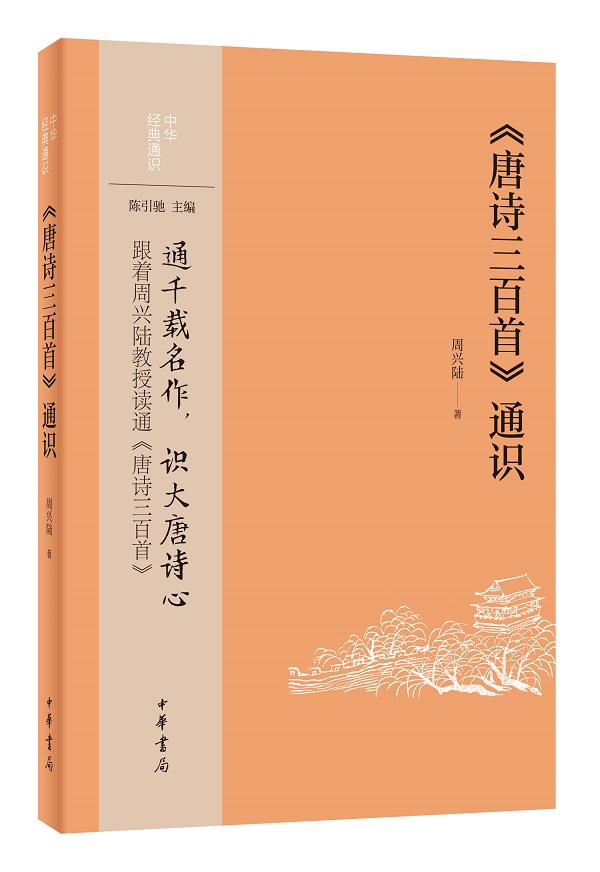
中国人的生命节奏与宇宙自然的运行节序谐和共振,诗人心灵敏锐,具有强烈的物候节序感。初春的一瓣新芽,秋夜的一声蛩鸣,都能引起诗人怦然心动,一年四季有情感的意义。陆机《文赋》说:“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秋日金风狂起,落叶飘零,让人悲伤;春天群芳争艳,枝叶扶疏,令人欣喜。春与秋是诗人最为敏感的季节。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曰:
首二句写出普遍的心态:在外宦游的人,对物候的变化更为敏感,气象转新,反而让他们感到惊心。中间四句具体写“物候新”:海边云霞透出曙光,梅柳的春色已由江南渡至江北。和煦的春风传来黄鸟的鸣叫,春光在绿蘋上跳荡。真是一派大地回春的美好景象。这四句写景很有绘画性和动态感。但是,对于宦游者,往往是乐景而生哀情。陆丞的《早春游望》引得诗人乡思之泪簌簌地流下来。“古调”指陆丞的诗,照应题目“和”字。这首诗虽是和作,却自抒怀抱,毫无生硬牵强之处。
刘方平一生没有做官,诗歌没有深刻的内容、重大的主题,但隐藏着一颗对自然节序敏锐的心灵。你看《月夜》:
夜已深了,月光斜照着庭院,只能看到半边;天空中星斗纵横,夜色将尽。久违的虫鸣透过窗纱,打破夜的澄净,传来了春气回暖的讯息。这首《月夜》就像诗中的“虫声”一样,是天地的元声。
古人的伤春悲秋,往往与爱情、个人仕途和家国情怀联系在一起,是多重情感的复调。李白的《春思》:
这是以闺妇口吻抒写春夜里对远行在外的丈夫的思念。燕在北方,是丈夫行役之地,北地碧草如丝;秦是今天陕西一带,闺妇所在,令人想到秦罗敷,闺妇所在的秦地桑叶繁茂,春意已浓。丈夫在燕地睹春草而怀归之日,正是闺妇相思断肠之时。夫妻二人彼此同心,甚至妻子的思念更痛苦难熬。末二句谓夜深了,闺妇孤独无眠,而春风偏偏吹进来,轻抚罗帏,搅扰得闺妇相思难耐。春情和闺思合在一处写,真切动人。秋月秋风同样也能惹起闺阁之思。李白《子夜吴歌》:
这是李白采用吴声歌曲写的一首乐府诗,写闺妇思念远征在外的丈夫。唐代前期实行府兵制,士兵出门打仗需要自带军需用品,家中闺妇到秋天的时候会制衣服送给丈夫。古代的葛布需要放在石砧上捶打去浆变软,才可裁制衣服。长安城月光之下,传来家家户户捣制衣服的杵声。“玉关”,玉门关,泛指丈夫所在的边关。闺妇对在外征戍的丈夫的思念都寄托在这捣衣声中,夜深了也绵延不绝,好像秋风都吹不散。末二句代闺妇发问:什么时候才能平定边疆敌人的侵扰,男人们可以不再离家远征啊!可见战争对平民百姓安定生活的破坏。秋思、闺情与对和平的渴望融为一体,升华了主题。
杜甫七律《阁夜》写夔州的冬景,跟家国情怀紧密联系起来:
大历元年(766)冬天杜甫在夔州西阁。首联点明时令和天气,冬天的太阳早早就落山了, 偏远的夔州的寒夜,霜雪初霁。颔联写阁夜之景,鼓角之声此起彼伏,星光映照在三峡中,光影动摇,境界壮大,实则有动荡不安之意,令人想到当时蜀中崔旰、郭英乂、杨子琳等军阀连年混战,局势混乱不堪。
于是生出颈联,因为战伐频仍,多有死伤,听到了几家的野哭。因为战死,不得收尸安葬,故曰“野哭”。“夷歌”句写僻远的夔州的百姓生活,在如此天寒地冻的夜晚,百姓打鱼砍柴,可以想见生活之穷苦。“卧龙”指诸葛亮,是杜甫一生仰慕的贤相能臣;“跃马”指公孙述,西汉末年曾据蜀为乱,是乱臣贼子。末二句谓不论忠奸贤愚终究归于消亡,那么诗人如此遭遇,远地音讯寂寥无闻,也就都随它了吧。一方面是对蜀地军阀混战的斥责,另一方面也是无奈的自我宽慰。

中国文人有渔樵情结,因其是隐逸的象征,但“樵夫晚担月为灯”,以渔樵为生的俗世人,面对的却是艰难繁重的生活。
除了春夏秋冬的季节外,若遇上一年里的重要节令,古人也往往有诗咏怀。旧历新年是国人情感分量最重的节日,当万家团圆之时,如果还漂泊在外,那是不能不作诗诉苦的。崔涂《除夜有怀》:
联系前面的《孤雁》,就可以理解这首诗里诗人远离家乡,孤独地漂泊在异乡的情景了。颈联所写之孤独无奈心情,非亲历其境者不易体会。这种异乡漂泊的感情因为除夕夜而尤其迫切沉痛,难以忍受。
寒食节是清明节前一二日,禁烟火,只吃冷食,故名。唐代朝廷于寒食节特赐近臣火烛,是特权阶层的“特供”。韩翃作《寒食》记此事:
“御柳”点明是宫廷的杨柳,“汉宫”是以汉代唐的手法,唐诗里常见。“五侯”指宦官,自肃宗、代宗以来,宦官炙手可热,白居易《轻肥》等诗就是针对当时的宦官而作的。此诗讽刺之意隐然言外,就连德宗看了也察觉不出什么讽刺意味,把起草制诰一职特批给“春城无处不飞花”的韩翃。言之者无罪,但没有达到“闻之者足戒”的效果。
在唐人众多的清明寒食诗里,《唐诗三百首》挑选出无名氏的一首《杂诗》:
首二句写寒食节的景色,按自然语序应该是“雨近寒食草萋萋,风著麦苗柳映堤”,为了符合平仄才调整了语序。唐朝时,官员清明节是放假的,可以归乡扫墓。但是这位诗人羁旅在外,有家归不得,因此,杜鹃别在耳边啼鸣。“杜鹃”,一名子规,其声似“不如归去”。全诗主旨不外是怀乡之情,但构想别致。
“九”在《周易》中是最大的阳数,九九归真,一元肇始,“九九”又谐音久久。古人把农历九月九日定为重阳节,享宴高会,登高秋游,佩插茱萸,把盏赏菊,祈愿生活的吉祥美好。重阳节往往能引起诗人更为强烈的思亲怀人之情,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抒写了漂泊游子的共同情怀:
王维是河东蒲州(今山西运城)人,属当地名门望族,兄弟有王缙、王繟、王纮、王紞,还有两个妹妹。王维十五岁就去长安参加科举考试。这首诗是他年轻时在长安所作。以华山为界,自己住在长安,是山之西;华山以东是他的家乡,故称山东。(今天的山东、山西省是以太行山为界。)王维诗中一个“独”字、两个“异”字写出了羁旅长安的孤独感、陌生感。“每逢佳节倍思亲”,是人之常情。诗歌是人人心头万不获已、必欲说出的话,代天下人抒写普遍的情怀,也就能引起广泛的情感共鸣。“遥知”领起后面二句,思绪飞回到家乡,想象兄弟们九日登高,佩插茱萸时少我一人,他们一定很思念我吧。明明是诗人思念家乡的亲人,却转而写家乡的亲人思念他。这就像杜甫《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一样,对面着笔,更委婉曲折,摇曳生姿。
(本文节选自周兴陆著《〈唐诗三百首〉通识》,2023年7月中华书局出版,标题为编者所拟)


诗歌是最美的语言,唐诗是最美的诗歌,是现代人灯火永不阑珊的精神家园。《唐诗三百首》作为风行二百多年的最经典的童蒙诗学教材,具有蒙以养正、诗以化人的重大作用。但是,当代人或只会背诵零星诗作,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未能对其有一通贯而清晰的整体认知。
本书从通识教育的立场出发,内容不仅涉及《唐诗三百首》的编选旨趣、艺术世界、经典化历程、遗珠之憾,还涵盖唐代精神风貌、唐诗的体裁与近体诗的格律、唐诗的域外传播等主题,拈出50位诗人的130余首诗作进行鉴赏,时代背景、诗人际遇、诗歌意境、名家点评融为一体,是以诗证史的唐代实录,是中国诗学传统的小像,是旧体诗创作的初级指导,是增强诗学修养、培养审美人格的简明易懂的大众读物。


www.zhbc.com.cn zhbc@zhbc.com.cn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邮编: 10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