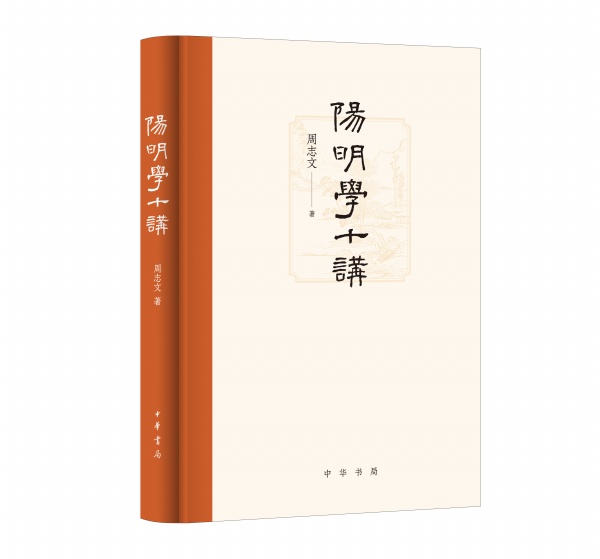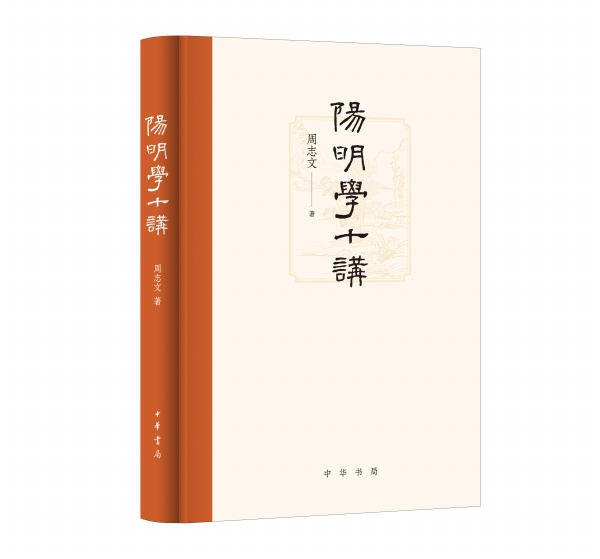
很多人都知道,阳明学的核心,是在讨论“良知”的问题。所谓“良知”,其实是指天生本然,不待学而有的智慧与能力,语出《孟子·尽心上》。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以为人类善的道德,都是从良知、良能发展出来,他举例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意即当人生下来,就知道爱他的父母,这叫作“亲亲”,亲亲是仁的基本;小孩长大,知道亲亲之后还会友爱兄弟,这友爱兄弟的行为叫作“义”;不断推广,终成为泛爱众而道德很好的贤人,由这个最基本的良知、良能发展出来的终极结果,便是孟子所谓的“达之天下也”。
“良知”,也可称为“良心”,是上天给我们的基本的辨识世上一切的力量,让最没有经验的孩童也具有喜善恶恶的能力。这理论最早由孟子提出,是用来证明他的“性善说”的,但后来哲学的讨论只停留在性善、性恶之上,良知之说就没有太多人提起,久之也被忘却了,直到阳明再度提出这个名词,成为阳明学说最主要的部分。
因为孟子在举例中言及“孩提之童”,阳明之后不久,李贽(号卓吾,1527—1602)以“童心”来取代这个名词,他在《童心说》中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又说:“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李贽解释,童心是人最早的初心,是“绝假纯真”的,这与孟子及阳明说的“良知”并无不同。孟子为良知、良能下了个定义,是“不学”
“不虑”而天生具有的,不学就是不经学习,不虑就是不经思考。阳明在《传习录》中说:
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母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良知”,“不假外求”,是一种不假思考的直觉式的反应,一经学习或用学术方式思考,就陷入一种学问的窠臼之中,表面看起来理论严整,但对良知而言,反而造成了伤害。所以良知不是知识,也不是学问,学习与思考之下所得的良知,绝对不是真的,也不是全的。
以艺术欣赏为例。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也译作克罗采,Benedetto Croce, 1866—1952)主张艺术欣赏要肯定“直觉”,不惜排除知识,这点跟阳明的良知“不假外求”很像。小孩看到美丽的事物自然会惊叹,有时会忘情地手舞足蹈,这种表现就是直觉。而这种直觉,是不必通过知识训练得来的,它是欣赏一切艺术的基础。孟子与阳明所提的良知,非常接近艺术欣赏论上所倡导的“直觉说”。
阳明被贬谪到贵州龙场驿,路上遇到了许多惊险的事,他有《杂诗》三首,其中有诗句曰“危栈断我前,猛虎尾我后。倒崖落我左,绝壑临我右”,所写可能是真实的状况。到龙场后,生活困顿险巇,更不在话下,在有形的生活与无形的心理压力下,处处窒碍,几乎不能度过,他在不断挣扎与反省之下,发现了长久以来不得其解的格物致知的真相,这层层的困顿在他心中盘据得太久了,想不到在这里终于得到解脱。据《明儒学案》:“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表面上说“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其实所谓“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指的便是良知,良知早已存在我心中,无须到外头去追求,所以最早的“良知说”只单说“良知”,不说“致良知”,“致良知”三字,是阳明平宸濠乱时在江西才提出的。
阳明为什么标举这个良知的说法呢?用这说法解释圣人或圣学,是与程、朱的方法不同的。大致说来,程、朱的求圣之法是通过学习逐步实现的,这跟阳明标举“心的发现”是不同的,阳明认为圣人早在我心,求圣之法当向自己心内求,两者在方法上言,当然差异是很大的。
阳明早年也跟一般读书人一样,是从朱熹的注本开始学习儒家经典的。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是当时所有人读书的根本,也是朝廷考试题目的来源,更是答题的唯一标准,阳明科举出身,哪会不读朱熹的书呢?朱熹除了《四书》之外,还有《诗集传》
《周易本义》等重要的著作。严格说来,朱熹是个人人钦服的经学大家,也是个伟大的理学家(照顾炎武的说法是:“古之理学经学也。”),毕生著作不辍。他的学问,累积了北宋以来很多著名大儒的整体成就,可说是集南宋之前儒学之大成者。
阳明少年时的性格有点“不羁”,崇尚自由,不喜格套。他虽出身儒学家庭,早年并不特别在儒家学问上用功,喜欢兵法,喜欢道教,对佛教也很好奇。他对儒家之学第一次觉得“有感”,是十八岁时从江西南昌携新妇回浙时,舟至广信,拜访了当时的大儒娄谅。娄谅是明代大儒吴与弼(号康斋,1391—1469)的弟子。吴与弼的学问继承北宋诸儒及朱熹,算是朱子学一脉的正宗,代表吴与弼的《崇仁学案》在《明儒学案》中排序第一,可见黄宗羲也认可吴在明代学术上的重要性。其实吴与弼的重要并不在于他在思想方面有什么太大的开创,比起朱熹,他的格局要小一些,但是他有娄谅、陈献章这样的弟子,是他们集合起来,开创了明代学术的一部分格局,二者之间,陈献章尤其重要。
当时娄谅跟阳明谈的是宋儒之学,说:“圣人必可学而至。”强调的是学,并不是悟。“学”是朱子之学最重视的,也算是儒门的真传,因为《论语》首章就是“学而时习之”,孔子也说过自己“好学”,又说过:“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学”是儒学的发端,是没人可否定的,但“学”是不是儒学的究竟呢?可讨论的地方就多了。阳明受娄谅的启发,开始对儒家性命之学发生兴趣,
也开始认真读宋儒讨论此类话题的书了。孝宗弘治五年(1492),阳明二十一岁,考上了浙江乡试,第二年进京参加会试不第,在这期间,他认真学习宋儒的格物之学,《年谱》说他“遍求考亭遗书读之”,考亭就是朱熹。《年谱》接着又说:“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这是有名的阳明“格竹子”的故事。
(本文选自周志文著《阳明学十讲》,中华书局2022年7月出版)
阅读王阳明的非凡人生经历,体悟阳明学的知行合一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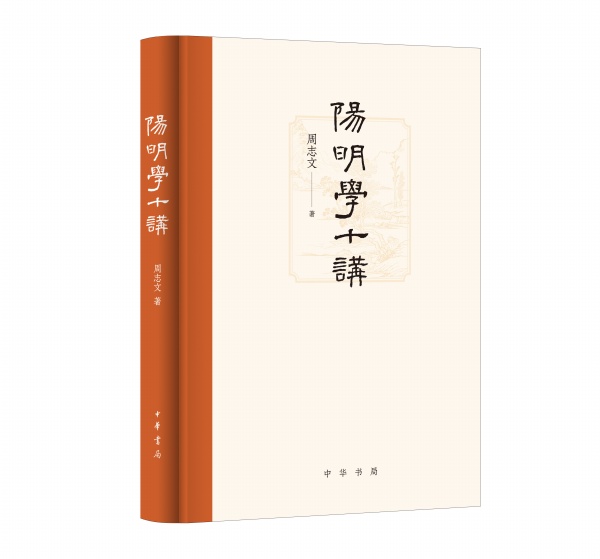
1. 学者、作家周志文研究阳明人生与学术的力作。作者有感于市面上有关阳明及阳明学的著作要么学术气息太浓重,要么偏重阳明的事功,将之近乎神话了,而较少谈其在思想上的启发与贡献,遂秉承“有一分证据才能说一分话”的写作态度,“就想写点儿别人没写的东西”,将一个好奇、倔强、勇敢、睿智的阳明渐次展现在读者面前,他的思想在当时及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亦被一一揭示。
2. 这是一部能够激活思想、引发深思,带领读者全面了解王阳明的大众读物。作者的散文功底极好,自然朴实又极富真情。这一风格在本书中亦能得到明证。整部书语言浅近,平白如话,像是一位和蔼的长者在对你娓娓而谈,谈阳明的非凡人生,谈阳明的学术,谈阳明的军功建设,谈阳明的后学分派,等等。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阳明,毫无压力地读懂阳明及阳明学。
3. 多面复合型人才——王阳明;能引领大众接地气——阳明学。阳明自小不受绳墨约束,喜欢兵法韬略,有经略四方之志,日后平南、赣乱事,平宸濠之变,平思、田变乱,一介文臣,竟然三次救国家于危难。中进士,做官,虽不显倒也平淡,但因辩戴铣案而被廷杖,随后被贬贵州龙场,于是就有了格竹子、龙场悟道。阳明学的核心是“致良知”“知行合一”,因为其化烦琐为简约,倡导与人讲学“须做得个愚夫愚妇”,和光同尘地用他们的思考方式、语言习惯讲解,才能真正引领他们;又强调为学求诸内心,无须他借,当下实行,直截便利。这使得阳明学在民间掀起了极大的波澜,产生的影响远盛于官方学术。
4. 学者杨渡撰写序言,力荐本书。他说:“这一本《阳明学十讲》,便是他(周志文)研究王阳明毕生功力的结晶。学养深厚自不待言,智慧的观察与分析,亦时时浮现。读者会从他的叙述中,感受到王阳明那既倔强又勤思好学、既智慧又幽默、既平实又充满理想主义的人格魅力。”
“阳明整个人在中国传统社会是个‘异类’”,自小不受绳墨约束,不喜“儒家四平八稳的那套”,喜兵法韬略,有经略四方之志,后又对道教、佛教感兴趣。然真正“折节”做起正统儒家学问来,冲突、波折不断,困顿、挫折接连,好奇和怀疑促使他不断思考,最终构筑起以“致良知”“知行合一”为核心的阳明学。
《阳明学十讲》是著名学者周志文先生基于讲稿整理而成的新作。作者有着深厚的学养,秉持“有一分证据才能说一分话”的态度,通过对阳明学之前儒学历史的溯源、阳明学出现的背景分析、阳明人生与学术的精到论述、王门后学的发展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使读者能够在平易而有力的话语中,深切感受到王阳明“不世出之天姿”,“冠绝当代,卓立千古”的道德、功业与文章。
周志文,祖籍浙江天台,1942年生于湖南辰溪。台湾大学文学博士,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现已退休。主要从事明清学术史、明清文学、现代文学研究,博涉广猎,著述颇丰,其中学术著作有《晚明学术与知识分子论丛》《汲泉室论学集》《论语讲析》等,另有散文随笔集《同学少年》《时光倒影》《家族合照》等。
阅读经典,面向未来 杨渡
自序
第一讲
一、为何讲阳明学
二、从孔子讲起
三、经的流变
四、儒学史上的问题
第二讲
一、唐、宋的儒学
二、《四书》与朱熹的贡献
三、 朱学的困境与阳明的出现
四、“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
第三讲
一、南、赣乱事
二、宸濠之变
三、丁忧下的王阳明
四、思、田的变乱与初到广西
第四讲
一、广西乱平
二、死亡之旅
三、军功与建设
四、死后的争议
第五讲
一、阳明对朱熹格物说的体验
二、“格竹子”的故事
三、致知与致良知
四、知行合一
第六讲
一、心即理
二、“满街人都是圣人”
三、关于《大学》的争议
四、《朱子晚年定论》
第七讲
一、“然吾之心与晦庵之心未尝异也”
二、“四有”“四无”
三、王学分派
四、浙中王门
第八讲
一、江右王门与“戒慎恐惧”
二、“正学”“归寂”与“静中恍见端倪”
三、泰州学派的“万物一体”
四、“何独于人而异之”
第九讲
一、“道理不行,闻见不立”
二、阳明的高迈处
三、阳明死后的争议与平反
四、清以后阳明学的发展
第十讲
一、韩、日阳明学的消长
二、日本阳明学的发展与现况
三、重新检视阳明学
四、结论
后记

www.zhbc.com.cn zhbc@zhbc.com.cn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邮编: 10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