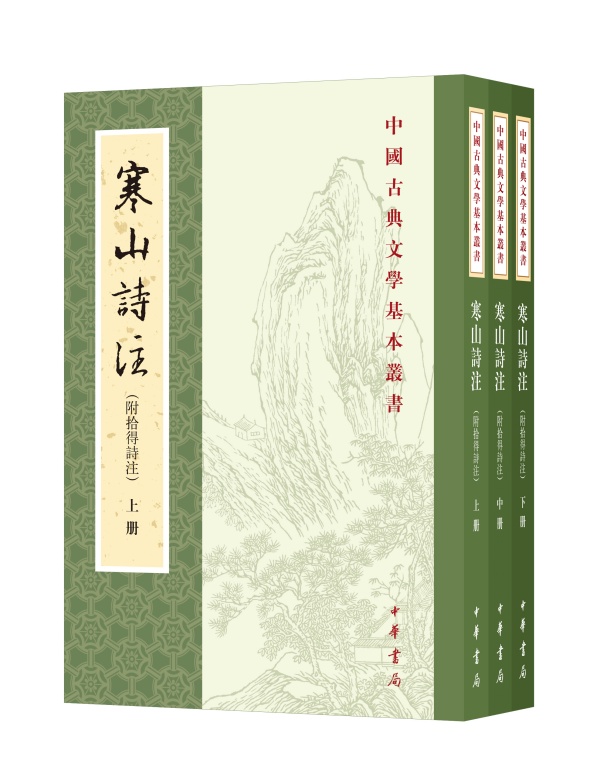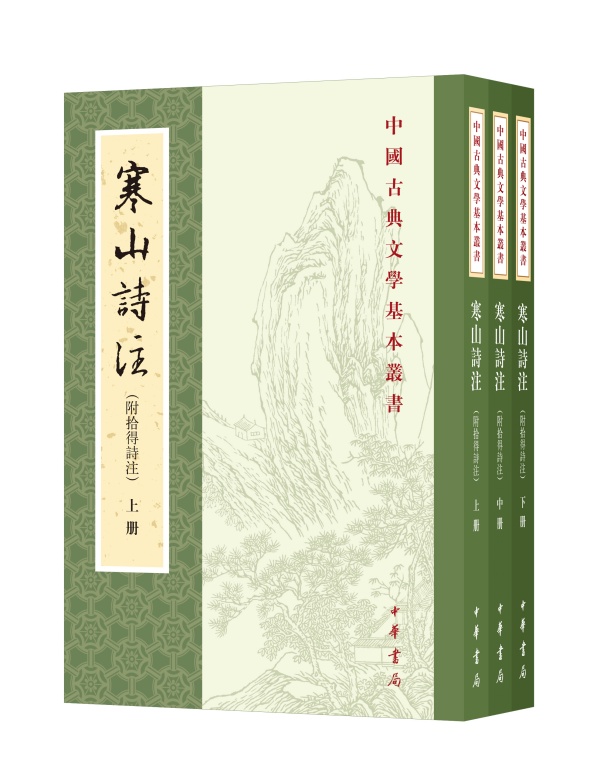
——世间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治乎?
——只要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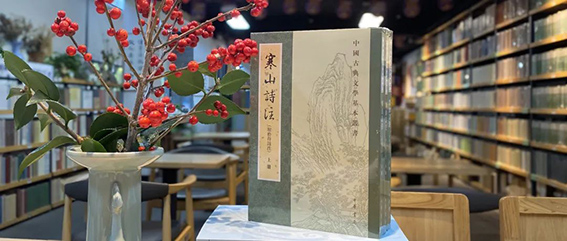
这组著名的对话,蕴含大智慧、大道理,诸君可知上述妙语问答出自何人?
他们便是唐代著名的诗僧,相传文殊、普贤化身的寒山与拾得。
寒山,生卒年不详,姓名亦不传,因为他长期隐居于天台山的翠屏山(又称寒岩、寒山),因而自称为寒山或寒山子。关于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生平等,历来众说纷纭。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寒山是初唐人。在宋本《寒山子诗集》前面有一篇署名“朝议大夫使持节台州诸军事守刺史上柱国赐绯鱼袋闾丘胤撰”的序。由于闾丘胤序在很长时期内产生较大影响,故历来谈论寒山身世的人,许多都以闾丘序为根据。近人余嘉锡以翔实的材料,考证闾丘胤序为伪作,以后一些学者进一步论证了余说的确凿可信。不过闾丘胤序虽是伪托,其中应该也有一些真实的成分,或许是来自关于寒山的传说,如云:
详夫寒山子者,不知何许人也,自古老见之,皆谓贫人风狂之士。隐居天台唐兴县西七十里,号为寒岩。每于兹地,时还国清寺。寺有拾得,知食堂,寻常收贮余残菜滓于竹筒内,寒山若来,即负而去。或长廊徐行,叫唤快活,独言独笑,时僧遂捉骂打趁,乃驻立抚掌,呵呵大笑,良久而去。且状如贫子,形貌枯悴,一言一气,理合其意,沉而思之,隐况道情,凡所启言,洞该玄默。乃桦皮为冠,布裘破弊,木屐履地。是故至人遯迹,同类化物。或长廊唱咏,唯言咄哉咄哉,三界轮回。或于村墅与牧牛子而歌笑,或逆或顺,自乐其性,非哲者安可识之矣。
这样一个疯疯癫癫、贫穷狂放的寒山形象,便被后人所接受而固定了下来。证以寒山诗:
时人见寒山,各谓是风颠。貌不起人目,身唯布裘缠。我语他不会,他语我不言。为报往来者,可来向寒山。
可知二者描绘的寒山的精神风貌是一致的。
另一种说法认为寒山是中唐时人。《太平广记》卷五五《寒山子》条引《仙传拾遗》云:
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历中隐居天台翠屏山。其山深邃,当暑有雪,亦名寒岩,因自号寒山子。好为诗,每得一篇一句,辄题于树间石上,有好事者随而録之,凡三百余首。多述山林幽隐之兴,或讥讽时态,能警励流俗。桐栢征君徐灵府序而集之,分为三卷,行于人间。
今人研究寒山者,多据《仙传拾遗》推定寒山生活的时代,但具体年代又有一些不同。
寒山的身份,闾丘胤序称他为“贫人”,《祖堂集》称他为“逸士”,《仙传拾遗》也说他“隐居天台翠屏山”,可见他是一位隐士。不过他的诗多说佛理,又曾写过“自从出家后,渐得养生趣”的诗句,所以后人多称他为“诗僧”。至于他的生平,亦不可详考,只是从他的诗作中透露出一些消息。他有许多诗作描写隐居寒岩的生活和感受,堪称实录。可是他的家世和隐居前的经历,却始终是个谜。他有诗云:
出生三十年,尝游千万里。行江青草合,入塞红尘起。炼药空求仙,读书兼咏史。今日归寒山,枕流兼洗耳。
可见他三十岁隐居寒岩以前的抱负。又有诗云:
少小带经锄,本将兄共居。缘遭他辈责,剩被自妻疏。抛绝红尘境,常游好阅书。谁能借斗水,活取辙中鱼。
可以窥见他隐居前的家庭生活。
一向寒山坐,淹留三十年。昨来访亲友,太半入黄泉。渐减如残烛,长流似逝川。今朝对孤影,不觉泪双悬。
则是他晚年隐居寒岩时心情的写照。一位研究者对他的生平作了这样的推断:“寒山本来是生活在农村中的文人,因为他有诗人气质,而又有骨气。开始是隐者或隐士,隐姓埋名,不应科举,自称贫子。在漫游中扩大了视野,认识了现实中更多的矛盾与民间疾苦,由隐士而避世入山。到了天台山,便在寒岩也叫翠屏山的山间住了下来,于是由贫子而成了寒山子。由避世而弃家。这时他结交了国清寺的拾得,他们成了莫逆之友。他便抛弃了驳杂的儒、道之流隐逸思想,皈依佛门,由弃家而出家,名字也由寒山子而成为寒山了。”不过从寒山诗《个是何措大》和《书判全非弱》两首看来,或许他也曾应试而落第。有的研究者根据寒山的诗作勾勒出他早年经历的较详尽的轮廓,但是在使用这些材料的时候,应该采取慎重的态度,因为这些诗作所描写的内容,是否全都是诗人本身的亲身经历,还是有待证明的。因此寒山早年的生活,仍有许多空白有待研究。
寒山在天台隐居时过从甚密的拾得,本是国清寺丰干禅师在路边拾得的弃儿,以后便留在寺院为僧,他和寒山有着一致的生活态度。后世人或称他们三人为天台国清寺的“三隐”,把他们的诗作编在一起,称为《三隐集》。

寒山诗云:“五言五百篇,七字七十九,三字二十一,都来六百首。”四部丛刊景宋本《寒山子诗集》收有寒山诗三百一十一首,附拾得诗五十四首。由于寒山诗是由好事者从“树间石上”抄录而来,在寒山诗和拾得诗之间也有重复现象,因此现存寒山诗或许不是寒山诗的全部,其中也可能有一些并非出自寒山本人之手。也有的研究者认为存在一个寒山诗的作者群。
寒山诗的思想驳杂不纯,有人说“似儒非儒,非儒亦儒;似道非道,非道亦道;似僧非僧,非僧亦僧;似俗非俗,非俗亦俗”。从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即世俗诗与宗教诗,不过二者并不是絶对地泾渭分明的。
寒山的世俗诗以他前期的作品居多,其中有一些抒情咏怀诗,表现的情怀与唐代一般士人的情怀并无二致。从《国以人为本》、《去家一万里》中,可以看出寒山的政治主张。前者云:
国以人为本,犹如树因地。地厚树扶踈,地薄树憔悴。不得露其根,枝枯子先坠。决陂以取鱼,是取一期利。
作者的民本思想,说明他从小接受的是儒家思想的教育。他也曾有过施展抱负的想法,然而现实中屡屡碰壁,因而怀才不遇的悲慨便屡屡从他的诗中发出,如《闻道愁难遣》、《书判全非弱》、《个是何措大》、《吁嗟贫复病》等都是。
一人好头肚,六艺尽皆通。南见驱归北,西逢趂向东。长漂如泛萍,不息似飞蓬。问是何等色,姓贫名曰穷。
我们不知道这首诗是否是寒山的自画像,但其中包含了寒山本人在生活中的感受,则是可以想象的。
寒山是感情笃厚的人,他也曾有过自己的家庭、亲人、朋友,他对他们怀有深厚的情意,如《弟兄同五郡》对乡国的追忆,《去年春鸟鸣》对兄弟的思念。下面一首尤为感人:
昨夜梦还家,见妇机中织。驻梭如有思,擎梭似无力。呼之回面视,况复不相识。应是别多年,鬓毛非旧色。
这首诗是寒山入山多年以后所作。他的家还存在吗?他的妻子还健在吗?我们无从知道。漫长的岁月已经改变了人们的面貌,纵然诗人与妻子重逢,也难以相识了。可是有一样是岁月无法改变的,那就是诗人对妻子的刻骨思念。某一个夜晚的这个梦境,把这位弃絶人世、隐居寒岩的白发老人内心的隐秘情感揭示了一角:他其实并未忘情于遥远的亲情之爱。
寒山诗中还描写了一些生意盎然的生活场景,特别是描写了许多年轻的女子,如像《相唤采芙蓉》、《春女衒容仪》、《三月蚕犹小》、《昨日何悠悠》等。
相唤采芙蓉,可怜清江里。游戏不觉暮,屡见狂风起。浪捧鸳鸯儿,波摇鸂鶒子。此时居舟楫,浩荡情无已。
这些诗里洋溢着的是对生活的热爱。可是另一些描写年轻女子的诗篇,如像《玉堂挂珠帘》、《城中娥眉女》、《璨璨卢家女》,青春的欢乐只是短暂的,死神最终将为一切美好的事物打上句号。下面一首诗曾被朱熹称赞为“煞有好处,诗人未易到此”:
城中娥眉女,珠佩何珊珊。鹦鹉花前弄,琵琶月下弹。长歌三日响,短舞万人看。未必长如此,芙蓉不耐寒。
这种人生无常的喟叹声在寒山的世俗诗中反复地回荡着,是他思索人生的结果,也是他终于通向佛道的途径。
寒山的世俗诗中有大量的讽世劝俗诗。他冷眼旁观那个你争我夺的社会,比喻为饿狗争食:
我见百十狗,个个毛鬇鬡。卧者渠自卧,行者渠自行。投之一块骨,相与啀喍争。良由为骨少,狗多分不平。
他抒发了对那个贫富不均的社会的愤懑不平,和对贫穷无路者的同情:
富儿会高堂,华灯何炜煌。此时无烛者,心愿处其傍。不意遭排遣,还归暗处藏。益人明讵损,顿讶惜余光。
他也揭露了富人的贪婪,并给予咀咒:
富儿多鞅掌,触事难祇承。仓米已赫赤,不贷人斗升。转怀钩距意,买绢先拣绫。若至临终日,吊客有苍蝇。
寒山对风俗浇薄和世态炎凉的批判,包含了他亲身经历的感受在内。他看到了金钱如何扭曲了人们的亲疏关系:“富贵踈亲聚,只为多钱米。贫贱骨肉离,非关少兄弟。”他有诗云:
城北仲家翁,渠家多酒肉。仲翁妇死时,吊客满堂屋。仲翁自身亡,能无一人哭。吃他杯脔者,何太冷心腹。
这样的故事在过去的生活中,一再地重复着,在文学作品中,也一再地被吟咏着,然而并没有失去新鲜的意义。他痛恨生活中嫌贫爱富、以貌取人的现象:“昨日会客场,恶衣排在后。只为着破裙,吃他残粑籉。”因为他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历:
我在村中住,众推无比方。昨日到城下,却被狗形相。或嫌袴太窄,或说衫少长。挛却鹞子眼,雀儿舞堂堂。
寒山对生活并不只是冷眼旁观,他以一个下层民众的导师的姿态,苦口婆心地告诉人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希望穷苦的民众能够过上较好的生活。他告诫人们改变“妇女慵经织,男夫懒耨田”的好逸恶劳态度。他主张对子女加强教育:“养子不经师,不及都亭鼠。” “养女畏太多,已生须训诱。”他提倡读书识字:
读书岂免死,读书岂免贫。何以好识字,识字胜他人。丈夫不识字,无处可安身。黄连揾蒜酱,忘计是苦辛。
他还向民众传授致富之道:
丈夫莫守困,无钱须经纪。养得一牸牛,生得五犊子。犊子又生儿,积数无穷已。寄语陶朱公,富与君相似。
寒山对民众的劝导,不乏迂腐的成分。在另一些场合,他力图用佛教的教条去感化民众。不过寒山作为一个沦落民间的下层知识分子,和民众生活有了血肉的联系,他扮演的民众导师的角色,使他的诗作在内容和形式上迥别于其他文人。
寒山的大半生是在隐居中度过的,最初是和家人在乡村中隐居,后来孤身一人结茅寒岩。他留下了许多隐逸诗篇,如像:
琴书须自随,禄位用何为。投辇从贤妇,巾车有孝儿。风吹曝麦地,水溢沃鱼池。常念鹪鹩鸟,安身在一枝。
茅栋野人居,门前车马踈。林幽偏聚鸟,溪阔本藏鱼。山果携儿摘,皋田共妇锄。家中何所有,唯有一床书。
携儿共妇,锄田摘果,而又不废读书,这样的生活,这样的诗歌,都使人想起陶渊明的田园诗来。不过数量最多、最具特色的是寒山后期的山林隐逸诗——寒岩时期的诗作。《平野水宽阔》、《可贵一名山》、《逈耸霄汉外》、《丹丘逈耸与云齐》等,都是对天台山的礼赞。
丹丘逈耸与云齐,空里五峰遥望低。鴈塔高排出青嶂,禅林古殿入虹蜺。风摇松叶赤城秀,雾吐中岩仙路迷。碧落千山万仞现,藤萝相接次连溪。
这首诗写登高遥瞰,摄入了天台山的全景,在寒山为数不多的七言诗中,是气象较为恢弘的一首。更多的诗篇则是记载了诗人自己在寒岩的生活和感受:
重岩我卜居,鸟道绝人迹。庭际何所有,白云抱幽石。住兹凡几年,屡见春冬易。寄语钟鼎家,虚名定无益。
自在白云闲,从来非买山。下危须策杖,上险捉藤攀。涧底松长翠,溪边石自斑。友朋虽阻绝,春至鸟
 。
。
寒山多幽奇,登者皆恒慑。月照水澄澄,风吹草猎猎。凋梅雪作花,杌木云充叶。触雨转鲜灵,非晴不可涉。
寒岩道路险阻,远离人烟。诗人长年隐居于此,摒弃了浮华的人世。“凋梅雪作花,杌木云充叶”两句真是神来之笔,为残败的冬景妆点出盎然的春意,下接“触雨转鲜灵”,春天真的到来,一切迅即恢复了生机,读者可以感受到诗人内心藴藏的旺盛的生命之力。当然,支持诗人数十年幽居寒岩乐不知返的力量,还有他对于佛教精神的感悟,融入诗篇,则属于宗教诗的范畴了。
天台山是道教的名山,也是佛教的圣地。诗人隐居寒岩期间,先后受到道教和佛教的熏陶,他有许多诗篇记载了在宗教领域内的心路历程。他也有一些批判道教和僧侣的作品,并不是宗教诗,只是为了方便起见和宗教诗一同叙述。他对道教的涉猎时间并不长,诗中写到“仙书一两卷,树下读喃喃”,“下有斑白人,喃喃读黄老”,大约是自叙。又有诗云:
手笔大纵横,身才极瓌玮。生为有限身,死作无名鬼。自古如此多,君今争奈何。可来白云里,教尔紫芝歌。
“紫芝歌”相传是秦末商山四皓所作,亦用以指仙歌。寒山倾向道教的契机,仍在于不甘心于人生有限的困惑。不过他终于觉悟了道教“长生久视”之说的荒谬,而痛加揭露:
昨到云霞观,忽见仙尊士。星冠月帔横,尽云居山水。余问神仙术,云道若为比。谓言灵无上,妙药必神秘。守死待鹤来,皆道乘鱼去。余乃返穷之,推寻勿道理。但看箭射空,须臾还坠地。饶你得仙人,恰似守尸鬼。心月自精明,万像何能比。欲知仙丹术,身内元神是。莫学黄巾公,握愚自守拟。
从“心月自精明,万像何能比”等语看,此时的寒山已经入佛,他是援佛以批道。他也批评僧侣:
世间一等流,诚堪与人笑。出家弊己身,诳俗将为道。虽着离尘衣,衣中多养蚤。不如归去来,识取心王好。
对于粗鄙僧侣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对佛教的否定,而是反衬出对禅宗“心王”的倾慕,也不自觉地流露出寒山的居士意识。寒山对佛教的信仰愈老愈笃,这是和他最终对道教的鄙弃不同的。禅宗是中国式的佛教,自从慧能创立禅宗南宗之后,佛教内部便有了教门与宗门的区别。寒山诗可谓深入禅宗三昧,但也有一些宣传教门观念的诗,如云:
生前大愚痴,不为今日悟。今日如许贫,总是前生作。今日又不修,来生还如故。两岸各无船,渺渺难济渡。
把众生的贫困归因于前生的不修,劝勉贫苦的人们为来生的富贵而修福,这当然是佛教的说教。又如寒山的戒杀生食肉诗:
寄语食肉汉,食时无逗遛。今生过去种,未来今日修。只取今日美,不畏来生忧。老鼠入饭瓮,虽饱难出头。
此诗的宗旨与上诗相同。类似的戒杀生食肉诗还有《怜底众生病》、《猪吃死人肉》、《唝唝买鱼肉》、《买肉血 》等许多首。寒山的这类诗歌浅陋粗鄙,并无深义,却是唐代民间佛教信仰的实际形态。
》等许多首。寒山的这类诗歌浅陋粗鄙,并无深义,却是唐代民间佛教信仰的实际形态。
禅宗主张不立文字,明心见性,顿悟成佛。寒山写了一些禅理诗,如云:
寄语诸仁者,复以何为怀。达道见自性,自性即如来。天真元具足,修证转差回。弃本却逐末,只守一场呆。
可贵天然物,独一无伴侣。觅他不可见,出入无门户。促之在方寸,延之一切处。你若不信受,相逢不相遇。
第二首的“天然物”,就是第一首的“自性”,也就是众生皆具的佛性。禅宗追求的目标,就是“达道见自性”,一旦彻见自性,也就顿悟成佛。自性非修证可得,故云“修证转差回”。从诗歌艺术的角度看,寒山的禅理诗并非佳作,倒是他的那些禅悟诗,能够在具体形像的描绘中,创造出一种充满哲理的悟境,予人以深刻的启迪和悠长的回味,如像:
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
以皎洁的明月比喻清浄的心性,本是佛教的习语。众生的心性被烦恼障翳,犹如明月被浮云障翳,所以不能见性成佛。《涅盘经》卷五:“譬如满月,无诸云翳,解脱亦尔,无诸云翳。无诸云翳,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寒山笔下的碧潭秋月,不沾纤尘,犹如心性大放光明,不沾丝毫的烦恼杂念,这是禅宗追求的最高境界,也能浄化读者的心灵,引起无限的沉思遐想。所以寒山诗中屡屡出现这类明月的形象,都有同样的寓意:
众星罗列夜明深,岩点孤灯月未沈。圆满光华不磨莹,挂在青天是我心。
千年石上古人踪,万丈岩前一点空。明月照时常皎洁,不劳寻讨问西东。
这种禅的领悟,已经渗透在寒山的寒岩隐居诗中。寒山与寒岩,心性与自然,已经和谐完美地融合,而达到禅的境界。这正是寒山的寒岩隐居诗引人入胜的永久魅力所在。例如:
粤自居寒山,曾经几万载。任运遯林泉,栖迟观自在。寒岩人不到,白云常叆叇。细草作卧褥,青天为被盖。快活枕石头,天地任变改。
在寒山的世界里,只有寒岩与白云,细草和青天,还有一个任运栖迟的诗人。任随天地变改,他枕石而眠,快活自在,在与自然的融合中,诗人似乎已经化为了寒岩的灵魂,而进入了永恒的境界。
寒山诗的思想虽然驳杂不纯,但仍然有着基本的倾向。过去的佛教徒从他的每一句诗中寻找佛教的义藴,固然是牵强附会,但佛教思想对寒山诗的主导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在他的抒情感怀诗中透露出的人生无常的慨叹,在他的讽世劝俗诗中表现出的悲天悯人的胸怀,在他的山林隐逸诗中达到的禅悟的境界,无不体现着佛教的精神,因此寒山诗是佛教思想在中国诗歌领域中结出的最重要的果实。
拾得诗今存五十余首,少部分与寒山诗相混。由于他自小在国清寺为僧,生活经历单纯,他的诗基本上都是佛教诗,虽可为寒山诗壮大声势,却并没有超出寒山诗的范围。
寒山诗的艺术风格也是多样化的。《四库全书总目》引清王士祯《居易録》论寒山诗云:“其诗有工语,有率语,有庄语,有谐语,至云‘不烦郑氏笺,岂待毛公解’,又似儒生语,大抵佛语、菩萨语也。”大体说来,寒山的化俗诗,多用白描和议论的手法,而以俚俗的语言出之。他的隐逸诗,则较多风景描写,力求创造禅的意境。而不拘格律,直写胸臆,或俗或雅,涉笔成趣,则是寒山诗的总的风格,后人称寒山所创造的这种诗体为“寒山体”。
寒山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八:“寒山子诗,如施家两儿事,出《列子》;羊公鹤事,出《世说》。如子张、卜商,如侏儒、方朔,涉猎广博,非但释子语也。”经史子集的典故,寒山诗时有运用。日本学者入矢义高特别指出:“寒山的魏晋体诗篇所取的古诗,几乎都是《文选》收録的。”佛教典故也常被寒山融入诗中,如:
有树先林生,计年逾一倍。根遭陵谷变,叶被风霜改。咸笑外凋零,不怜内纹彩。皮肤脱落尽,唯有贞实在。
末二句论者或以为是用药山惟俨的名句“皮肤脱落尽,唯有一真实”。其实《涅盘经》卷三九云:“如大村外,有娑罗林,中有一树,先林而生,足一百年。是时林主灌之以水,随时修治。其树陈朽,皮肤枝叶悉皆脱落,唯贞实在。如来亦尔,所有陈故悉已除尽,唯有一切真实法在。”寒山诗典出《涅盘经》,并非转手稗贩。《涅盘经》而外,《法华经》、《维摩经》、《楞严经》等许多佛经的典故,他都随时拈用,得心应手。
寒山诗同时也是以王梵志诗为代表的唐代白话诗传统的直接继承者,他的劝世化俗诗与王梵志诗的俚俗风格十分接近。他们的有些诗篇的主题和题材是相似的,如寒山诗《东家一老婆》与梵志诗《吾家昔富有》,寒山诗《我今有一襦》与梵志诗《家贫无好衣》。有些诗篇的表现手法是相似的,如寒山诗《猪吃死人肉》以猪与人对举,梵志诗《身如圈里羊》以羊与人对举,构思的奇特在文人诗中是极少见的。寒山是继王梵志之后,唐代白话诗派的最重要的作家。
寒山的诗在当时并没有产生社会影响,只是在禅林中流传,有时在禅师上堂时被引用。降至宋代,寒山诗在文人中找到了知音,例如黄庭坚就对包括寒山在内的唐代白话诗派有特殊的兴趣,王安石也写了《拟寒山拾得二十首》,苏轼、陆游、朱熹也都提到寒山的诗,这是因为寒山诗的内容与风格,与宋代的社会思潮有一致之处。不过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寒山诗主要被佛教内部的人士阅读,没有在正统文学中得到一席之地。直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学,寒山诗才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然而随着抗战军兴,寒山诗又被束之高阁了。
然而在国外,寒山诗却有颇为显赫的命运。近几百年来,寒山诗在日本一直受到重视与推崇。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之间,美国被称为“疲惫求解脱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的苦闷青年把寒山奉为偶像,寒山诗风靡一时。如今西方的“寒山热”虽然已经过去,然而寒山诗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已经确立。海外“寒山热”的回流,使诗人重新受到他的同胞的重视与研究。寒山有诗云:
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不恨会人稀,只为知音寡。若遣趁宫商,余病莫能罢。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
寒山的预言已经成为现实,曾经受到冷落的寒山诗,已经流行于天下。在寒山诗的传奇性经历后面藴含的奥秘,还有待人们进一步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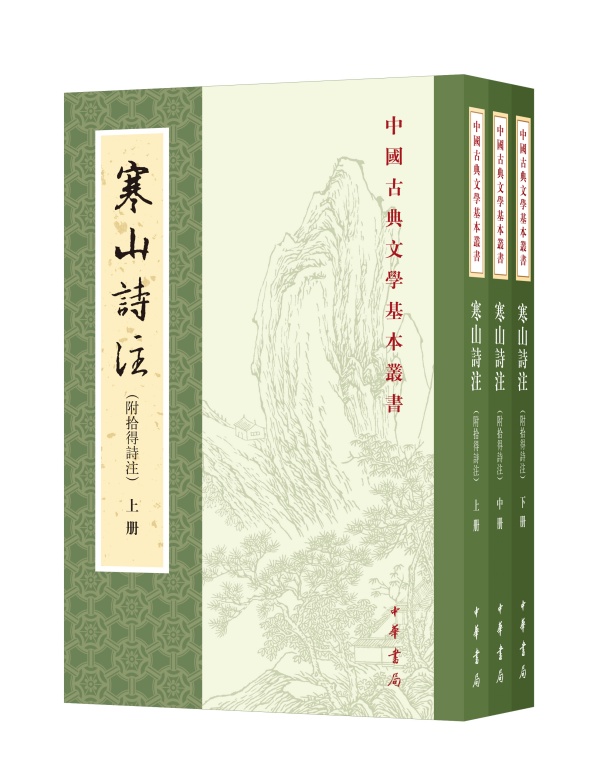
《寒山诗注》是项楚先生关于唐代白话通俗诗歌校注、阐释的一大力作。本书原文以四部丛刊影宋本为底本,校以日藏宫内省本、正中本、高丽本及四库本等传世善本,堪称寒山诗之定本。
本书的注释,除一般生词僻典外,重点在寒山诗所涉及的俗语词、佛教语言典故,特别注重寒山诗语言、寓意的佛教来源以及在禅门、世俗社会运用中的流变。推源溯流,广征博引,探赜索隐,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书注释除充分显示了寒山诗作为文学作品的价值外,在语言学方面(特别是俗语词、佛教语词)的创获极多,甚至称其为语言学专著也不为过;加之贯穿全书的对生词僻典和佛家语的推源溯流式的考释,揭示了寒山诗思想内容、艺术风格、文化意蕴的承传流变,更使本书在文学、语言学的价值之外,具有了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和宗教史的意义。书末附《拾得诗注》。

www.zhbc.com.cn zhbc@zhbc.com.cn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邮编: 10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