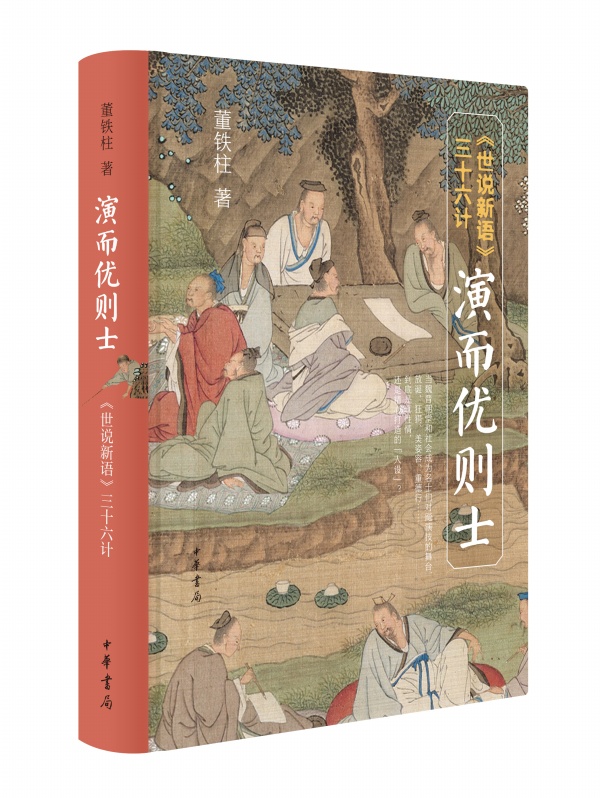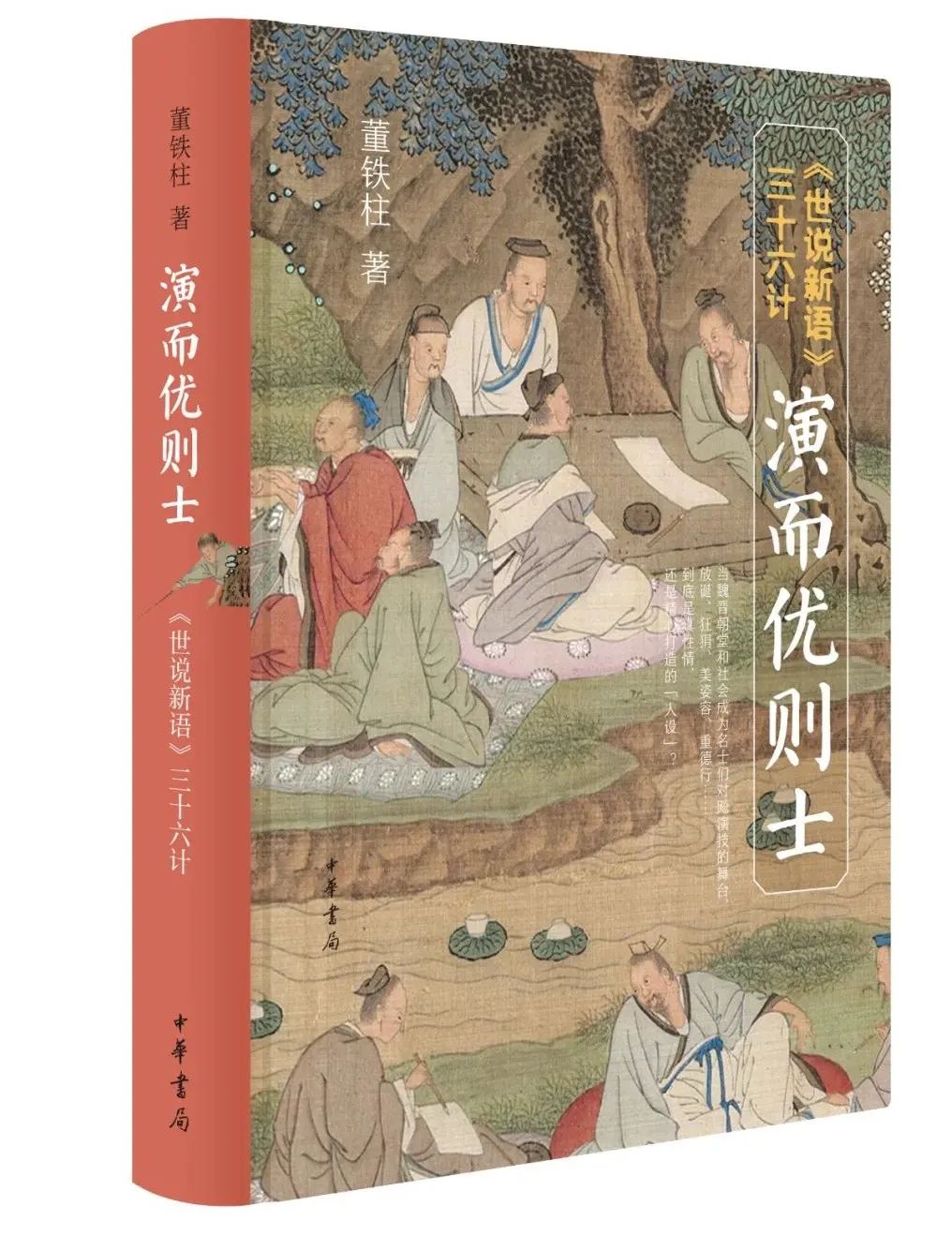
正是因为酒同时代表了礼和知这两个层面的文化内涵,所以它可以被用作触及礼教底线的常用工具。一群人在一起喝酒可以是出于礼仪,也可以是出于欣赏。出于礼仪而在一起喝酒之人,有时候在心里并不一定互相肯定对方。鄙视对方之人就可以利用共饮的机会,借醉来表达对对方的不满或轻蔑。《世说新语·言语》篇第101则载,桓玄有一次拜见司马道子,司马道子已经喝醉了,而当时座上有很多客人。他就问人说:“桓温来欲作贼,如何?”桓玄听了伏地不敢起身。这时候身为长史的谢景重说:“故宣武公黜昏暗,登圣明,功超伊、霍,纷纭此议,裁之圣鉴。”于是司马道子说:“我知!我知!”然后他举杯邀请桓玄喝酒。
这一场面堪称一场精彩的表演。众多的客人是天然的观众,而司马道子和谢景重之间的配合可谓天衣无缝。桓玄的父亲桓温的谋反之心可谓人尽皆知,当司马道子在桓玄来到之后才问这样的问题,可以说是在“醉与不醉之间”,说醉了,那是因为不醉是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的,说不醉,是因为他说话的时机是恰到好处。观众们可以自己判断司马道子的状态,而这样模棱两可的局面正是酒赋予司马道子的。他们甚至没有办法去批评他:在宾客众多的情况下,司马道子即使喝醉都是由于礼的缘故,每个客人来了作为主人都得陪着喝酒,客人多了他就自然醉了。而这些客人是不是司马道子在知道桓玄会来访的情况下故意请来作为观众和证人的,我们这些千年后的观众就不得而知了。
谢景重的回答看似是替桓玄解围,夸赞了桓温的功劳,将其比作了伊尹和霍光,两者都是位高权重却并没有谋反的典范。谢景重的话仿佛是在对司马道子和众人说桓温也是一位忠臣。然而,这段话完全可以被理解为是对桓温的警告,告诫他应该以伊尹和霍光为榜样,不要试图谋反。谢景重和司马道子的一问一答,正是借用酒在公共空间中的角色,对他们所看不顺眼的桓玄提出了劝诫,更是对在场所有人的一次劝诫。很显然,司马道子和桓玄之间并不互相肯定,但是由于和礼的紧密关系,酒依然给了司马道子借用的机会,让他可以公开质疑桓玄及其父亲。这种在清醒情况下属于“失礼”的话,在“醉”酒的场合就容易被人接受。
在《雅量》篇第21则中,身为弟弟的周仲智同样靠酒对大哥进行了挑衅。他在喝醉之后对大哥周伯仁说,你的才华不如弟弟我,却平白获得了赫赫名声。过了一会儿,他甚至举起蜡烛扔向周伯仁。周伯仁笑着说,你这样用火攻,是下策啊!周仲智对大哥的不满大约是由来已久,可是由于为弟须悌的关系,在正常的情况下,是不敢对周伯仁说如此无礼的话的。正是酒给了他这样的权力。
在严格的礼教中,周仲智的自我肯定在外在的压力下无法得以宣泄,向兄长挑衅是一种社会的禁忌。这样的压制也会进一步导致兄弟之间的紧张关系。而用以成礼的酒却能在很大程度上动摇这一礼仪结构的单一坚固性,让礼变得更有弹性。一方面,周仲智酒后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触犯了礼法,释放了内心的自我;但是另一方面,他的举动并没有从正面肯定自己,反而暴露了自己的狭隘,恰恰给了他的兄长周伯仁一个展示其雅量气度的机会。就这样,通过酒,周仲智用冒犯兄长的言行增加了兄长的威望,主观上触犯礼仪的行为却在客观上维护了礼仪。
然而,要使酒能起到通过触犯礼法而让礼法更有弹性的功能,也需要被触犯一方的配合。就本质而言,酒只是工具,重要的是使用工具的人。如果被触犯的一方只是把对方的行为看成是对自己的冒犯,而没有认识到礼的弹性,并利用这一机会展示自己的气度,那么就会变得尴尬。《方正》篇第54则载,王濛、刘惔有一次和桓温一起去覆舟山玩,酒酣后刘惔把脚放在了桓温的脖子上。桓温很是不开心,用手把刘惔的脚拨开了。回来后王濛对刘惔说,他难道可以对人发怒的吗?这则故事的微妙之处在于王濛的话并没有当着桓温的面说,而是在回去之后对刘惔说的。
刘惔酒后之举和上一则故事中周仲智所做的相似,都是借酒来做平时不被允许的无礼之举。王濛的话表明,这样的举动在酒后是被允许的,这是公共空间的游戏规则,因此桓温不应该发脾气。而王濛之所以不和桓温解释,也许是因为他觉得既然桓温不理解或是不接受这样的规则,那么桓温就是不属于同一公共空间的人,解释对他来说是没有必要的。在第一章中,我们已经讨论过桓温在清谈的场合对王濛等人表示了蔑视,可见王濛、刘惔等人和桓温之间不但没有互相肯定,反而是互相轻视的。可是,为何桓温和王濛等人相互看不上,却又保持着相对紧密的联系,经常在同一公共空间参与清谈或饮酒呢?难道不是互相欣赏之人才会选择共饮的吗?
对于这个问题,刘义庆的叙述并没有给我们明确的答案。但是这一现象告诉我们的一个事实是,魏晋名士参与公共空间活动的界限是模糊的。名士间的交往并不存在着非此即彼的原则,即使是自己所鄙视的人,也可能出现在相同的公共空间内。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可能会选择坚决不与自己所不欣赏的人共饮,然而这样的坚持只能局限在相对封闭的空间之中。在较大的公共空间中,名士们有很多机会和各类人共饮,这也再次证明了公共空间的开放性。
《世说新语》中与酒相关的各个故事告诉我们,饮酒对于魏晋的名士来说,似乎并不仅仅是一种生理的需要,而且和个性无关。魏晋时期绝大部分的名士都有着酒瘾,这种瘾更像是布迪厄(Bourdieu)所说的生存心态(habitus)的体现。由于社会对酒的推崇,在名士们的个人意识中充满了对酒的向往,从而试图从多方面通过酒来展示自己。这种瘾更多的是来自内心,是一种渴望在公共空间中“战胜”他人的社会需求。他们通过酒来展示自己的个性和态度,也表达了自己对他人的判断或欣赏,而重要的是,他们所显示的价值判断表明,好酒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并不是全然的颓废或逃避,也不是彻底的狂放,更不是一种对现实反抗或是对自由的追求,而是在遵循一定的社会礼仪、习俗和规则的情况下,对自己才性的展现。
嗜酒的名士们同样遵循着“将无同”的原则,一方面认可酒与礼的密切关系,在公共空间内通过酒来表明自己对既有社会体系的认同,而在另一方面,则利用酒可以让人“醉”的特点,通过各种极端的方式来表现自己对于礼仪、社会和他人的独特见解。也就是说,名士们在酒的世界里所展现的个性,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对抗这个社会的规则,而是对这个社会的规则作了自己的诠释。而这样的诠释和清谈有着一样的效果,可以让他们在与同侪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豪爽》篇第13则中说,王敦每次酒后就吟诵“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然后用如意击打唾壶,壶口都破损了。这则故事很好地说明了名士如何通过酒来表达自己的态度。王敦所吟咏的是曹操的诗句,而曹操的身份人尽皆知,王敦此举从广义来说是用曹操的诗句来激励自己,而从狭义来说则是向大家表明自己的野心—要成为曹操这样手握大权之人。然而,王敦在且只在酒后吟咏,这首先是因为他要表达的是对当前社会体系的认同,他不想公然做一个乱臣贼子,同时他也想展示的是在认同的前提下,对当前社会的不满以及做出相应改变的抱负,然而这种理想绝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定社会的制度。至于他究竟是想篡权夺位,还是想做一个匡时救世的重臣,这就让观众有了自己判断的自由。这样“有意无意之间”地表述自己的态度,正是由酒赋予了这种可能性,而在抛却一般的善恶准则的前提下,王敦通过酒所表达的态度是积极的,正面的,而不是消极的,颓丧的。这正是《世说新语》向我们所展示的名士们和酒之间的关系。
本文节选自董铁柱著《演而优则士——〈世说新语〉三十六计》,略有删减。
往期精彩
《谭其骧历史地理十讲》《演而优则仕》入选搜狐文化2022年度好书之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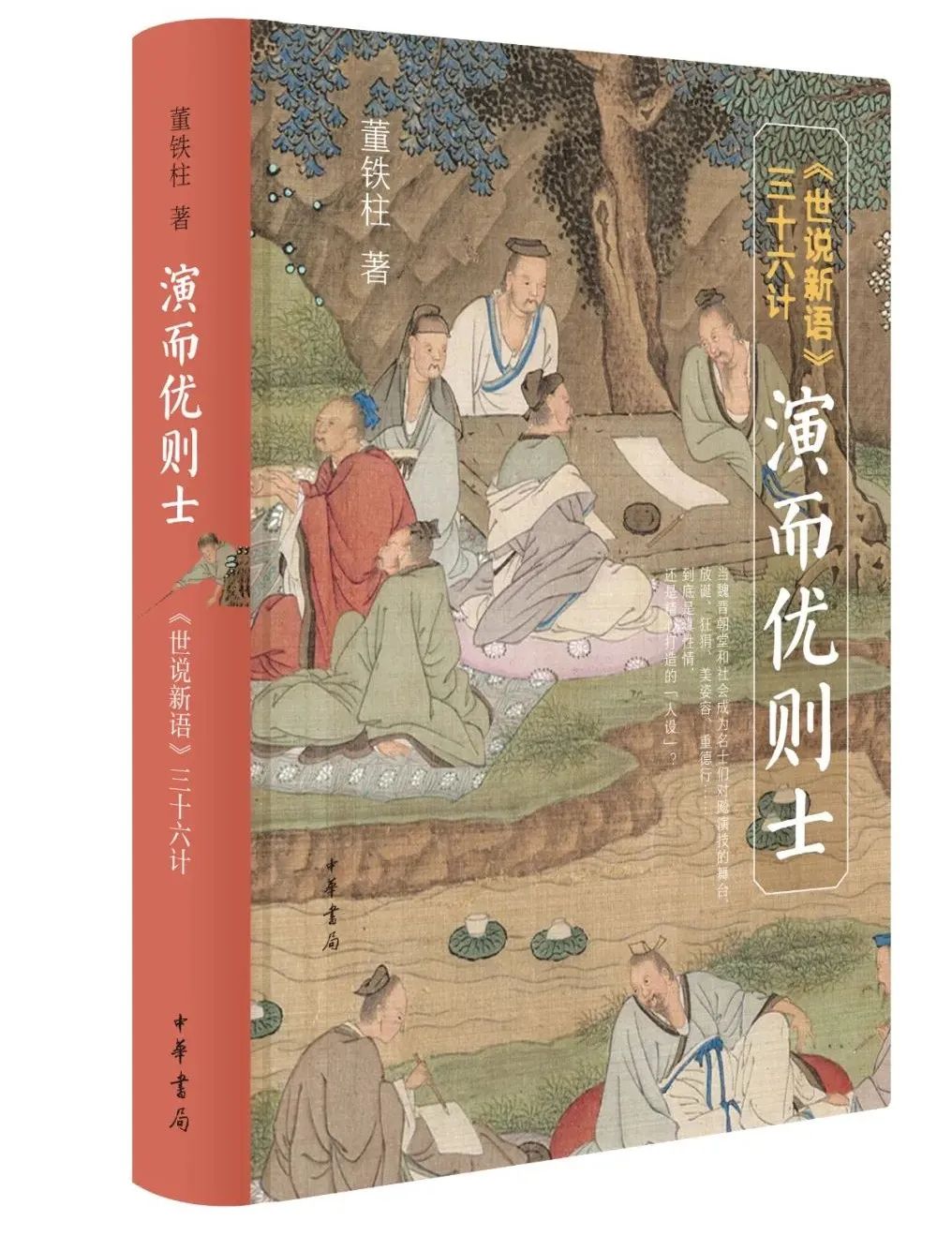
基本信息
著 者:董铁柱
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编辑推荐
1.这是别具一格的“有魅力的魏晋读本”。提起《世说新语》和其中以魏晋名士为代表的魏晋风流,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自由、个性、反抗等标签。本书一反老生常谈,认为魏晋名士的风流洒脱、放荡不羁并不是真性情,也不是所谓“个性的觉醒”,而更像是一场场经过精心谋划的“表演”,需要“观众”看到并广为传播,借助这条路径,以获得更佳的社会性利益,如声誉、地位、官阶等,所谓“风流”,只不过是一种精心且刻意的营造。这种基奠于《世说新语》文本的别样解读,令人耳目一新,鞭辟入里而又逻辑自洽,读来引人入胜。
2.《世说新语》分为三十六门,在作者看来,更像是名士们谋求脱颖而出的“三十六计”。三十六门不论褒贬,每位名士或有侧重,都可以看作名士与众不同的三十六个方面,作者认为这些是名士们刻意表现的特质,目的是打造一个个专属“人设”,塑造自己想要的社会形象,从而跻身所谓名士之列。
3.读本书如同看剧,酣畅淋漓的同时而又别有会心。作者师从著名汉学家魏斐德,秉承西方历史写作传统,重叙事,以通俗悦读为目的,这样来聊《世说新语》和魏晋名士,除了讲述种种有趣、颇富韵致的故事外,更深一层,浑化故事背后蕴含的社会学动因于全书之中,并且加之以出色的心理分析。这样,专业读者能看到对经典的不同解读,而普通读者就仿佛看戏一般,看着这些魏晋之际的大名士上演一幕幕活剧,评判哪个的演技更为高超。


www.zhbc.com.cn zhbc@zhbc.com.cn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邮编: 10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