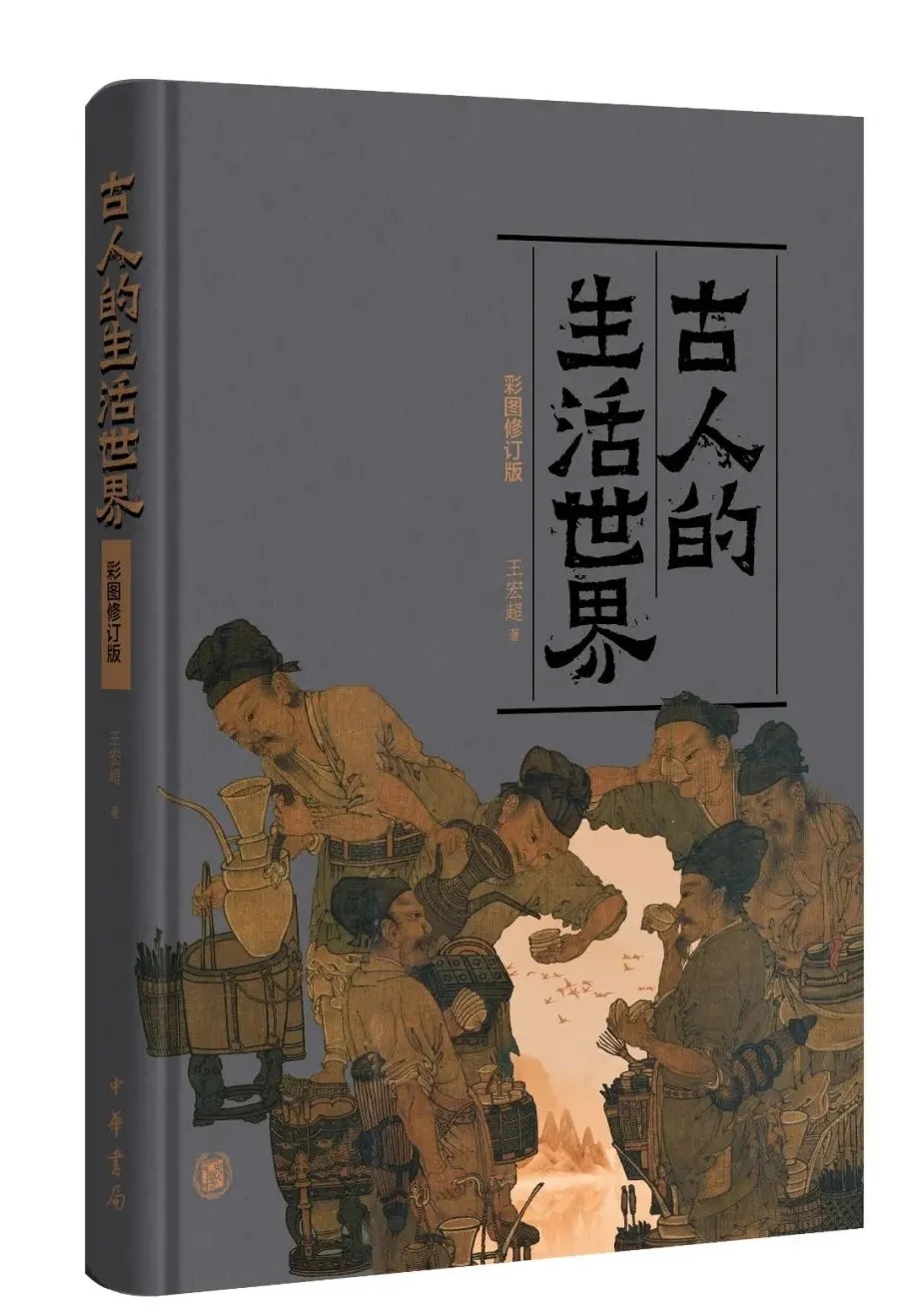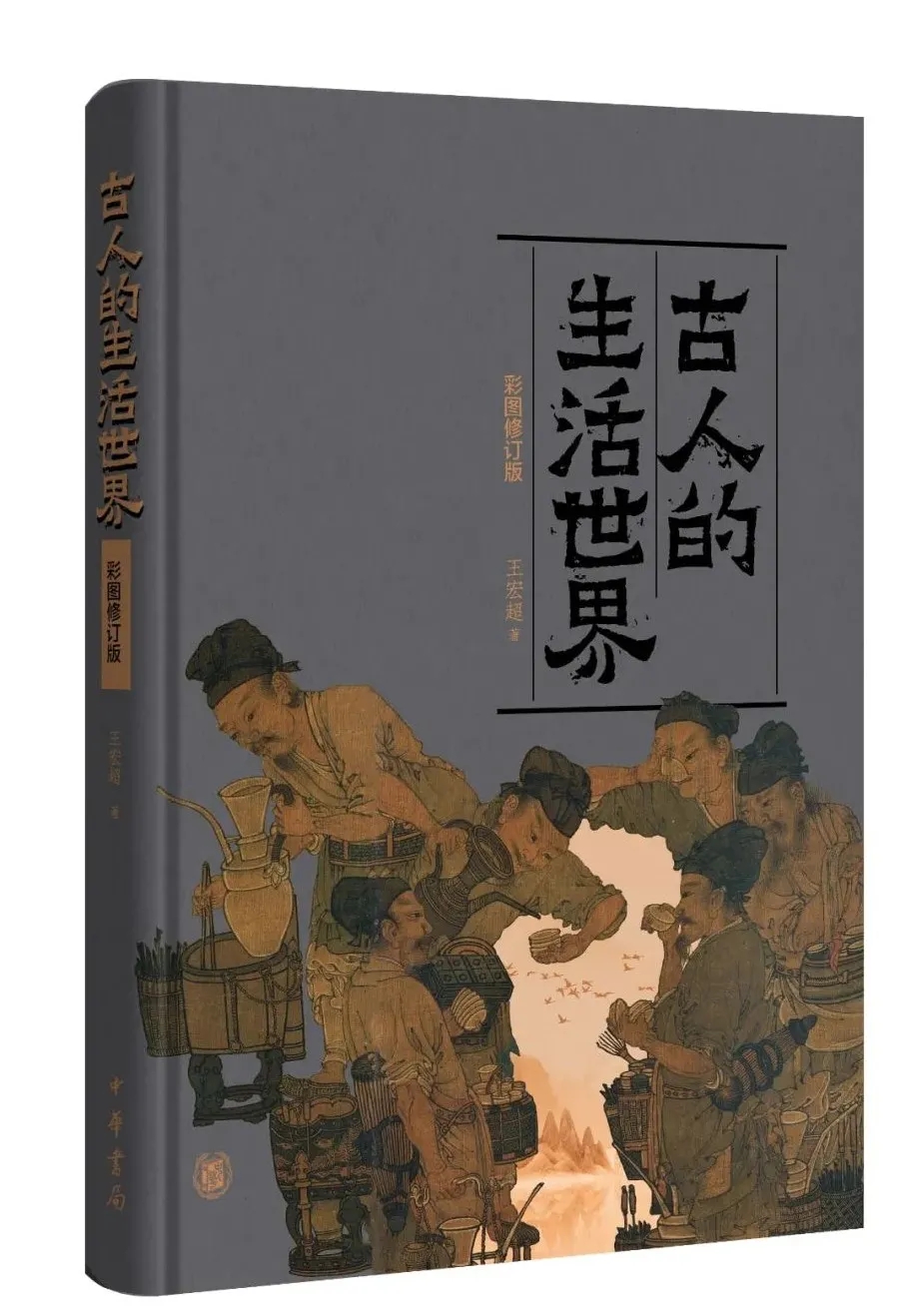
昼起夜伏的观念
社会学家李景汉在《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一书中,还提出了另外一个解释,那就是照明的成本。
此书调查的对象是民国时期的北京,但其中反映出来的一些情况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来说也是基本适用的。
书中谈到民国时期农民家庭的照明,一般使用煤油。“在夏季,昼长夜短,许多贫家不用灯火,只在冬季天短时每晚用油少许,每月少者约用一斤,多者约用二斤,每斤价约八分。普通人家在暖季每月约用一斤,在冷季每月约用三斤。”
在对一个村庄的调查中,平均每家一年花费二元。而这个村庄的收入情况,每家年收入在一百元上下,照明费用占年收入的百分之二;全村一百多户人家,蔬菜消费未满五元的有三十六家,占三分之一多,所以两元的煤油费用,也算是一笔不大不小的开支了。
古代官方在一些节假日中张灯结彩,要求百姓挂灯,许多百姓都难以承担这笔对他们来说很高昂的费用。
夜晚的时间管理
古人昼起夜伏的生活方式受到了自然的限制,在照明条件落后的情况下,晚上无法做更多的事。同时,时间的安排除了遵照自然规律以外,还受到社会管控因素的影响。
对于时间秩序的管理,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对于夜晚,历代官方都有严格的管理制度,这称为夜禁制度。
“禁民夜行”,夜间人们不能随意出行,行为方式受到了很大的约束。
白天的世界如果说是光明的、理性的、有秩序的,那么黑夜则代表着黑暗、非理性、混乱与罪恶。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中就规定:“其夜禁之法,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违者笞二十七下,有官者笞一下,准赎元宝钞一贯。”
昼伏夜出,夜聚晓散,是对昼出夜伏秩序的打破,在官方看来,就代表着罪恶、奸盗之事。
宵禁制度也与城市防火有关。
古代建筑多用木材,而城市中人口密集,房屋距离很近,一旦失火,局面往往容易失控。
尽管古代的城市建立了在当时来说比较完备的消防系统,比如南宋时的杭州城,城内有消防军卒2 000多人,城外有1 200多人,配备有水桶、绳索、旗号、斧头、锯子、灯笼、防火衣等装备,但城市防火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马可·波罗对于杭州城的灯火管制印象深刻,他专门记录说:“守望者们的职责是,在法定禁火的时刻到来之后,看看还有谁家露出任何火烛之光。如果他们发现到了,就会在其门上标上记号,而一大早房主便会被传唤到官吏面前,如举不出正当理由,便会受到惩处。同样,在法令禁止的时间内如果他们发现有任何人在街头乱走,亦会将其拘捕,并于次日清晨将其押送给官吏。”(〔法〕 谢和耐著,刘东译《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
夜间的狂欢
一个人的生活要有张有弛,如果一直处于紧绷状态,长此以往,就会造成精神和心理的失衡。
一个社会也是如此,平时政府对社会有严格的管控,但也会在一些特殊的日子放开各种禁令,让人们得以放松。
在各个民族、文化中,都有狂欢节,就是通过狂欢的方式来释放被压抑的生命本能,从而使社会心理得到平衡。
古代中国的狂欢节就是元宵节,在这天,官方会破例取消夜禁,称为“放夜”。
“元宵不禁夜,自汉始”,在元宵节前后的几个夜晚,都是“金吾不禁夜”,普通百姓得以肆意狂欢。
统治者之所以愿意弛禁,让百姓在节日中娱乐狂欢,除了让百姓得到放松和休息的目的之外,或更在意于从节日的色彩与斑斓之中彰显社会祥和繁荣的气象。
就如清人描述扬州灯节之繁华,虽不及原来,但“银花火树,人影衣香,犹见升平景象”(清黄钧宰《金壶七墨全集》卷四),以此来提振社会之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维护统治秩序。
夜 市
古代的夜市也十分红火。《东京梦华录》记载,宋太祖撤销宵禁之后,汴京城中,“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
南宋时期的杭州,夜市非常流行,《梦粱录》中说:“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按照现在的时间刻度,四更结束已是凌晨三点,此时“游人始稀”,可见夜间活动的人很多,夜市也十分发达。五更时,卖早餐的商贩就开业了,市场几乎是全天候经营的。
这种发达的夜市,一方面说明人们的夜间活动丰富,另一方面也说明经营活动的多元化,给人们的休闲生活带来了更多的便利。
从一个细节可以看出夜市中酒楼的繁荣热闹—汴梁夜市中没有蚊子,原因是因为酒楼中油烟太多:“天下苦蚊蚋,都城独马行街无蚊蚋。马行街者,都城之夜市酒楼极繁盛处也。蚊蚋恶油,而马行人物嘈杂,灯火照天,每至四鼓罢,故永绝蚊蚋。”(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四)
还有一种“夜市”,从事的不是正常的商业行为,而类似于一种“黑市”,主要用于销赃或秘密交易。
在清代的南京,就有这样的“夜市”:“在笪桥,每五更,人各以所售物至,不举灯,惟暗中度物,又不出声,或价物两直,或得利数倍,率以为常。旧传以为偷儿所窃物,故以此时私鬻,其实不然,大抵皆故家儿,不欲显言家物,忌人之知,以为耻耳。然故诗有云:‘金陵市合月光里。’则夜市之由来久矣。”(康熙《江宁县志》卷三)
晨起与夜晚的结束
四更(1—3点)或五更(3—5点)往往就有人晨起,或苦读,或远行,或劳作,或买卖。
凌晨时有不少专门的报晓者,多由寺院僧人来承担,“每日交四更,诸山寺观已鸣钟,庵舍行者、头陀打铁板儿或木鱼儿,沿街报晓,各分地方”(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
北宋时也是如此:“每日交五更,诸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亦各分地分,日间求化。诸趍朝入市之人,闻此而起。”(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
报晓的同时,也会兼顾提示天气情况,还形成了专门的术语:“若晴则曰‘天色晴朗’,或报‘大参’,或报‘四参’,或报‘常朝’,或言‘后殿坐’;阴则曰‘天色阴晦’,雨则言‘雨’。”(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
“三更灯火五更鸡”,五更时分代表着新一天的开端,中国人向来勤奋,从五更时就陆续开始忙碌,一夜的欢乐时光也到此终结。
总之,古人在夜间的休闲生活十分丰富多彩。“两行宝炬照华堂,一派笙歌夜未央。”(明屠隆《夜饮李将军帐中》)华灯初上,人们似乎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之中,彻夜笙歌,把酒邀月,欢愉无限。
本文摘选自王宏超著《古人的生活世界》
往期精彩
古人近视了怎么办?街头竟也有“奶茶”买?这本书把古人生活世界还原了
推荐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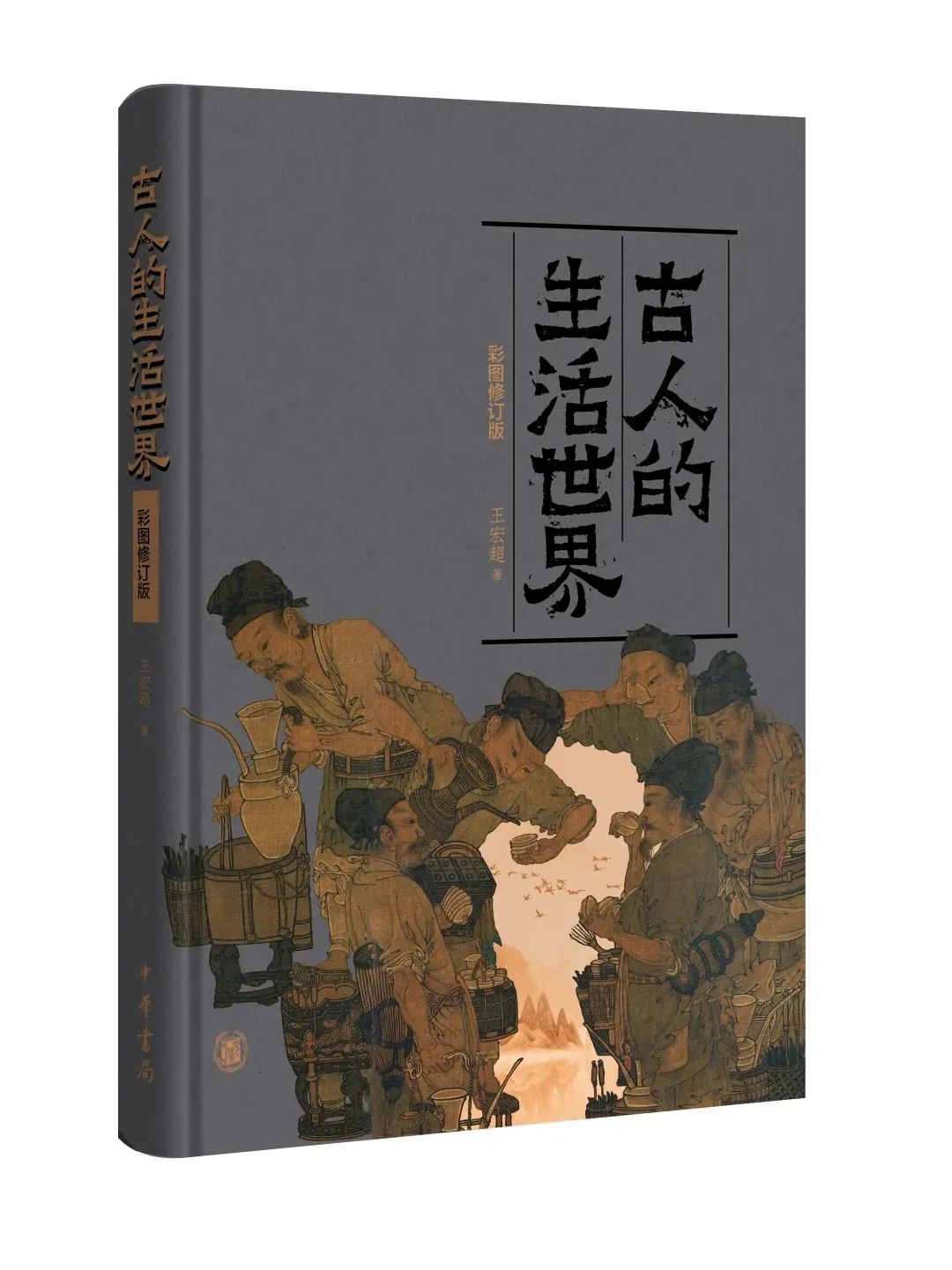
著 者:王宏超
书 号:978-7-101-15453-5
出版时间:2022年1月
定 价:68.00元
内容介绍

作者介绍


www.zhbc.com.cn zhbc@zhbc.com.cn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邮编: 10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