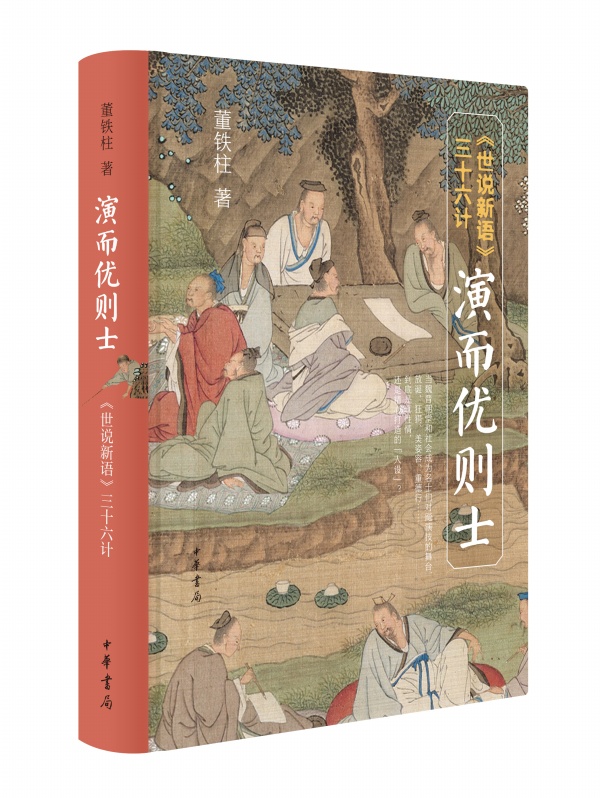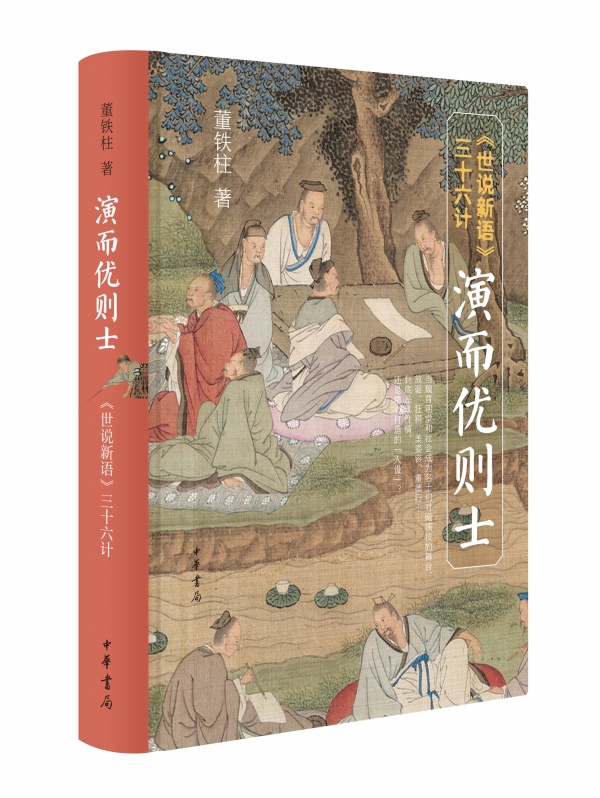
刘义庆明确地告诉我们,肤白、貌美和眼亮等只不过是容貌,所谓“容止”,容貌之外,还有举止。因此,单纯用长得好来形容魏晋时的帅哥是不全面的。在刘义庆的叙述中,有关举止的故事通常更为生动—这当然可能是因为举止本身就是动作,而动作则具有更强的表演色彩。
《容止》篇第35则说海西公司马奕在位时,大家每次上朝的时候朝堂还昏暗,只有会稽王司马昱来的时候,器宇轩昂,像是朝霞进来了一样。其他上朝之人站在昏暗的朝堂之中,正是理想的观众,而司马昱的器宇轩昂也被他们所见证。这样的情况下,司马昱的容貌如何已经不再重要,观众已经被彻底折服。这则故事中最关键的一个词是“每”,所谓“诸公每朝”,即当大家每一次上朝都有这样的印象时,司马昱也就成了他们心中不会磨灭的印记。事实上,这则故事虽然看似只字未提及政治,但却是不折不扣的一个政治预言。刘义庆同时代的读者肯定都了解晋废帝司马奕在被桓温废黜后,接替其位的正是简文帝司马昱,而朝霞和太阳(天子象征)的联系也属于常识。西晋诗人张协的《杂诗》中便有“朝霞迎白日”这样的诗句。因此,刘义庆在这里从容止的角度来解释桓温废司马奕而立司马昱的原因:给昏暗的朝堂带来亮色的是司马昱,而不是当时的皇上司马奕,司马奕在举止上完败于司马昱。难怪有的学者认为《世说新语》所描写的公共场合虽然看似轻松愉快,实则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竞争比赛。
《容止》篇第38则的故事也颇为有趣:
庾长仁与诸弟入吴,欲住亭中宿。诸弟先上,见群小满屋,都无相避意。长仁曰:“我试观之。”乃策杖将一小儿,始入门,诸客望其神姿,一时退匿。
如果说司马昱的直接观众是众位朝臣的话,那么这则故事中的观众首先是客舍中的老百姓,也就是“群小”。也许有人会问,“群小”有没有足够的判断和鉴赏能力,孔子不是将“小人”和女子并提的吗?既然前文中潘安携弹弓出洛阳被妇人包围可能暗带讥讽,那么这里是否也对庾统有所微词呢?
事实上,作为间接观众的刘义庆已经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潘安是被妇人轻佻地包围的,而庾统则使“群小”自动地让开。这意味着庾统的举止神态中自含着“恭”,从而可以让“小人”感到敬畏。司马昱能获得同侪的赞赏,而庾统则能令他人敬畏,刘义庆告诉我们这才是魏晋名士的容貌和举止所应有的效果。而这两则故事的共同点则在于,刘义庆其实根本就没有写司马昱和庾统的具体举止,两人的举止完全是通过观众的反应让我们自己想象的。也就是说,和容貌有着相对具体的标准相比,举止实际上并没有可以遵循的准则。如果容貌是“有”,那么举止则是“无”,它的评判标准是依赖于观者的反应的。
当举止的重要性大于容貌的重要性时,男性之美的定义已经悄悄有了变化。这意味着那些长得并不貌美、肤白或是眼神炯炯的名士们,也能够靠举止和气度来获得他人的肯定,甚至在公共空间的间接比拼中战胜别人。在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士名单上,刘伶就是一个长得又矮又丑却很著名的人物。《容止》篇第13则说:“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土木形骸”是个颇有意思的形容,一般指的是不加修饰,《晋书 · 嵇康传》中也用这个词来形容嵇康,因此在当时应该算一个褒义词。如果和之前所说的魏明帝与何晏的故事,以及对裴楷的描述联系在一起来看,何晏(至少在《世说新语》中)也并不敷粉雕琢,而裴楷“粗服乱头”也很好,尽管没有人用“土木形骸”来形容何晏和裴楷,但是三则故事对崇尚自然的推崇却是一致的。在整个《容止》篇中,并没有笔墨述及名士们如何细心打扮,也没有任何当时的评论赞叹名士们的装扮,也许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刘义庆所想展现的魏晋名士对所谓人本身之美的态度,是在重视容貌举止的同时又崇尚自然,反对人为的修饰。这样对美既重视又不重视,正是清谈之时“有意无意之间”的原则在容止上的体现。
而提出“有意无意之间”的庾子嵩对容止的态度也正是如此。《容止》篇第18则说他“长不满七尺,腰带十围,颓然自放”。很显然单从外面来看,庾子嵩是一个矮胖子,但是他似乎并不在乎自己的外表,“颓然自放”正给人一种颓放不羁的感觉。说是似乎,是因为既然刘义庆在《容止》篇中提到他,那么说明庾子嵩矮胖而颓放的容止在当时应该具有相当的知名度。事实上,在《赏誉》篇第33则中,刘义庆借庾亮之口明确地夸赞了庾子嵩。当时司马越的府上有很多名士,都是当时的俊秀出众之人,而庾亮说:“见子嵩在其中,常自神王。”在这么多的名士之中都能脱颖而出,充分说明外表非常普通甚至有些丑陋的庾子嵩在风度神态上完胜他人。不在乎外表而能获得关于容止的正面评价,这表明庾子嵩在客观上获得了他人的肯定,而其主观究竟是否有这样的动机,则可能是在有意无意之间吧。
在刘伶和庾子嵩的对比之下,回头再看《容止》篇第9则中同样长得很丑的左思,就可以比较出他的境界低于刘、庾二人了。左思长得丑,这本来并不是问题;他的问题在于他想拙劣地模仿潘安,寄希望于用弹弓来增加自己的魅力,而不知道魅力其实就在于自身的不加修饰。实际上,以左思之才,如能颓然自放,必也是一时风流人物。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左思和潘安年纪相仿,在他想要“东施效颦”般模仿潘安的时候,也是一个年轻人。众所周知,左思在二十二岁左右因妹妹左棻入宫而举家迁入洛阳,在此之后左思花了十年时间才写成《三都赋》。也就是说,当他初到洛阳想要模仿潘安的时候,他对自己的文才—或者说对自己—还没有后来的那般自信,因此才希望通过所谓的风流举止来获得他人的肯定,以至于反而受到了羞辱。那么,刘义庆在叙述中是否暗含了对年轻人的批评,认为懂得安于貌丑需要生活阅历和年龄呢?从《容止》篇来看,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受到赞赏之人,几乎都是有一定年龄和地位之人。这也就更加证明了当时对于男性之美的态度:“才”才是根本,是比单纯的美貌更重要的元素,也就是说,“才大于貌”,貌需要在和才相称的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而对于才的理解,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狭义的才华,有学者指出“才”可以被视为“人的品貌气质等内在才质”,因此,本章中所说的“才”,主要指的是一种超然自得的气度。
东晋时的丞相王导对自己儿子王恬的评价就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容止》篇第25则说:“王敬豫有美形,问讯王公,王公抚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称!’”有趣的是,故事中在王导这句话的后面,还有一句他人的评价:“敬豫事事似王公。”
这个故事可以有多层次的解读,不过无论哪一层面的解读都凸显了才对于貌的重要性和优先性。首先,我们可以理解为王导真的对儿子王恬不满意,认为他有貌而少才。如果是这样的诠释,那么后一句话就可以有两种理解: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对王导的暗讽,既然他儿子王恬处处都像他,那么王恬没有才的话,王导也就自然地缺乏才华;我们也可以将它理解为对王恬的夸赞,虽然王导对儿子不满意,但是这是他对王恬要求过高,事实上王恬和他一样优秀。
同样,我们也可以把王导对儿子的评价理解成一种表演。也就是说,王导并不是真的不满意他的儿子,而是希望通过对儿子的感慨来让世人知道才的重要性,也让世人不要片面地重视和欣赏美貌。这样的表演正是孔子和学生之间表演的延续。如前所述,孔子指责樊迟或是宰我这样的学生,很可能并不是真的认为他们不行,而是通过指责他们,来警示他人或是后人要注意相关的问题,所以从本质来说孔子对爱徒的指责是他们合作的一场表演。为了让表演具有震撼力,孔子往往会挑选自己的得意弟子进行批评。如果我们对王导的话作这样的诠释,那么王导选择爱子王恬作为批评的对象也就可以理解了,因为这样可以更好地让他人了解其观点。而当他人说王恬处处都像其父王导时,他们可能是真的在体会到王导的苦心之后,对王导和王恬父子作了夸赞。
从《世说新语》其他几则关于王恬的故事来看,他似乎是一个在被赞扬和批评之间的人,批评他的是自己人王导,赞扬他的则都是外人。《德行》篇第29则说王导见到长子王悦就很开心,见到王恬就“嗔”;而《赏誉》篇第106则中简文帝夸王恬为“朗豫”,刘孝标引《文字志》注解说:“恬识理明贵,为后进冠冕也。”把王恬作为后辈的榜样,这样的评价不能不说非常高。《简傲》篇第12则中谢万想去拜访王恬,谢安事先劝他说王恬不一定会招待你。结果谢万去后,王恬果然洗头又晒头发,就是不肯搭理他。谢万生气而回,谢安评价说,王恬只不过是不做作而已。谢安事先事后所言,都表明他对王恬非常了解而且欣赏。如果我们参考阮裕对谢万的评价,就知道王恬不屑与谢万交往是有缘由的。《简傲》篇第8则中,谢万当着兄长的面就要尿壶。当时阮裕在座,就说:“新出门户,笃而无礼。”正是由于谢万这样的做派,当王恬看似对他“怠慢”时,反而体现出王恬的价值判断。
即使是在《忿狷》篇第3则中,王恬面对言语有冒犯之意的族兄王胡之变了脸色,也是不做作的表现。在这几则故事中,王恬很显然是一个有“才”之人,其做派完全符合当时的名士之举。如此看来,被王导批评而被外人赞扬是《世说新语》中王恬的人设,《容止》篇第25则并没有脱离这一模式。因此,将王导的批评视作一种孔子式的表演,也属合乎情理。当然不管怎样,这则故事最重要的是王导要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才,那么貌也就失去了基础,当然,这里的才指的还是气度,而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才华。
《容止》篇第21则中,周伯仁评价王濛的父亲王讷说“形貌既伟,雅怀有概”。这也是从才、貌两方面来赞扬王讷的:魁梧而俊美,又有高雅的情怀和非凡的气度。而周伯仁的下半句话也值得玩味,“保而用之”,王讷才可能卓有成就。也就是说,貌和才是需要珍视、保持并在生活中发扬光大体现出其价值的。这则故事的重要性在于,周伯仁的这句话指出了貌和才需要持续性,这意味着灵光一现的人是不会得到真正的肯定的。
之所以说才大于貌,从某种意义上也正是因为和貌相比,“才”的持续性有着更大的难度。虽然通常有美人迟暮之叹,但是既然有公孙弘花甲之年以貌美而被赏识的先例,已经充分说明在古人看来,男性貌美的持续性并不短,短的是“才”,因为有些人的才可能是假装的,对于假装有气度的人来说,也许只有在假装的一刻才显得“有才”,而在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不过是个俗人。
《世说新语》讲述了庾亮因气度不凡而被人怀疑假装的故事,这表明在当时假装有气度的人应该不在少数。《雅量》篇第17则说,庾亮风度仪表都非常出众,举止又端庄持重,当时的人都以为是假扮的。庾亮的长子才几岁,就和他父亲一样端庄持重,大家都知道这是天性。温峤有一次躲在幔帐后面吓唬他,这孩子还是神色恬然,且慢慢跪下问温峤为什么要这样做。大家都认为他完全不输给自己的父亲。有的人说,看见庾恭的样子,就知道庾亮的气度不是假的。
如前所述,学潘岳的左思就有想假装风流的意思。而在《假谲》篇第13则中,范玄平就是想假装对做官没兴趣却被人识破,从而丧失了他人的赏识。话说有一次他刚好丢了官,因桓温在南州势力很大,他就前去投奔。桓温正想招揽人才,之前也知道范玄平的名声颇好,所以很高兴。一开始两人相谈甚欢。桓温对袁虎说:“范公且可作太常卿。”很显然这时候范玄平的“才”获得了桓温的肯定。然而这样的肯定是短暂的,因为范玄平的伪装支撑不了太久。虽然其实他是真的来投奔桓温想捞个一官半职的,但一听桓温这么说,就怕别人觉得自己过于功利从而损了自己的名声,于是赶紧说自己之所以到这里来是因为儿子葬在此处。桓温马上就对他特别失望,之前的好感也消失殆尽。由此可见,某些人的才可能是伪装出来的,所以像庾信这样的真才才更为难得!也正因如此,才才比貌更为重要。
才比貌更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美貌只能吸引俗人,而气度才能征服名士。这并不是说貌美之人就一定没有才,而是说美貌本身是外在的,即使是普通人都能够发现并欣赏,而且普通人只会停留在欣赏美貌的层面。同样,这也并不说明名士们就只重视才而不在乎貌,相反,他们也一样欣赏男性之美貌,但他们更欣赏的是才。
《容止》篇第19则所讲的故事最为戏剧性地体现了俗人欣赏美的方式。当时著名的帅哥卫玠从南昌到南京,因为他实在太出名了,所以前来看他的人多得像一堵墙一样。卫玠本来身体就不太好,在这样的情况下更是累得不行,就生了病直至去世,当时人把这称作“看杀卫玠”。
这则故事所蕴含的可悲之处在于卫玠其实除了貌美之外,具有真正的才华,无论是气度还是清谈都属一流。当初卫玠从洛阳到南昌投奔王敦时,王敦“相见欣然”(《赏誉》篇第51则),欣赏的正是卫玠之才,但是俗人们只能欣赏外在的容貌,而且是以破坏性的方式粗暴地欣赏,最终甚至导致了卫玠之死。
而真正的名士们才可能既欣赏他人之貌,又欣赏他人之才,而且这样的赏识是具有活力的,甚至能让被赏识者绝处逢生,与卫玠被看杀成鲜明的对比。《容止》篇第23则说苏峻叛乱后,东晋政局动荡,温峤和庾亮想要去江西投奔陶侃。陶侃说苏峻作乱本来就是庾家多人造成的,就是应该让他们都被杀了。当时庾亮在后面听到了很是担忧。改天温峤劝庾亮去拜见陶侃,庾亮很是犹豫。温峤就说我很了解这家伙,你去好了,不用担心。结果庾亮“风姿神貌”,陶侃一见面就改变了态度,又边吃边谈了整日,“爱重顿至”。
这则故事中的“容止”和“知”的关系至少有两层。第一层当然是庾亮和陶侃之间的。原本恨不得庾亮去死的陶侃在一见庾亮之后顿时改观,这是由于庾亮的貌美;而两个人能谈一整天,最后使得陶侃对庾亮“爱重顿至”,这是由于庾亮的才。如果庾亮没有貌,陶侃可能一开始就不会好好招待他;而如果庾亮只有貌,那么在一天的谈话中陶侃也可能会失望。一方面庾亮在容止的两方面—才与貌—都出类拔萃,另一方面陶侃也能够发现并欣赏庾亮的才貌。因此庾亮才在绝望之时迎来了转机,可以说在这一次的比拼中庾亮获得了完胜。
而第二层关系则是庾亮和温峤的。两人是多年的好友,故事中也充分体现了温峤对庾亮的“知”。在前面所讲的故事中,当有人认为庾亮的举止是假扮的时候,是温峤出来吓唬庾亮的儿子。如果孤立地来看那个故事,很容易以为温峤也觉得庾亮是假装有气度的。可是当遇到危难之际,温峤还是如此相信庾亮的才貌足以征服陶侃,说明他对庾亮非常了解。那么回头再看他吓唬庾亮儿子的举动,就完全有可能是他为了打消他人对庾亮的怀疑而和庾亮儿子所作的一场表演。这其中小朋友当然并不知情,但是温峤也非常了解庾亮爱子,相信即使小朋友事前并不知道他的苦心,表演也不会砸。这正是从容止到知的完美展现。
在两人投奔陶侃的过程中,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关注,就是当最初陶侃对庾家的态度非常糟糕时,庾亮很是担忧,不知所措。这样的举止,似乎和我们想象中的潇洒淡定完全不同。当然,陶侃是没有看到这一场景,可是在温峤看到庾亮这副模样的时候,难道没有觉得他不够超脱恬然吗?
庾亮的慌乱看起来当然是缺点的表现,关于缺点我们在第五章还会详细论述。但是庾亮的慌乱首先是一种自然的表现,一种不加掩饰的表现。即使是被当时名士认为是圣人的孔子,在得意弟子颜回过世之时,也会悲恸地哭喊说“天丧予”。庾亮自然的慌乱和孔子自然的悲恸,从本质来说是一样的举止,因此温峤并不会以此而看轻庾亮。如果和前文所述裴楷的容貌作一个对比,那么裴楷不戴冠冕头发乱糟糟的模样,是在容貌层面的自然而乱,而庾信的慌乱则是在举止层面的自然而乱。两者在赏识之人看来,都是“乱而好”的。
而对于貌相对不出众的名士来说,也许让他人欣赏到自己的才就比较困难。这使得能“知”才之人更加难得,也显得相对藏于深处的“才”更为珍贵。《容止》篇第32则说有人对谢尚评价不高,桓温慧眼独具地说,大家不要随便下结论,仁祖(谢尚)踮着脚在北窗下弹琵琶的样子,“自有天际真人想”。这则故事的独特之处在于并没有直接的表演者,而是一群观众在谈论表演者,而通过谈论谢尚,观众本身也成了表演者。众所皆知,北窗借代的是“寄傲怀高和闲情逸致”,而琵琶则在《世说新语》所展现的名士圈子中属于相对小众的乐器——琴在《世说新语》中出现的次数明显要多得多,“企脚”(踮着脚)则又表明谢尚有所期待。谢尚自得其乐地在内室弹琵琶,并不刻意地想让别人听到,却又若有所待。这就是魏晋名士所推崇的“有意无意之间”的气度。而颇能识人之才的桓温,在肯定了谢尚之才的同时,也表现出自己高于同座之人的“知”人能力,从而也让后人知道了他自己的“才”。
(本文节选自董铁柱《演而优则士——〈世说新语〉三十六计》,中华书局,2022年1月)
《世说新语》三十六门,门门都写尽如何成就名士的苦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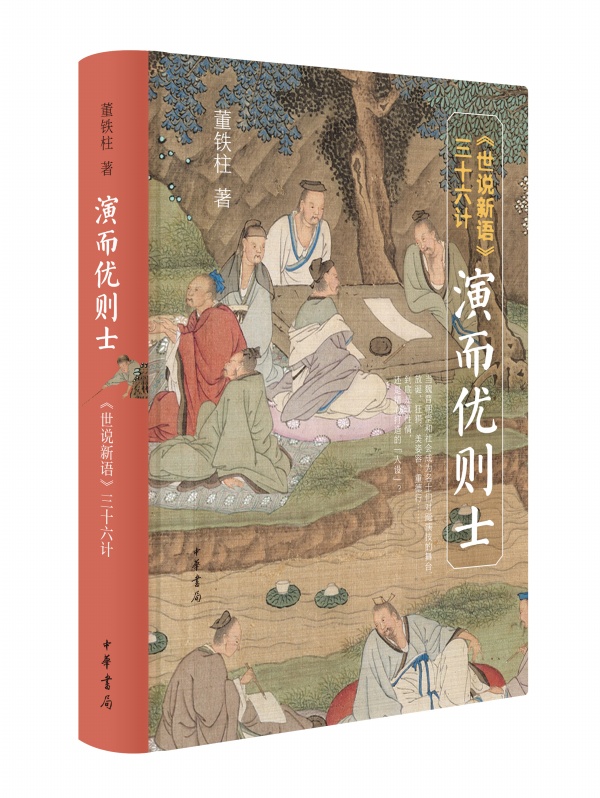
当魏晋朝堂和社会成为名士们对飚演技的舞台,放诞、狂狷、美姿容、重德行……到底是真性情,还是精心打造的“人设”?书中展现给我们的,是另一个维度的魏晋名士群像。
董铁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哲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学,出版有《孔子与朽木——中国古代思想的现代诠释》。


www.zhbc.com.cn zhbc@zhbc.com.cn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邮编: 10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