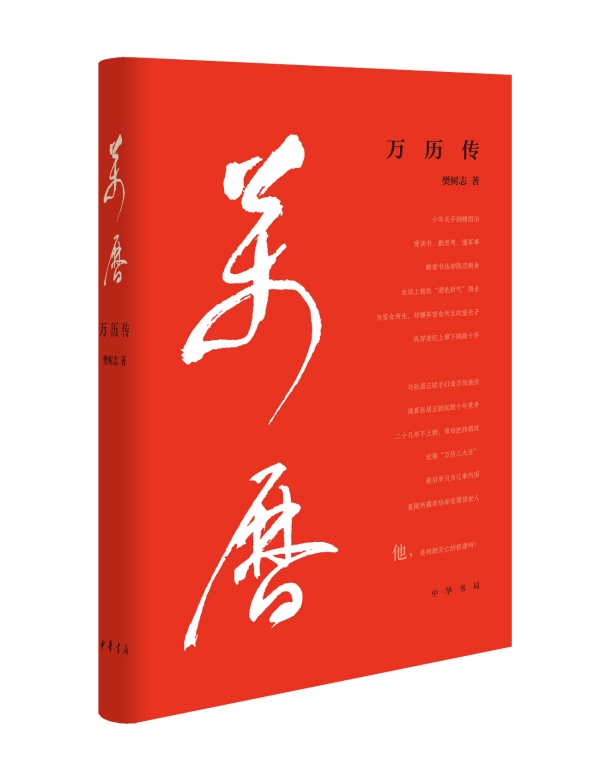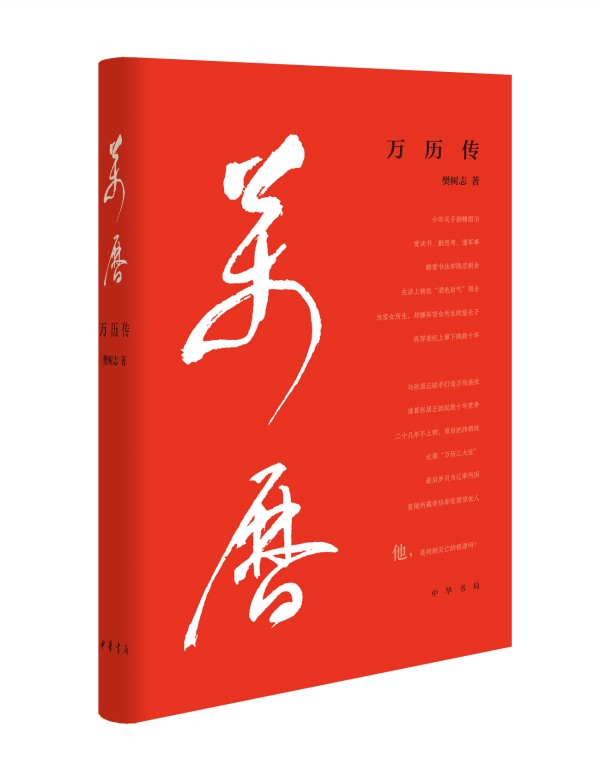
5月4日是一年一度的青年节。犹记得一百多年前新文化运动领袖李大钊先生洋溢着激情的论说:“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作为青年人,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是非常重要的学习途径。 为了配合节日主题,中华书局上海聚珍文化“聚珍12点·午间日读书”于当日展开直播活动。《张居正与万历皇帝》责编董洪波和《万历传》责编吴艳红一道向大家讲述大明首辅张居正的成长历程,体会一代大政治家对于家国兴衰的责任与担当。 一 青年张居正的才志与秉性
张居正的远祖来自安徽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同乡,参加红巾军,追随朱元璋征战四方。后来被授予军职,分配到荆州。所以说,张居正是世袭的军户家庭出身。军户家庭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张居正屡次说自己“家世寒贱”,是符合真实情况的。
他的父亲就曾想通过科举改变命运,但没有成功,甚至连个举人都没有考上。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这一点,和清末大员曾国藩有相似之处。不过,比起曾国藩,张居正的仕途之路要顺利得多,简直可以说是一个神童。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受到了地方官员的赏识。
张居正进士考了两次才考中,即便如此,已经是非常顺利的了,当时他才23岁。他还觉得不满意,在后来给儿子的信中反思道,自己是由于小小年纪考中秀才、举人,以为进士及第很容易,于是放松了对于科考项目的钻研,而关心与“治国平天下”紧密相关的实际事务。在落第后,又回到应试教育的轨道上,才顺利考中,成为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进士。
 (清)梁亯《观榜图》局部
(清)梁亯《观榜图》局部关于张居正的科举,有一个广为流传的佳话,就是说,他13岁考乡试时被主考官故意落榜,因为怕他这么年轻就中举容易骄傲自满,想磨练他的志气。这其实是一种有心栽培的表现。张居正后来在一封书信里曾提到自己少年时受到的礼遇:
仆昔年十三,大司寇东桥寇公(顾璘)时为敝省巡抚,一见即许以国士,呼为小友。每与藩臬诸君言:“此子将相才也。”又解束带以相赠。“子他日不束此,聊以表吕虔意耳。”一日留仆共饭,出其少子,今名峻者,指示之日,“此荆州张秀才也。他年当枢要,汝可往见之,必念其为故人子也。”仆自以童幼,岂敢妄意今日,然心感公之知,思以死报,中心藏之,未尝敢忘。
这里的“吕虔”是有典故的。三国时的吕虔有一把佩刀,工匠观看后,认为佩有此刀的人一定会登上三公之位。吕虔对别驾王祥说:“我不是可以做三公的人,这刀对我说不定还有害。而您有公辅的器量,所以送给您。”王祥坚决推辞,吕虔强迫他才接受。后来王祥官至太保。王祥临终前,又将这把刀送给其弟王览,说:“你的后代一定兴盛,足以配此刀。”果然,王览的后代之中便有东晋政权的奠基人,大将军王敦、丞相王导。琅琊王氏家族从东晋开始贤才济济,成为其后光耀几百年的望族。故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顾璘用这个典故,足以看出对少年张居正的赏识。
此时的张居正真可谓少年得志。进士及第后,按照常规,进士里面的佼佼者可以成为翰林院庶吉士。在当时翰林院可以说是做官的终南捷径。在明朝的政治体制中,翰林院至关重要,内阁大员大多是翰林院出身。进入翰林院,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远大的前程在向他招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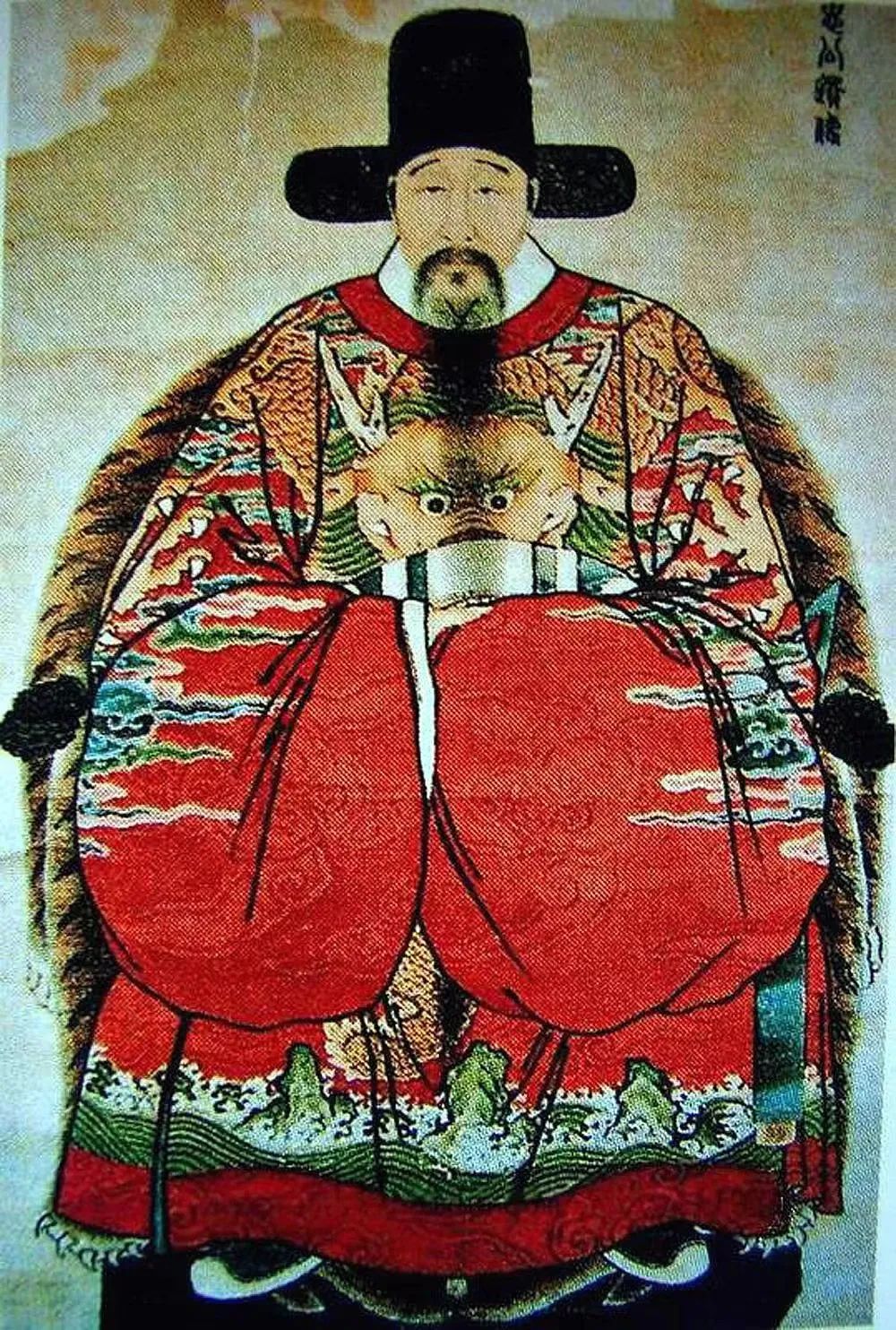
关于张居正在翰林院的表现,与他同科中进士,又同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以后成为著名学者的王世贞,回忆说:
(当时)进士多谈诗、为古文,以西京、开元相砥砺,而居正独夷然不屑也。与人多默默潜求国家典故与政务之要切者。
不过,在一开始的做官之路上,张居正似乎并不顺利,他在翰林院的编修职务上徘徊了十年之久,而这个职务仅仅是编写国史和实录的七品官员。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张居正竟然一度遇挫,想打退堂鼓。
二
张居正进入政坛时的政治形势
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两位皇帝,一位是嘉靖帝,一位是万历帝。明朝的皇帝很有个性特点,嘉靖帝最大的特点就是崇信道教。他把权力委托给内阁大臣,自己则躲在宫里,和一群道士一起修炼。在举行道教仪式时,需要奉献给玉皇大帝的表文,使用红笔写在青藤纸上的,因而又叫青词贺表。当时涌现出一批因善写青词而受宠的臣子。权臣严嵩就是最大的代表,《明史》中就说,写青词的话,除了严嵩,没有能让嘉靖满意的。因而严嵩有“青词宰相”的美名。严嵩之所以能得到嘉靖的信任,专擅朝政二十年,这是其中的一个奥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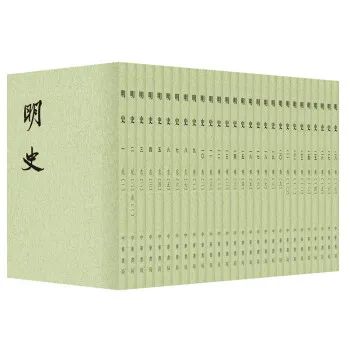
张居正进入政坛时,正是严嵩、严世蕃父子呼风唤雨的时候,形成了一个以严氏父子为中心的巨大权力网络。严氏父子在卖官鬻爵、聚敛财富、排斥异己等方面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有一个说法叫做:“嵩好利,天下皆尚贪;嵩好谀,天下皆尚谄。”可见严嵩的恶劣影响。当时的言官虽然也有许多谏言,但嘉靖帝根本听不进去。
初出茅庐的张居正,想依靠才能获得皇帝的赏识,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在嘉靖二十八年上呈的一封《论时政疏》指出皇帝沉迷于道家,不理朝政,拒绝大臣批评批评,导致政局紊乱,结果完全石沉大海,毫无回音。
另外有一件事也刺激到他,就是先前的内阁首辅夏言受严嵩陷害,而被处死。严嵩平日里对夏言毕恭毕敬,利用嘉靖帝对夏言的不满,说他是收复河套地区的幕后指使人。皇帝对此本来就持消极态度。夏言未能审时度势,加上严嵩的谗言。导致夏言被当众处死。当时不知道张居正有没有现场观刑,但此事对他的冲击非常之大,堂堂内阁首辅竟然被当众处死,且罪名很难支撑。由此他深刻领略到官场权力斗争的险恶。等到严嵩父子权倾天下的时候,更是如此。难怪在张居正后来的回忆中,对于嘉靖朝的政治批评很多。
三
张居正如何一步步获居高位
张居正自己作为晚辈,也没有办法,虽然对严嵩有不满,也不敢表露出来,甚至表面上需要敷衍乃至讨好,比如帮助严嵩起草过一些青词。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严嵩七十大寿时,张居正也写过俗不可耐的贺诗,诸如“声名悬日月”等。但是在实际的政治关系里,张居正无疑是倾向于徐阶的。只不过,在他初步领略到官场的险恶和无奈时,倍感失望,绝意辞官回乡休养一阵。就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张居正以身体欠佳为理由,辞官回乡休养。就这样,张居正居乡6年,直到嘉靖三十八年(1559)才重回朝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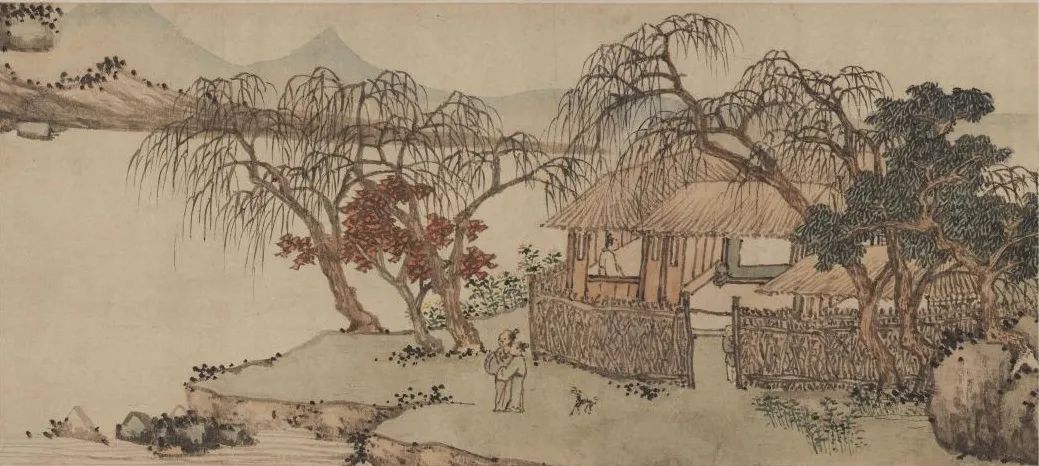
这一举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成是在逃避。但以后见之明,也可以说成是在规避风险,韬光养晦。之所以如此说,乃是因为张居正在家乡表面上过着悠游闲适的生活,但在给朋友的信中却流露出几分真心情。比如屡次言及对于京城政局走向的忧虑,并慨言“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可见他的自我期许和胸怀抱负。他绝对不甘于做一个阿谀奉承的小官。他需要大展身手的平台,更需要超越常规的权力,“大破常格,扫除廓清”。而这种机会,在严氏父子倒台后才有可能浮现。
张居正回到官场后,受到了老师徐阶的关照,被安排到裕王府,担任讲读官。因为按照惯例,皇长子裕王继承大统是早晚的事情。徐阶担任内阁首辅后,颇有一点拨乱反正的意味。在内阁办公室里写了一副条幅:“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也就是说,他并不打算像严嵩那样独揽权力,而是让权力各安其位。在嘉靖帝驾崩后,徐阶拉拢张居正一起起草皇帝遗诏,促成了嘉靖帝、隆庆帝的顺利交接。而张居正也距离权力中枢有了更进一步的距离。
然而,就在嘉靖、隆庆之际,徐阶与另一位耿直的权臣高拱之间的矛盾也愈趋明朗化。高拱是一位能臣干吏,被认为是明朝最有作为的吏部尚书。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进入内阁。高拱性格耿直,与徐阶常有冲突,尤其对徐阶引用门生张居正、瞒过同僚起草遗照耿耿于怀,于是多方面制造“倒徐”的舆论。可结果是朝中之人纷纷赞誉徐阶,弹劾高拱,导致高拱以身体有病为由辞官而去。但是徐阶不久也遭到弹劾,再加上与高拱亲善的隆庆帝本来就对高拱的离去有所不满,于是同意徐阶退休离去。
值得注意的是,张居正在徐阶的栽培之下,一年多的时间里,便由五品的翰林院学士,一跃成为内阁辅臣。尤其在高拱徐阶相继辞官之后,在内阁中逐渐拥有了自己的威望。隆庆二年(1568)曾提出很有分量的《陈六事疏》,提出了六条改革主张,包括“省议论”(少发议论,多干实事)、“振纪纲”(加强法纪、统一号令)、“重诏令”(朝廷要审慎制订政令,一旦制订,便要不折不扣执行)、“核名实”(综核名实)、“固邦本”(巩固国家的根本,照顾人民的利益)、“饬武备”(加强国防建设)。可以说,这六条主张,充分体现了张居正的法治思想。隆庆帝对此似乎表示欣赏,但是内阁掌权者李春芳、陈以勤都是明哲保身、不想大动干戈的人物。张居正对此心知肚明,于是暗中策划鼓动皇帝重新召用高拱,因为高拱毕竟是能干实事的。于是到了隆庆三年(1569),隆庆帝召回辞官两年的高拱。高拱成为内阁中大权在握的人物。

高拱掌权后,两个铁腕人物必然会有冲突。高拱虽然是一个做事的能臣,却喜欢独断专行。他和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之间有着难以调解的矛盾,也看不惯冯保的权力膨胀。不过,他也担心张居正与冯保的结盟。在小皇帝万历即位以后,高拱和张冯的斗法到了更进一步的阶段。就在冯保遭受弹劾,危机四伏的时候,张居正献计,让冯保转告太后高拱曾经说过“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极力凸显高拱的跋扈和对孤儿寡母的蔑视。果然,高手过招,一招毙命,高拱被赶出朝廷了。
这个时候,内阁大权独揽的张居正,以内阁首辅而兼任帝师,在内廷冯保和太后的支持之下,权势逐渐到达了巅峰状态。张居正自己的一句名言“吾非相,乃摄也”,很能说明这种状态。于是,张居正在教导小皇帝的同时,也就有能力推行谋划已久的改革。在此前的直播中,我们讨论过张居正对于小皇帝的教导,以及他推行变法的主要内容。总之,小皇帝虽然对张居正有心悦诚服的一面,但在逐渐长大,尤其是成年后还无法掌握权力,对张居正的敬服便逐渐转变为恨,最终导致了张居正在死后被抄家的局面。
四
张居正是否想过急流勇退
那么在权力巅峰的时候,眼看着小皇帝一天天长大,张居正有没有过急流勇退的念头?当然是有的,尤其在皇帝年满十八岁,独立治理朝政的条件成熟之时。张居正的头脑非常清醒。其实,在位高权重、功勋卓著的巅峰时期急流勇退,是历代政治家推崇的最佳选择。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名句“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表达的就是这种理想。张居正又何尝没有这一念头!在万历八年(1580)张居正呈送《归政乞休》的奏疏,请求退休,把权力归还给皇帝,即所谓“归政”。这篇奏疏情真意切,不妨一阅:
臣一介草茅,行能浅薄,不自意遭际先皇拔之侍从之班,舁(音于)以论思之任。壬申之事,又亲扬末命,以皇上为托。臣受事以来,夙夜兢惧,恒恐付托不效,有累先帝之明。又不自意特荷圣慈眷礼优崇,信任专笃,臣亦遂忘其愚陋,毕智竭力,图报国恩。嫌怨有所弗避,劳瘁有所弗辞,盖九年于兹矣。
这段文字读起来颇有诸葛亮《出师表》的韵味。但张居正讲这些,不是为了“出师”,而是要“急流勇退”。张居正的奏章写出来诸葛亮的味道,实是因为张居正的确对诸葛亮推崇备至。张居正为了推行改革,的确也是不避嫌怨,不辞辛劳。

当然,除了表达对皇帝信任的感激之外,他也意识到“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其实张居正并不是瞻前顾后,谨小慎微的人物,他做事敢作敢为,大刀阔斧。根据樊老师的分析,这种急流勇退的想法在他心里其实早就有所酝酿,直到皇帝成年的这个时机才选择和盘托出。
张居正在给朋友的书信中最能透露这一点。他说“盖骑虎之势自难中下,所以霍光、宇文护终于不免”。霍光、宇文护都是权倾一时的大臣,但霍光死后被满门抄斩,宇文护被处死,他们的结局都不是很好。可见,张居正已经意识到久在高位,可能会不得善终,有一种内在的危机感。
奏疏呈上以后,皇帝却似乎没有准备,毫不犹豫地驳回。两天后,张居正再次乞休,进一步袒露自己的心迹,说自己自从隆庆六年(1572)至今,“惴惴之心无一日不临于渊谷”,也就是没有一天不在胆战心惊。皇帝收到第二份奏疏,有点犹豫,便征询太后的意见。但太后却果断做出决定:“张先生亲受先帝托付,岂忍言去!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
这个决定在某种意义上激化了万历帝与张居正之间的关系。本来如果张居正急流勇退,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结局。欲退而不能的张居,只能继续承受“高处不胜寒”的命运。而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态度,则产生重要转变。张居正死后被抄家的场景非常凄惨,在《张居正与万历皇帝》里有非常细腻的描述。可以说是墙倒众人推,哭诉无门,长子张敬修被迫上吊自杀,写了一份绝命书,供述了张府被抄家的惨状。
五
为什么张居正会说“愿以深心奉尘刹”
任何一个大人物都有思想复杂的一面,张居正也不例外。他早年第一次辞官的时候,其实也曾流露出一点归隐的思想,当然不占主要部分,主要部分仍然是想要等待好的机会来施展抱负,所谓“大破常格,扫除廓清”。而在他掌权的过程中,主要是法家思想指导改革。
“愿以深心奉尘刹”来自张居正的一首诗,全句是:“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据说是他在读《华严经》时有所感悟而写下来的。从表面上,体现出一种高尚的人生境界,也就是无私奉献,毫不利己,专心为民。但是如果把这句话和海瑞对张居正的一个评价对照来看,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收获。海瑞说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拙于谋身”和“不于自身求利益”其实有相通之处。张居正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不畏人言,任劳任怨,尽心尽力,的确有无私的一面。从其结果来看,也的确是“拙于谋身”,没有给自己谋得一个圆满的结局。反而树敌无数,在死后被围攻。所以张居正对于这句诗的确是有所实践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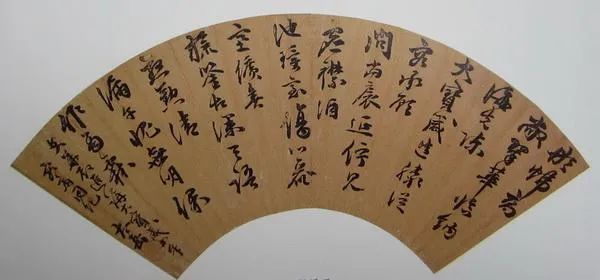
近代大儒熊十力有一篇有名的《与友人论张江陵书》,里面提到:“江陵学术宗本在儒,而深于佛,资于道于法,以成一家之学”,“江陵之学毕竟归本儒家,融会于佛者较深,资于老者少,取于商韩者更少”,认为“自佛法东来,传宣之业莫大于玄奘,而吸受佛氏精神,见诸实用,则江陵为盛”。可见在他看来,张居正有着很深的佛学造诣。所谓的“愿以深心奉尘刹”,即表达了张居正本人对于佛学的契合与投入。
其实如果读过《韩非子》《商君书》,会觉得的确像熊十力先生讲的那样,法家的富强是不惜剥削百姓的。如果注意到张居正在隆庆二年向皇帝呈进《陈六事疏》中的条目,会发觉他非常重视维护百姓的利益。所以会有人说张居正其实本质还是有着儒家的精神。这一点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大家如果对张居正及其主持的改革有兴趣,推荐阅读樊树志先生的《张居正与万历皇帝》《万历帝》《重写晚明史:新政与盛世》三本书。
直播现场精彩花絮




直播间精彩评论



左右滑动解锁更多图片
推荐阅读
《张居正与万历皇帝》
《万历传》
著者:樊树志
书号:978-7-101-14730-8
出版时间:2020年11月
定价:68元
点击上方书影,马上进入京东购读
内容简介
万历帝十岁登极,少年天子励精图治,与张居正联手打造万历盛世。张居正死后,却对其抄家清算,掀起数十年党争。其后二十几年不上朝,被大臣痛批“酒色财气”。运筹“万历三大征”,战果辉煌,最后岁月却为辽东战事所困。在位四十八年,一生分为黑白分明的两段,心灵在成长中蜕变。是什么导致了他的压抑、偏执与报复?他的人性弱点为他的王朝带来了哪些厄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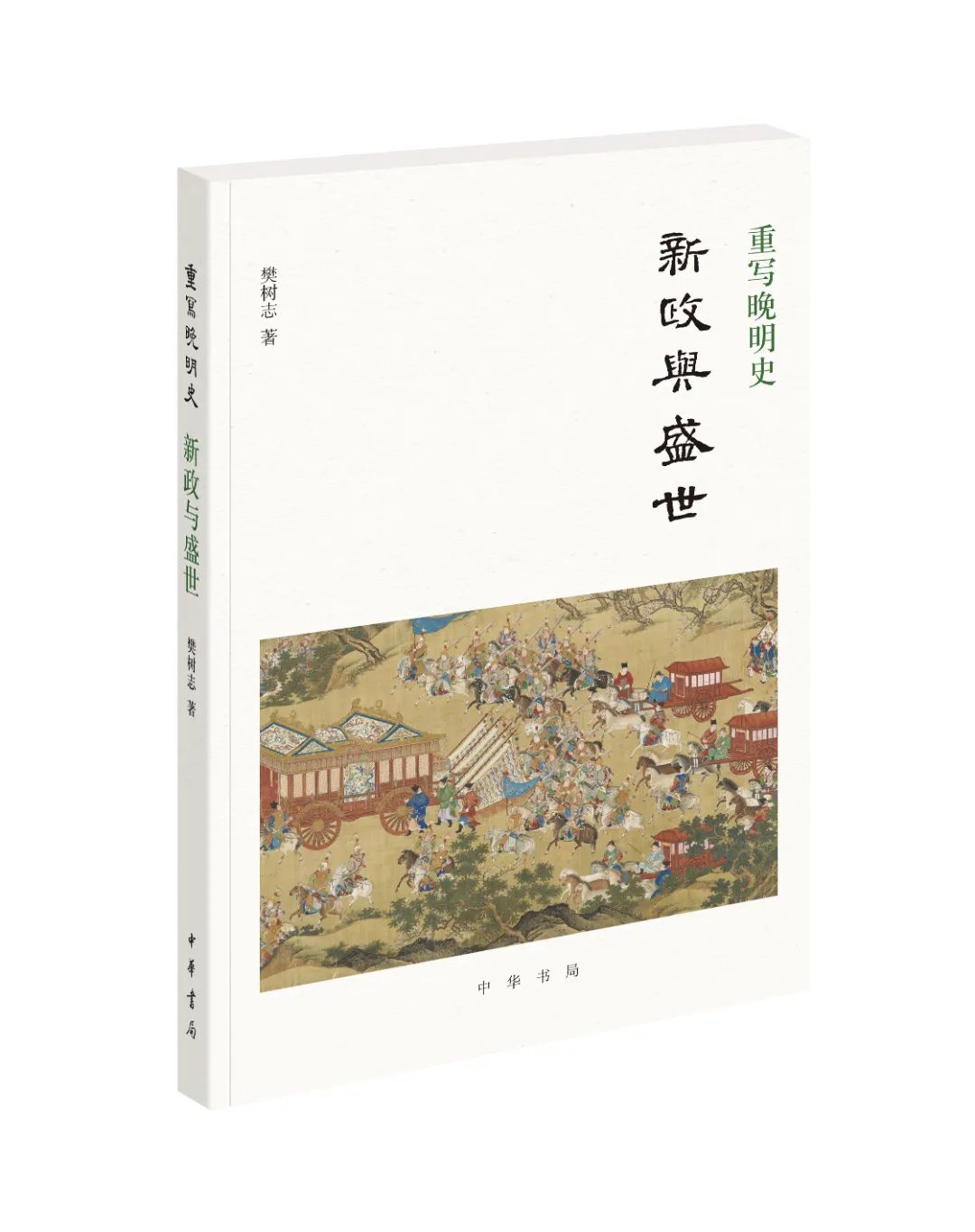
著 者:樊树志
出版时间:2018年8月
定 价:56元
点击上方书影,马上进入京东图书购读
往期精彩
青年张居正如何踏入政坛丨聚珍12点·午间日读书(第13期)活动预告
万历帝:用一生治愈童年丨聚珍12点·午间日读书(第11期)活动预告
上书坊·书展首发 |《重写晚明史:新政与盛世》(文末附活动预告)
喜讯:《重写晚明史:新政与盛世》获《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8年度好书奖


www.zhbc.com.cn zhbc@zhbc.com.cn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邮编: 10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