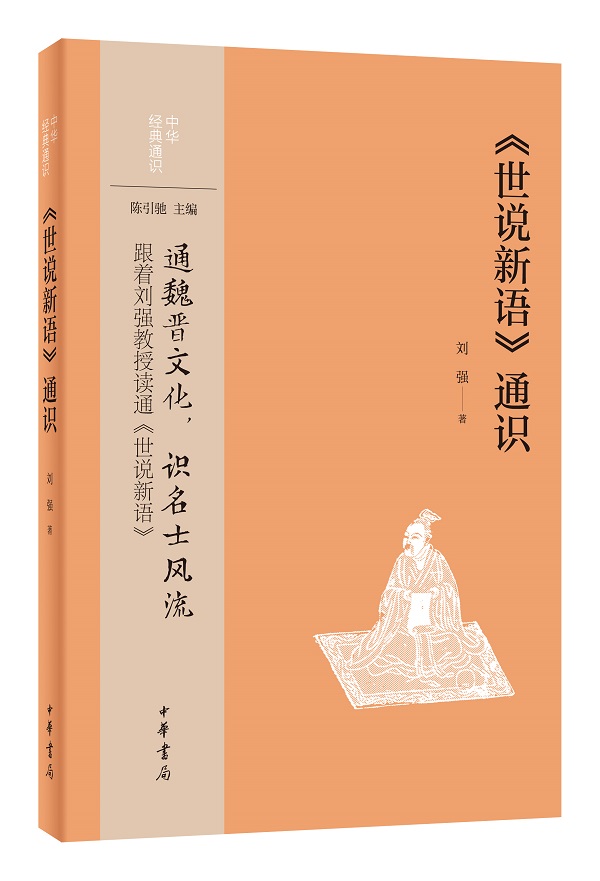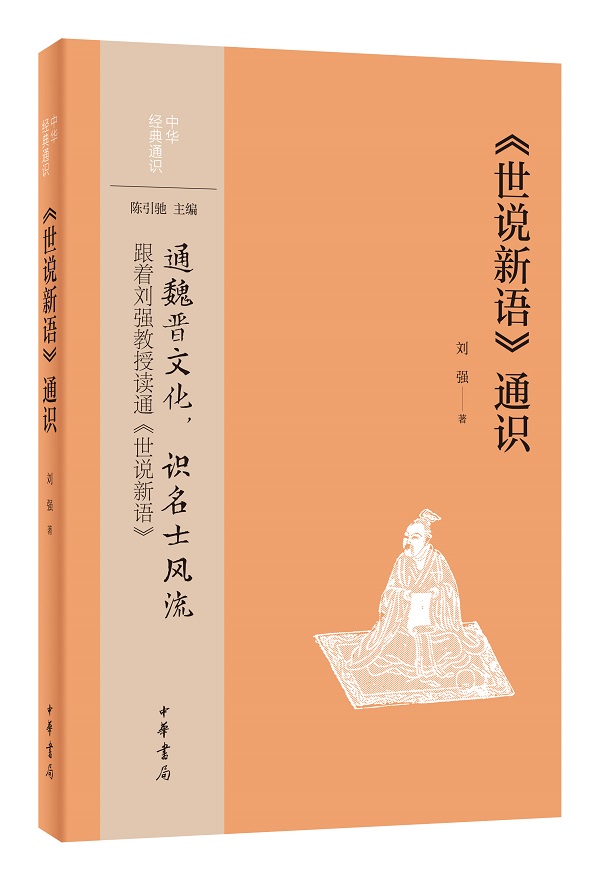
中华书局上海聚珍近两年陆续推出了“中华经典通识”系列经典普及丛书,邀请一流的学者大家撰写,引导大众了解传统经典。春节期间,兹选其中与中学、大学教学相关的几部通识著作中的章节,以飨读者。
因为年代久远,文献不足,关于《世说新语》的成书,留下了一些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谜团,虽然无关宏旨,但就“通识”的要求而言,也应该有所了解。下面我就择要予以说明。
首先,《世说新语》的作者是谁?这本书究竟是一人独撰,还是“成于众手”?
如前所述,《世说新语》的作者,一般认为是南朝宋代的临川王刘义庆。如《世说新语·假谲》“诸葛令女”条,刘孝标注对故事的真实性提出批评时就说:“葛令之清英,江君之茂识,必不背圣人之正典,习蛮夷之秽行。康王之言,所轻多矣。”这里的“康王”,就是刘义庆的谥号。这说明至少在刘孝标眼里,《世说新语》的作者非刘义庆莫属。此后的目录学著作及类书,也都认同此说,一向并无异议。
刘义庆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我们结合史书的记载简要作一介绍。
刘义庆,字季伯,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生于东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卒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444)。他是宋武帝刘裕的侄子,长沙景王刘道怜的次子。刘道怜一共养了六个儿子,而他的幼弟刘道规没有儿子,所以义熙八年(412)刘道规病逝后,便以年仅十岁的刘义庆为嗣子,义庆十三岁时也就袭封了南郡公。刘义庆幼时聪明伶俐,刘裕对他很是喜爱,常说:“此吾家丰城也。”丰城,是传说中龙泉、太阿两宝剑沉埋之地,足见刘裕对刘义庆寄望甚高。永初元年(420)刘裕称帝,追封刘道规为临川王,年仅十八岁的刘义庆作为嗣子得以袭封临川王,征为侍中。
永初三年(422),刘裕病逝,长子刘义符即位,改元景平。景平二年(424),刘义符被徐羡之、谢晦等人所废,不久被杀。紧接着,刘裕的第三子刘义隆(407—453)即位,是为宋文帝。刘义隆登基后,改元元嘉,他在位三十年,励精图治,营造了一个所谓“元嘉之治”。刘义庆作为皇帝的堂兄,颇受重用,历任秘书监、丹阳尹、尚书左仆射、中书令、荆州刺史等职。其间,刘义隆因为猜忌,杀害了不少宗室和功臣,而刘义庆因为性格谦退,为人低调,与世无争,一直受到皇帝的信任。
元嘉八年(431),因太白星(即金星)侵犯了左执法星,时任右仆射的刘义庆害怕会有灾祸,便向皇帝上书,自求外镇。皇帝下诏挽留未果,乃出其为荆州刺史。义庆在任八年,清正廉洁,颇受百姓爱戴。元嘉十六年改授散骑常侍,都督数郡,任江州刺史。元嘉十七年任南兖州刺史。二十一年病故于京城,时年四十二岁。朝廷追赠侍中、司空,谥号为康王。
我们看刘义庆的这份“简历”,觉得他更像是一个政治家,似乎与文学没有多少关系,但是且慢,真正使刘义庆名垂后世的却正是他的文学成就。据《宋书·临川烈武王道规传》记载,刘义庆“在州八年,为西土所安。撰《徐州先贤传》十卷,奏上之。又拟班固《典引》为《典叙》,以述皇代之美”。这里尽管没有提及《世说新语》,但据学者们推测,此书的编撰,应该就是在荆州和江州刺史的任上。
问题是,刘义庆的文学才华究竟如何?他能否独自完成《世说新语》以及其他著作的编撰呢?这个问题近代以来曾引起不小的争议。我们先看史书上怎么说:
(义庆)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谘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太祖与义庆书,常加意斟酌。(《宋书·临川烈武王道规传》)
这段话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刘义庆“爱好文义”,才词虽不多,但文学才华“足为宗室之表”(这个说法连褒带贬,似乎算不上第一流的意思)。其二,刘义庆以藩王之尊,在文坛拥有相当号召力,故其招聚文学之士,无论远近,大家一定前来效力,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当时一流的文人皆先后为其所用。其三,因为其门下文人荟萃,故皇帝刘义隆写信给刘义庆时,“常加意斟酌”,生怕言差语错,贻笑大方—正是这段话,给后人留下了联想和揣测的空间。如《南史·刘义庆传》就在“引为佐吏国臣”后加上一句:
所著《世说》十卷,撰《集林》二百卷,并行于世。
这是史书的传记第一次提到《世说新语》。《南史》是唐朝人李延寿编写的,当时《世说新语》已经成为一部“畅销书”,故不能不引起重视。李延寿似乎认为,《世说新语》和《集林》以及前面所说的《徐州先贤传》《典叙》等书一样,应该是刘义庆和他门下的“佐史国臣”们“集体编撰”的成果。不过,细究起来,“著”和“撰”的含义或有不同,这样的记载也并没有剥夺刘义庆对于《世说新语》的“著作权”。
到了明代,《世说新语》的作者问题进一步凸显。如陆师道在《何氏语林序》中就指出:“抑义庆宗王牧将,幕府多贤,当时如袁淑、陆展、鲍照、何长瑜之徒,皆一时名彦,为之佐吏,虽曰笔削自己,而检寻赞润,夫岂无人?”“笔削自己”自然是肯定刘义庆的著作权,“检寻赞润,夫岂无人”则是说,《世说新语》或许“成于众手”,亦未可知。
一百多年后,清人毛际可在《今世说序》中也说:“予谓临川宗藩贵重,缵润之功,或有借于幕下袁、鲍诸贤。”毛氏大概以为,《世说新语》这样的书,应该是刘义庆以自己贵重的身份地位,召集幕下袁淑、鲍照这些文士编撰而成,义庆本人充其量不过是个“挂名主编”而已。历史上类似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
有了这些铺垫,到了近代,鲁迅才顺理成章地提出了“成于众手”说:
然《世说》文字,间或与裴、郭二家书(引者按:指《语林》《郭子》)所记相同,殆亦犹《幽明录》《宣验记》然,乃纂缉旧文,非由自造。《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
从此以后,《世说新语》“成于众手”,便几乎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了。萧虹、范子烨、宁稼雨等学者先后撰写论文,从各个角度论证此一观点。
不过我倒是认为,说刘义庆的其他著作“成于众手”应无问题,唯独《世说新语》却很有可能是独撰,义庆绝非仅仅是袖手旁观的“挂名主编”或“总编辑”,而是“笔削自己”的“第一作者”。我的理由有三:
首先,编撰《世说新语》这么一部笔记小说,刘义庆远比幕府中其他文士更具“愿心”与“愿力”。据《汉书·艺文志》著录,《世说》的书名源自汉代大学者刘向,尽管刘向的《世说》早已亡佚,但他的另外两部书《说苑》《新序》,体例上却和《世说新语》极为相似。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世说新语》说:
刘向《世说》虽亡,疑其体例亦如《新序》《说苑》,上述春秋,下纪秦汉。义庆即用其体,托始汉初,以与向书相续,故即用向之例,名曰《世说新书》,以别于向之《世说》。
鲜为人知的是,刘义庆与刘向有着绵长深远的血缘纽带(详下),他比任何人都具备编撰《世说》的心理动机,正如他编撰《徐州先贤传》一样,未尝不怀有弘扬家族文化、延续祖先功业的现实抱负。这与吕不韦和淮南王刘安召集门客分别编撰《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其文化背景和创作动机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我倾向于认为,《世说新语》的编撰,刘义庆应该是责无旁贷的倡导者、总策划和亲力亲为的“第一作者”。
其次,《世说新语》不是一般的小说书,而是一部兼综儒、释、道,涵摄文、史、哲的“中古文化的百科全书”,一般的文学之士恐怕并不是其理想作者。从思想倾向上看,刘义庆于儒、道、佛均有涉猎,体现出涵化众家、折中调和的玄学特质,这与《世说新语》的总体思想旨趣颇为契合,几乎可谓相得益彰。
一方面,刘义庆年轻时就怀有儒家济世之志,对儒家思想尤其是孝悌之道最为尊崇,表现在《世说新语》的编撰上,也一目了然。如《世说新语》三十六门以“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居首,《德行》门的四十七条故事中,有十余条都与孝道有关。此外,从《仇隙》门的几条复仇故事也可看出,刘义庆对符合儒家礼义的复仇行为怀有理解之同情。
另一方面,《世说新语》中到处可见清静无为、遗世高蹈、儒道兼综、礼玄双修的玄学趣味,这与贵为藩王的刘义庆一踏上仕途,就遇到血雨腥风的政治权力斗争有关。《宋书》本传称其“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这是颇具政治潜台词的一个细节。作为宗室亲王,又是朝廷宰辅的刘义庆,深感伴君如伴虎、高处不胜寒,为了全身远祸,不得不自求外镇。透过《世说新语·政事》的记载不难看出,刘义庆最为向往儒家的“仁政”与儒、道二家都崇尚的“无为而治”,对严刑峻法、刻薄寡恩的“察察之政”颇为排拒。到了晚年,对现实政治的失望,使他深感“世路艰难”,人生无常,于是其思想渐从儒家转向佛、道。《宋书》本传说他“受任历藩,无浮淫之过,唯晚节奉养沙门,颇致费损”,就是很好的例证。据《高僧传》记载,刘义庆曾与多位僧人有过密切交往,所以在《世说新语》中,以名僧为主的故事就有八十余条。以上这些思想资源,恰恰是袁淑、陆展、鲍照、何长瑜等文学之士所不具备的。
最后,即使从文学才华的角度看,刘义庆也比他幕府中的文学之士更具备编撰《世说新语》的可能性。要知道,《世说新语》并非原创性作品,其性质不过是“小说家言”,是“纂缉旧文,非由自造”(上引鲁迅语)的一部志人小说集。编撰这么一部书,所需要的未必是编者的诗文天才,而是对时代思潮的敏感性,对历史材料的熟悉度,以及对编撰体例特别是分类思想的总体调控能力—这些条件,袁淑、鲍照等人未必具备,而刘义庆却是无一不有。总之,《世说新语》的编撰需要的不是文采斐然的诗人和作家,而是一个拥有史识、学养和文献整理能力的学者和编辑。刘义庆虽然文学才华稍逊一筹,但论及思想的复杂、经历的丰富、识见的深刻、学养的广博,实在比幕府中袁、何、陆、鲍诸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要说《世说新语》“成于众手”,也并非全无道理,但这个“众手”,恐怕不是来自刘义庆同时代的那些“文学之士”,而是包括纷繁错综的魏晋史籍材料的众多作者—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所以,尽管《世说新语》“成于众手”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假说,但在找到确凿的证据前,刘义庆“第一作者”的身份,还是不容抹煞的。

《世说新语》中的魏晋风度和名士风流常常令后人神往不已,人们也常常津津乐道于名士们的故事。这本关于《世说新语》的“通识”,不止讲这些趣味盎然流传千载的故事,更通过对《世说新语》一书来龙去脉的爬梳,讲作者编纂故事和设置门类的巧思;不止讲魏晋风度,更进一步揭示《世说新语》所隐含的魏晋时代精神和重大议题;不止讲名士风流,更描绘了一幅魏晋名士的全景图卷。从而引领读者真正进入《世说新语》的世界,构建阅读《世说新语》的知识骨架,亲身融入鲜活的魏晋文化,捕捉名士们早已逝去的流风遗韵。


www.zhbc.com.cn zhbc@zhbc.com.cn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邮编: 10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