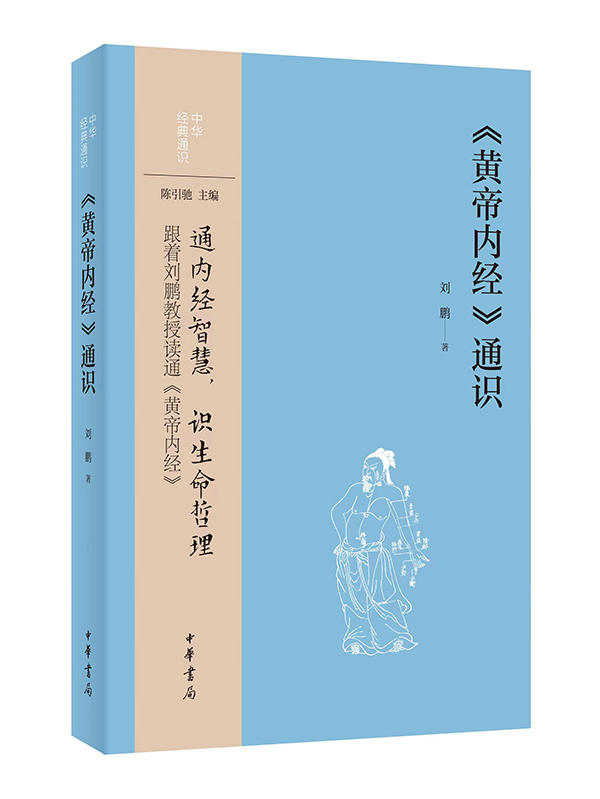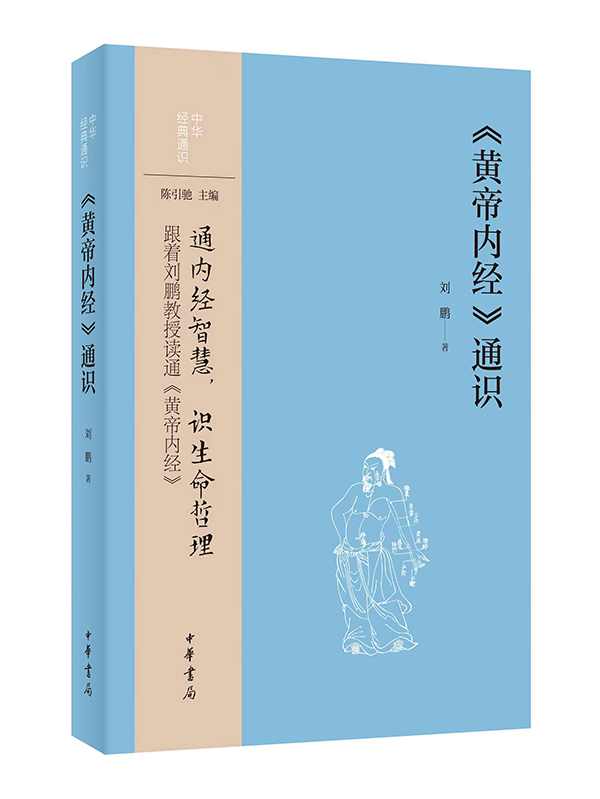
是否知晓《黄帝内经》成为文人笔下区别良医与庸医、精英医者与普通医者的重要标志。《汉书·艺文志》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小说虽多杜撰,却是了解市井社会芸芸众生的重要窗口。略举清代小说几例以为说明。
《聊斋志异》中的邵九娘医术不一般。妒妇金氏病后,“数日腹胀如鼓”,邵九娘起初“以医理自陈”,但金氏顾忌自己曾残虐对待过邵九娘,会遭她报复,所以推辞了。延请数医诊治,皆误作“气蛊”,即气机郁滞所导致的腹胀,服药毫无效果。邵九娘将金氏所服之药悄悄更换,“药下,食顷三遗,病若失”。而后,金氏又患心病,“痛起则面目皆青,但欲觅死”,也是经邵九娘针刺而愈,“按穴刺之,画然痛止”。邵九娘并非医生,为何医术了得?蒲松龄的铺垫和设计便是:“邵贫士,止此女,少聪慧,教之读,过目能了。尤喜读《内经》及冰鉴书。”
与真读《黄帝内经》的邵九娘不同,《金瓶梅词话》第六十一回《韩道国筵请西门庆 李瓶儿苦痛宴重阳》中的赵太医则是妄称饱读《黄帝内经》等医书的真庸医。赵太医本是“东门外有名的赵捣鬼,专一在街上卖杖摇铃,哄过往之人”,他自我吹嘘说:
平生以医为业,家祖现为太医院院判,家父现充汝府良医。祖传三辈,习学医术。每日攻习王叔和、东垣、勿听子、《药性赋》《黄帝素问》《难经》《活人书》《丹溪纂要》《丹溪心法》《洁古老脉诀》《加减十三方》《千金奇效良方》《寿域神方》《海上方》,无书不读,无书不看。
《黄帝素问》被杂列于毫无章法堆砌的医家医书之中,与之同样被拿来充门面的还有伪造的世医身份。反过来看,这也说明时人眼中好的医者应该既有世代为医的经验积累和传承,也要有饱读医书的理论水平。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看南宋陈自明(约1190—1270,字良父,今江西抚州人)《妇人大全良方》自序中所言:“仆三世学医,家藏医书数千卷。既又遍行东南,所至必尽索方书以观。暇时闭关净室,翻阅涵泳,究极天人,采摭诸家之善,附以家传经验方,萃而成编。”算是高水平的炫耀了。
不止于简单列出《黄帝内经》之名,《红楼梦》则直接引述《黄帝内经》的相关理论,写得详细,水平也高。《红楼梦》第八十三回《省宫闱贾元妃染恙 闹闺阃薛宝钗吞声》王太医诊治林黛玉,脉诊、病机分析和治疗方案为:
六脉弦迟,素由积郁。左寸无力,心气已衰。关脉独洪,肝邪偏旺。木气不能疏达,势必上侵脾土,饮食无味,甚至胜所不胜,肺金定受其殃。气不流精,凝而为痰;血随气涌,自然咳吐。理宜疏肝保肺,涵养心脾。虽有补剂,未可骤施。姑拟黑逍遥以开其先,复用归肺固金以继其后。
黑逍遥,即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逍遥散的基础上,加生地或熟地而成。王太医认为黛玉此次发病的主要原因是肝气偏旺,进而影响脾、肺,所以首先要疏肝以治急,然后方能缓补肺、脾,正所谓“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张景岳《类经》)。
因为黑逍遥中的疏肝药柴胡具有升提之性,所以贾琏看了王太医所开处方后,有所质疑,认为其不适宜黛玉的吐血之症,便问:“血势上冲,柴胡使得么?”王太医解释:
二爷但知柴胡是升提之品,为吐衄所忌,岂知用鳖血拌炒,非柴胡不足宣少阳甲胆之气,以鳖血制之,使其不致升提,且能培养肝阴,制遏邪火。所以《内经》说:“通因通用,塞因塞用。”柴胡用鳖血拌炒,正是“假周勃以安刘”的法子。
“通因通用”,语出《素问·至真要大论篇第七十四》:“帝曰:反治何谓?岐伯曰:热因热用,寒因寒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中医治法有正治与反治之别,正治适用于疾病的外在症状表现属性与内在本质相符的情况,例如,热盛于内,在外表现出一派发热、口渴、汗出等热象的症状,就可以选择寒凉药治疗,即治热以寒。反治,则是疾病的外在症状表现是有别于内在本质的“假象”时,如同样是热盛于内,也可表现为怕冷、四肢发凉等“寒”性假象,治疗便不能依从假象而寒者热治,而应从疾病本质入手用寒凉药,即寒因寒用。王太医引用《黄帝内经》“通因通用”,其意为林黛玉吐血的症状根本原因在于木气积郁不能疏达,就肝气积郁闭塞于内而言,血液妄行而上溢于外,是表现为“通”的假象,用柴胡这样疏通肝气之药,是以通性之药治疗“通”的假象,即通因通用。但是,柴胡疏肝的同时又有升提之性,需要避忌,以免加重吐血,鳖血拌炒便能制约其升提之性。柴胡用鳖血拌炒,并非是小说家的杜撰,清代医家不乏应用。(可参阅拙文《鳖血柴胡背后的用药地域化与医家争论》,《中药材》2020年第11期)。假周勃以安刘,典出《史记·高祖本纪》,汉高祖刘邦曰:“安刘氏者必勃也。”以周勃安刘,喻指以鳖血安柴胡。
《金瓶梅》《红楼梦》等明清世情小说中大量中医内容的出现,正说明了文人知医在明清社会的普遍,这与宋元以来士人逐步走向民间所引致的社会转型密切相关。一物不知,实以为耻,医书作为经、史、子、集四部中子部之一,也被文人列入应读之列。文人知医、业医,医者读书通文,皆已在当时社会成为进阶儒医、良医的关键途径,《黄帝内经》等中医经典的影响自然也越来越大。
近现代中国社会依然如此。20世纪80年代《山东中医学院学报》曾设专栏,邀请全国名老中医撰文回忆学医成才之路,这些文章之后被结集成《名老中医之路》,由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影响很大。据颜纯淳等统计,《名老中医之路》涉及的97位名老中医,有91位明确述及《内经》相关内容(《名老中医研习〈内经〉之路探析》,《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稍稍翻阅近现代中医的个人著述,便不难发现,从基础理论到临证各科,由“《内经》曰”以发皇古义,汇通西医以融会新知,是最为常见的书写模式。《黄帝内经》对于近现代中医的影响,由此可窥一斑。
可以说,汉代至今,两千余年,星斗屡易,时空变幻,《黄帝内经》对于医家的意义和价值,却未曾变易。
(选自刘鹏著《〈黄帝内经〉通识》第三章《〈黄帝内经〉的流传、整理与影响》,中华书局2024年5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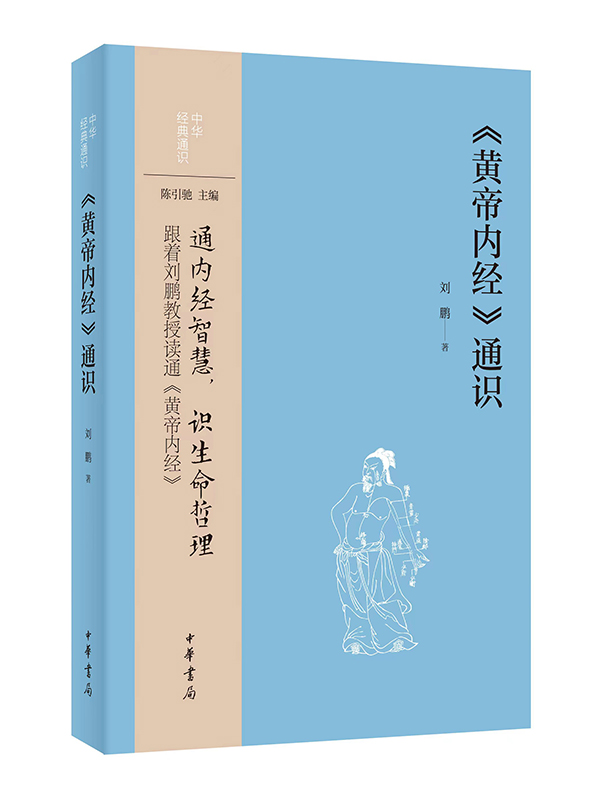
《黄帝内经》被视为“医家之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它不仅是中医学专业的必修书,也是其他领域了解、认识中医的一个窗口。可《黄帝内经》究竟是怎样一部书,又是如何成为中医“经典之经典”的呢?
本书涉及《黄帝内经》的成书、主要内容、版本流传与影响,以及其与现代中医的关系等方面,在导言部分,先摆出“四问”直击《黄帝内经》的“灵魂”,后于正文中再逐步深入解析原典。作者提炼了《黄帝内经》中一些容易引起共鸣的、与传统文化关联密切的内容,如中医有解剖吗、什么是经络、如何尽终天年等,还将艰深的中医理论与古代小说、诗歌、出土医药文献与文物,甚至是日常生活体验相互印证,行文简明、流畅,令人深刻感受到中医对于生命的独特理解和其中蕴含的传统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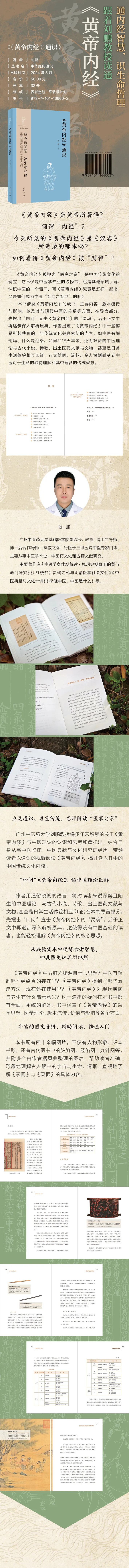

www.zhbc.com.cn zhbc@zhbc.com.cn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邮编: 10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