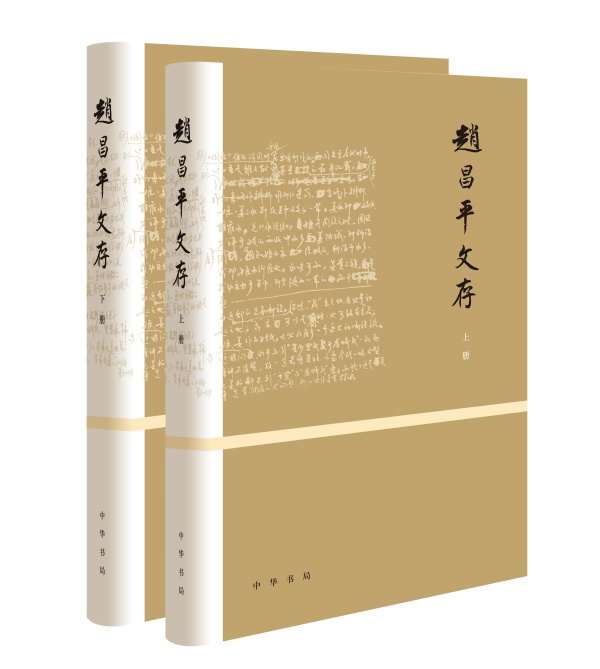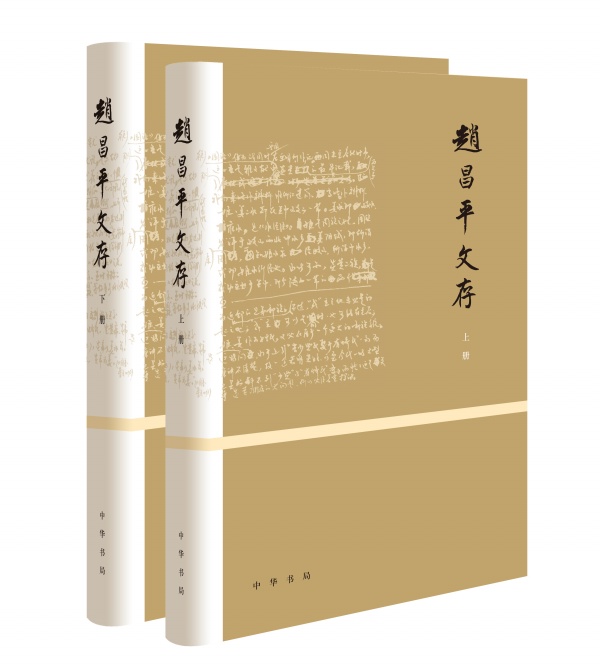
作为一位有丰硕成果的唐诗学杰出学者,更是一位有众多建树的出版人,三年前的5月20日,赵昌平的遽然离世令出版界、学界震惊哀痛。日前,纪念赵昌平逝世三周年追思会暨《赵昌平文存》出版座谈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赵昌平生前的20多位学界、出版界好友及亲属到场,回忆与他交往的点滴,追念赵昌平的学术人生。

赵昌平,1945年10月20日生,浙江上虞人。1963年,赵昌平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后在内蒙古开鲁县、安徽来安县教育部门工作。1979年考取华东师大中文系唐代文学研究生,1982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10月分配至上海古籍出版社,历任编辑、编辑室副主任、主任。1992年任上海古籍出版社副总编辑,破格晋升编审职称。1996年起获国务院杰出贡献专家津贴,出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
赵昌平是一位公认的有思想、有实践、有业绩的出版人。从事编辑出版工作33年,他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发展、为扩大上海出版在全国的影响力,为我国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赵昌平进入总编岗位时,正遇古籍出版业的行业低迷。他正确分析了古籍专业出版题材无再生性的弱势与读者源生生不绝的优势,敏锐地预判到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必将迎来传统文化与古籍出版的复兴。于是提出“市场意识、专业意识、品牌意识、规模意识”的十六字战略,以“适应读者,引导读者”为旨归,以“传统题材、现代表述”为实施要点。短短数年,即较为成功地完成了上海古籍出版社选题结构的转型及四个均衡:学术、普及均衡,文史哲均衡,古代、近现代均衡,大中小项目均衡,从而使古籍出版在走向市场的大潮中,严格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防止了非专业化的趋向。上海古籍出版社多项出版物获得全国古籍图书奖、中国图书奖,销售码洋稳步增长,形成了持续发展的态势。

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说,作为一位从事古籍出版的专业出版人,赵昌平的出版理念和实践无疑聚焦于“找准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的契合点”,做到古今相通、中西相容,即做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而致力于策划出版高品位、系列化、精品化的普及读物是做好传承与传播的有效途径。这一理念,随着他思考的深入和实践的积累,日益清晰和丰富。近二十多年来,赵昌平的出版理念和实践不仅影响着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出版,其影响还波及上海出版界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界。
出版人,是赵昌平的职业身份,也是其倾注心血最多的事业。赵昌平同时还是唐诗与中国诗学的知名专家,而于文、史、哲兼长,著有《唐诗三百首全解》《孟子:匡世的真言》《赵昌平自选集》等专著及论著400余万字。作为上海市、区政协委员和两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关注国家文化建设和出版业的发展,积极参政议政法发表真知卓见,他呼吁《盛宣怀档案》《上海近代文献》专项出版,均被采纳列入上海市文化发展规划。退休后,他还为上海的文化传播工程“中华创世神话”完成了40万字的学术文本。

此次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赵昌平文存》分上、下两卷,由近百篇文章组成,分为10个专题,包括中古诗学、唐诗史论、李白研究、诗人考论、治学门径、书序书评、神话研究、出版专题、杂谈及其他、怀人忆旧。其中“出版专题”是对古籍整理和出版业相关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怀人忆旧”是深情怀念师友、回忆母校等的散文,其他七个专题则展示了他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诗学等方面的文章和卓识。
座谈会上,中华书局执行董事徐俊谈起了在赵昌平生前就已有的文集出版之约。“他慨允将论文集交给中华,每次见面我都重申此约,但他总是说忙过这一阵就着手再编。”徐俊翻出了2017年2月间赵昌平发来的一条短信,其间写道:“我一年来忙于开天辟地学术文本,写了近40万字,估计旬内可成,再忙文集事。”赵昌平去世后,在其家人的协助下,由海南大学海滨教授承担文存的编目整理工作,中华书局的同事们共同努力,高效率、高质量完成了文存的搜集和编校,按原计划在赵昌平去世三周年之际出版。
徐俊感慨:“我相信,文存的出版不仅是我个人的一己之私愿,也不仅仅是我们这些生前友好的私愿,这是一个杰出出版人的学术人生的结晶,是一个为人作嫁者的美丽衣裳,属于中国的出版界,也属于中国的学术界。”
作为赵昌平大学期间的同学、好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葛晓音说,看到《赵昌平文存》出版的心情,可用“悲欣交集”形容。文存是对赵昌平一生学术成就的总结,很多研究方法对学界依然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比如,文存中关于追溯李白思想和创作源头的一系列论文,颇具开拓价值。在葛晓音看来,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多样,但能够全面掌握的学者并不多。赵昌平则既能做作家年谱考证以及别集注释等文献整理工作,又能对作家的思想性格作深入精辟的分析。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发表了一批唐诗研究的代表性文章。
“昌平兄的主要精力都用在出版工作上,自己的学术研究则依靠下班回家以后到半夜这段时间。这种工作习惯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加上抽烟太多,很早就患有冠心病。尽管如此,他一直没有放松学术研究,无论是对于自己的方向还是古典文学研究的趋势,都有很深入的思考。”葛晓音说,赵昌平主张宏观和微观研究的汇通,力求从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探寻文学现象更深层的内涵,一点点地从中抽绎出诗史演进的轨迹。他又特别重视对诗歌的感悟力,强调文学的内在规律研究,形成自己的研究个性。而他最独到的思考则是将文学史研究中的体悟和古典文论中的理念结合起来,形成自己对古典文学研究本质的理论认识。尤其是关于《文赋》《文心雕龙》《诗式》理论体系的思考。他不但贯通了《文心雕龙》各章理论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而且还将刘勰的理论体系活用到当前的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建构之中。他本人也运用这种思考,从更高的理论层面上来认识唐诗,提出过贯通“意兴、意脉、意象”的观点。

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陈尚君回忆,早在1990年11月,在参加南京大学主办的唐代文学研讨会期间,江苏古籍出版社两位主事者就约请赵昌平撰写分体断代文学史系列著作中的《唐诗史》一书,当时听其对《唐诗史》写作的设想作了比较详尽的叙述。赵昌平不赞成以时序叙述唐诗发展过程的框架,更不赞成写成作家作品论,也不赞同写成文学社会史,他坚定地认为唐诗发展有它的内在逻辑,个人命运、社会变动及作者取径虽有各自的不同,决定因素是诗歌本身的生命力。他特别强调体式、气韵、意象、意脉等诗歌内在因素所能展示的唐诗发展史。在赵昌平公开发表的文章中,1990年悼念马茂元先生文、2016年悼念傅璇琮先生文,都说到要完成此书,以不负二位前辈的嘱托,偶也说到已经成文若干万字,但在公私困扰下,最终没有完成这部学界期盼甚殷的著作。
陈尚君表示,赵昌平的唐诗研究成就及其唐诗史写作构想,是他留给当代学术的最宝贵财富。尽管他构想中的《唐诗史》没有完成,此次收入《赵昌平文存》中的系列论文,事实上已经具备了唐诗史的基本框架,而赵昌平自著及协助马茂元先生完成的多种唐诗选本,也具备此一方面的意义。
上海作家协会主席王安忆用“提灯照路”来形容赵昌平。在其写作《天香》的整个过程里,赵昌平是那个一路为作家把关的人。“写完《天香》,我让他给我通读,请他来替我看看,提提一些硬伤什么的。”王安忆说,赵昌平还提醒了很多关于文理的问题,提醒了一个说话的方式。
复旦大学教授骆玉明说到赵昌平在生命后期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即对中华创世神话的梳理,为此耗费很大精力,以致病倒。这项工作希望建立中华神话的一个系统,以此追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流,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问题。赵昌平认为,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一个精神系统建立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反映在早期神话里面。然而中国神话没有一个完整的著作,所有的材料都是松散的、零碎的,并且互相矛盾地存在于各种典籍之中。他希望通过细致的考索,找出神话内在演变的轨迹,并在一个系统里面去解说中华民族的精神,去阐述中华文明的建立这样一个自我体认的过程。

“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到父亲工作的专业领域。”赵昌平之子赵晔炯说,记忆中的父亲,坦诚热情,从不揣度他人心思,待人常以欢喜之心。为人做事公平公正、慷慨大方,考虑他人多过考虑自己,有利益冲突时宁愿自己吃亏也会成全别人。《赵昌平文存》是对父亲整个学术生涯里研究和创作的一次系统性梳理。对于家属和挚友来说,该书的出版带来更多的是心灵慰藉,和对于逝去亲人的缅怀与纪念。
本次活动由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上海市出版协会、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主办。
(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 颜维琦)

www.zhbc.com.cn zhbc@zhbc.com.cn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邮编: 10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