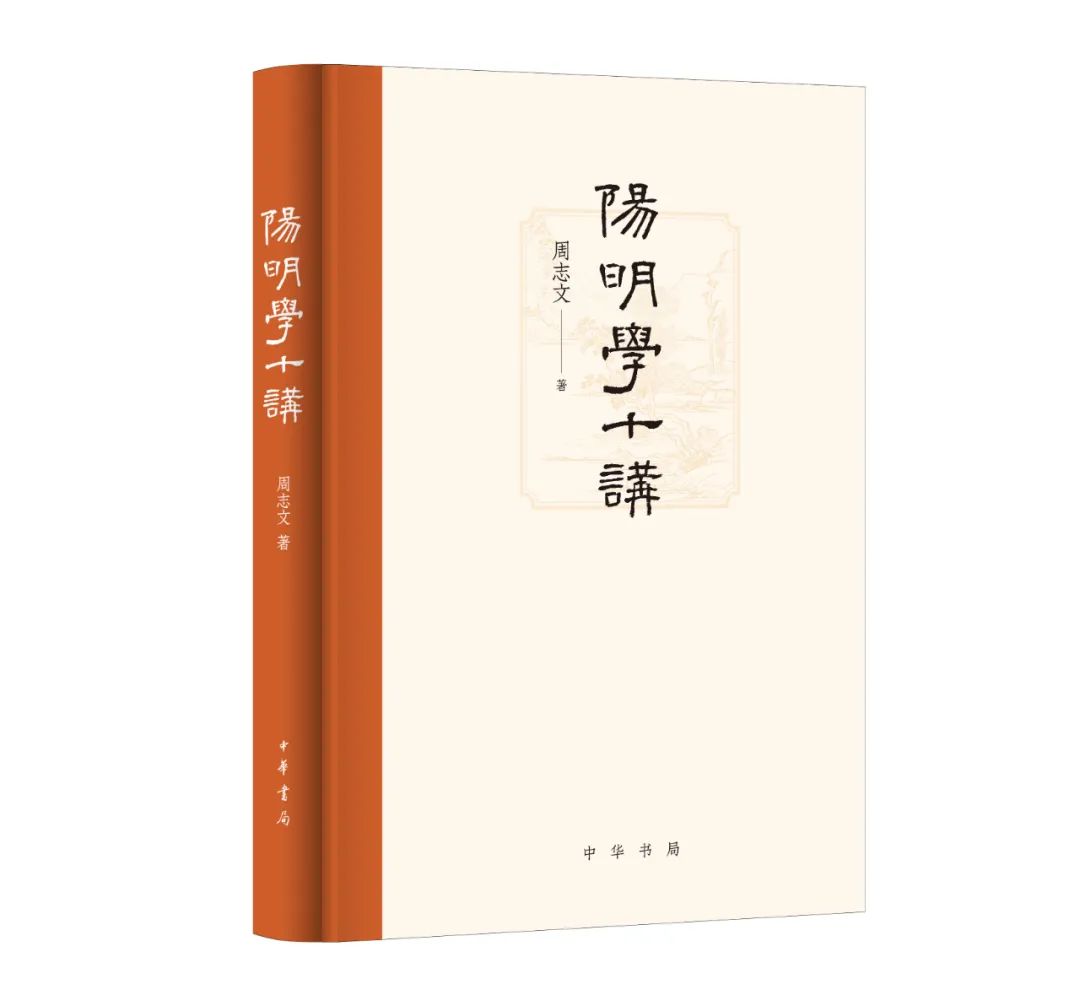-
 中华文化教师素养读本
作者:楼宇烈,傅首清主编
定价:¥58.00
中华文化教师素养读本
作者:楼宇烈,傅首清主编
定价:¥58.00
-
 辽史--全五册(精)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
作者:脱脱著 刘浦江整理
定价:¥280.00
辽史--全五册(精)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
作者:脱脱著 刘浦江整理
定价:¥280.00
-
 南明史(精装本)
作者:钱海岳撰
定价:¥980.00
南明史(精装本)
作者:钱海岳撰
定价:¥980.00
-
 宋书(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平装本)
作者:(梁)沈约 撰
定价:¥360.00
宋书(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平装本)
作者:(梁)沈约 撰
定价:¥360.00
-
 魏书—(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精装)
作者:魏收著 何德章,冻国栋修订
定价:¥510.00
魏书—(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精装)
作者:魏收著 何德章,冻国栋修订
定价:¥510.00
-
 史记--全五册(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精
作者:[汉]司马迁撰 陈曦、王珏、王晓东、周旻译
定价:¥298.00
史记--全五册(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精
作者:[汉]司马迁撰 陈曦、王珏、王晓东、周旻译
定价:¥298.00
-
 全元词(全三册)--中国古典文学总集
作者:杨镰主编
定价:¥298.00
全元词(全三册)--中国古典文学总集
作者:杨镰主编
定价:¥298.00
-
 金史(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精)
作者:[元]脱脱等撰
定价:¥540.00
金史(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精)
作者:[元]脱脱等撰
定价:¥540.00
-
 明实录 附校勘记(183册)布面精装
作者: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 黄彰健校勘
定价:¥45000.00
明实录 附校勘记(183册)布面精装
作者: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 黄彰健校勘
定价:¥45000.00
-
邹鲁文化研究 作者:贾庆超等 定价:¥0.00
阳明学指心学,儒家的一个学派,北宋程颢开其端,至王阳明始大,因其学理平实、易学易用,特别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为抵抗幕府政治,“维新派”假借其说,为自身合法性建立依据,遂使国人误会,以为阳明学可直通现代性。至今民间俗儒,多以王阳明为尺度,其实本末倒置、舛错无穷,专业学者虽正本清源,但相关著述难为普通人理解,致“学术界的阳明学”与“民间的阳明学”断裂。 从孔子讲起 经的流变 儒学史上的问题 (本文摘编自周志文著《阳明学十讲》) 阅读王阳明的非凡人生经历,体悟阳明学的知行合一之道 点击上方书影,马上进入京东购读 基本信息 上架建议 哲学 大众读物 编辑推荐 1. 学者、作家周志文研究阳明人生与学术的力作。作者有感于市面上有关阳明及阳明学的著作要么学术气息太浓重,要么偏重阳明的事功,将之近乎神话了,而较少谈其在思想上的启发与贡献,遂秉承“有一分证据才能说一分话”的写作态度,“就想写点儿别人没写的东西”,将一个好奇、倔强、勇敢、睿智的阳明渐次展现在读者面前,他的思想在当时及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亦被一一揭示。 2. 这是一部能够激活思想、引发深思,带领读者全面了解王阳明的大众读物。作者的散文功底极好,自然朴实又极富真情。这一风格在本书中亦能得到明证。整部书语言浅近,平白如话,像是一位和蔼的长者在对你娓娓而谈,谈阳明的非凡人生,谈阳明的学术,谈阳明的军功建设,谈阳明的后学分派,等等。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阳明,毫无压力地读懂阳明及阳明学。 3. 多面复合型人才——王阳明;能引领大众接地气——阳明学。阳明自小不受绳墨约束,喜欢兵法韬略,有经略四方之志,日后平南、赣乱事,平宸濠之变,平思、田变乱,一介文臣,竟然三次救国家于危难。中进士,做官,虽不显倒也平淡,但因辩戴铣案而被廷杖,随后被贬贵州龙场,于是就有了格竹子、龙场悟道。阳明学的核心是“致良知”“知行合一”,因为其化烦琐为简约,倡导与人讲学“须做得个愚夫愚妇”,和光同尘地用他们的思考方式、语言习惯讲解,才能真正引领他们;又强调为学求诸内心,无须他借,当下实行,直截便利。这使得阳明学在民间掀起了极大的波澜,产生的影响远盛于官方学术。 4. 学者杨渡撰写序言,力荐本书。他说:“这一本《阳明学十讲》,便是他(周志文)研究王阳明毕生功力的结晶。学养深厚自不待言,智慧的观察与分析,亦时时浮现。读者会从他的叙述中,感受到王阳明那既倔强又勤思好学、既智慧又幽默、既平实又充满理想主义的人格魅力。” 内容简介 “阳明整个人在中国传统社会是个‘异类’”,自小不受绳墨约束,不喜“儒家四平八稳的那套”,喜兵法韬略,有经略四方之志,后又对道教、佛教感兴趣。然真正“折节”做起正统儒家学问来,冲突、波折不断,困顿、挫折接连,好奇和怀疑促使他不断思考,最终构筑起以“致良知”“知行合一”为核心的阳明学。 《阳明学十讲》是著名学者周志文先生基于讲稿整理而成的新作。作者有着深厚的学养,秉持“有一分证据才能说一分话”的态度,通过对阳明学之前儒学历史的溯源、阳明学出现的背景分析、阳明人生与学术的精到论述、王门后学的发展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使读者能够在平易而有力的话语中,深切感受到王阳明“不世出之天姿”,“冠绝当代,卓立千古”的道德、功业与文章。 作者简介 目 录
《阳明学十讲》是台湾著名学者周志文先生讲座的辑稿,深入浅出,独具新见,言儒却能超越俗儒,力主“有一分证据才能说一分话”,令人茅塞顿开,堪称当下少有能深入浅出、立论持重的佳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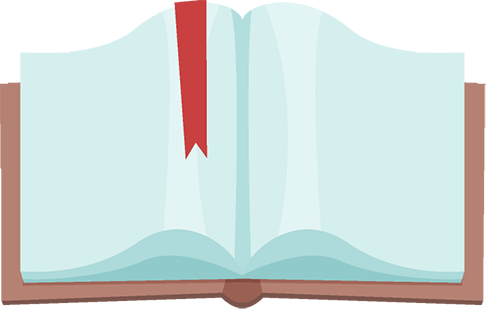
本讲不是谈黄宗羲的,我们得回归谈阳明学术的主线上。
谈起阳明必须先从黄宗羲的著作谈起,而谈起黄宗羲,又必须从黄的老师谈起。
黄宗羲的老师刘宗周(字启东,号念台,学者称蕺山先生,1578—1645),是浙江山阴人。山阴就是今天的绍兴,春秋时叫作会稽,是当时越国的首都。这地方出了许多历史名人,晋代的书法家王羲之(303—361)自少年便迁居到此处,有名的《兰亭集序》就写于此,兰亭就在绍兴。王阳明虽是余姚人,但少年时就随父亲王华迁居山阴,以后在此长住,在此讲学,所以山阴也算阳明的故乡,余姚反而很少回去。山阴、余姚两地其实不远,阳明死后也葬在山阴。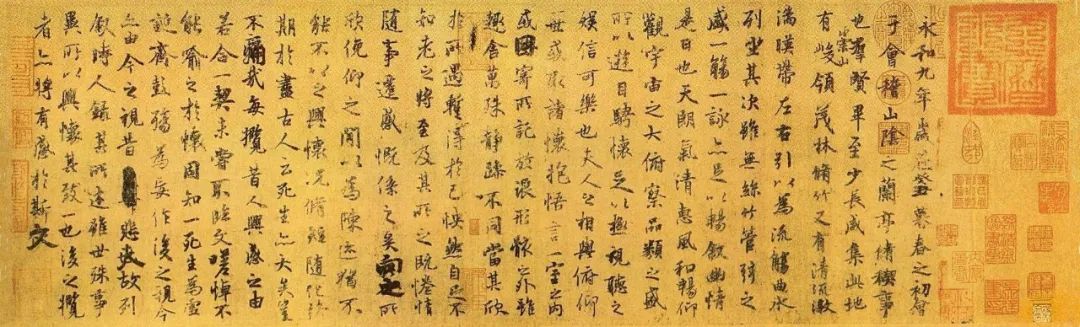
东林在今江苏无锡,原是宋朝大儒杨时(字中立,号龟山,1053—1135)归隐讲学之处,到明朝逐渐成为一个有名的书院。东林书院的人物讲学,十分注重经世致用。所谓经世致用,也就是后世说的“学问为济世之本”,主张求学问是要用来服务社会的。东林书院的学者都比较主张用学术干预实际政治,学问不是空谈心性就够了,说穿了,就是传统儒家讲的“内圣外王”之学,而所谓“内圣外王”,讲的就是自己修养好了,要去解救世人,君子是不以“独善其身”为满足的,必求兼善天下。
《明儒学案》形容东林师友的特色,说:“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冷风指社会的反响不见得好,热血指自己仍不死心,虽经挫折,仍充满了拯救时代的愿力。黄宗羲又称道东林的作用,说:“数十年来,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义之盛,度越前代,犹是东林流风余韵也。”可见东林在晚明的作用及重要性。
东林派学者基本上都是阳明学派,但他们对晚明有一派的阳明后学很不满,认为其太猖狂又不学无术。东林派学者都比较重视读书,又主张读书要能变化气质,还认为读书的目的不在讲玄虚的道理,更不在媚俗,而在立身。立身的目的是要积极服务社会,即“经世”。今天我们到无锡的东林书院,还看得到那副有名的对联高悬在大厅,对联写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东林书院领导人顾宪成(字叔时,号泾阳,1550—1612)写的,于此可见东林派学者的胸襟。
刘宗周治学严谨,一生标举“慎独”两字,要求学生哪怕一个人独处,也得小心谨慎,丝毫不苟。
刘宗周无疑是明代阳明学的殿军,承袭了阳明良知学说中最严谨的部分,对良知说所达的幽微处境深有所契,对当时阳明学的“末流”也严词批判。
有一点非常值得说的是,刘宗周虽也科举出身,但在明亡时并未担任要职。他在北京任职时经常上书,却多次被崇祯斥为迂阔。听到明思宗崇祯帝自缢煤山的消息后,他悲痛不已,后来眼看着清兵南下,杭州即将沦陷,竟然采取绝食的方式殉国了。绝食是很辛苦的事,要靠极坚强的意志力才能做到。刘的绝食而死,在当时影响很大,他的学生王毓蓍(?—1645)、祝渊(1614—1645)也都先后自杀,还有一些学生如陈确(字乾初,1604—1677)、黄宗羲等虽未死,却以气节自励,不肯降清,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很大。
今天要研究明代思想,一定要依据、参考黄宗羲的《明儒学案》,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来看《明儒学案》这本书,王阳明及其后学所形成的学派占有多少篇幅。
《明儒学案》从第一卷《崇仁学案》开始到第六十二卷《蕺山学案》为止,一共六十二卷,卷九之前是阳明前的诸儒学案,包括《崇仁学案》四卷、《白沙学案》二卷、《河东学案》二卷、《三原学案》一卷,从第十卷《姚江学案》(就是写阳明本身的那一部分)之后,其中在《泰州学案》五卷之前有《止修学案》一卷,《泰州学案》后有《甘泉学案》六卷,《诸儒学案》上、中、下十五卷,《东林学案》四卷,《蕺山学案》一卷。最后这两学案中的人物对阳明学虽有批判,但也算是阳明学的一支,所以我统计全书,写阳明、阳明后学的共有三十一卷,以卷数而言,正好占了《明儒学案》的一半;就内容而言,当然更不止于此,因为阳明后的“诸儒”,就算其学宗旨不标榜阳明学,其所讨论的,也绝大多数是与阳明学有关的事。
我认为阳明学的重要,在于它改变了传统儒学的态势,也就是说阳明学比较注意自己存在的必要,这是以往儒学家比较忽视的问题。
传统的儒家比较注意礼,比较讲道德,礼是一种行为的约束,而道德又是社会生活下的产物,因此儒家讲学问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的,这套学问讲到极致,往往忽略了自己,忽略了个人。阳明学比较注意个人良知的呈现,主张一个人内心最初的判断往往最为准确。这种有点否定传统认知的说法,在当时引起了很多的争议与回响,是十分特殊的。当然在阳明之前,在北宋的时候与朱熹(字元晦,号晦庵,1130—1200)同时的陆九渊(字子静,号存斋,学者称象山先生,1139—1193)之学,已经有了这种“态势”了。“陆学”与“朱学”最大的不同在于“朱学”比较讲学问,即“道问学”,强调学问知识的重要,而陆九渊比较注意的是“尊德性”,即重视一个人的内在涵养,换句话说是重视一个人的内心所达到的道德境界,因此“陆学”也被称为是“发明本心”。
陆九渊这派学说比较注意内在,不求外表,在乎心之所得,不在乎自己读过了多少书、掌握了多少知识。但在宋朝,“陆学”的势力始终不敌“朱学”,原因是客观知识比变化莫测的内心更好把握一些,“朱学”比较有途径可寻,而“陆学”的境界对于一般人而言,反而难以达成。
但到了明朝,这种态势就大大改变了,这是因为“朱学”已兴盛了几百年,本身已露出了疲态,再加上明代社会已去南宋的时代太远,很多事已变得十分不同了。王阳明的学说比较接近象山一派,陆、王之学都有一种“发明本心”的倾向,阳明之学自兴起后,得到的社会呼应极大。在明代,“王学”的兴起有点像掀起了一场遍及社会各阶层的“发现自我”运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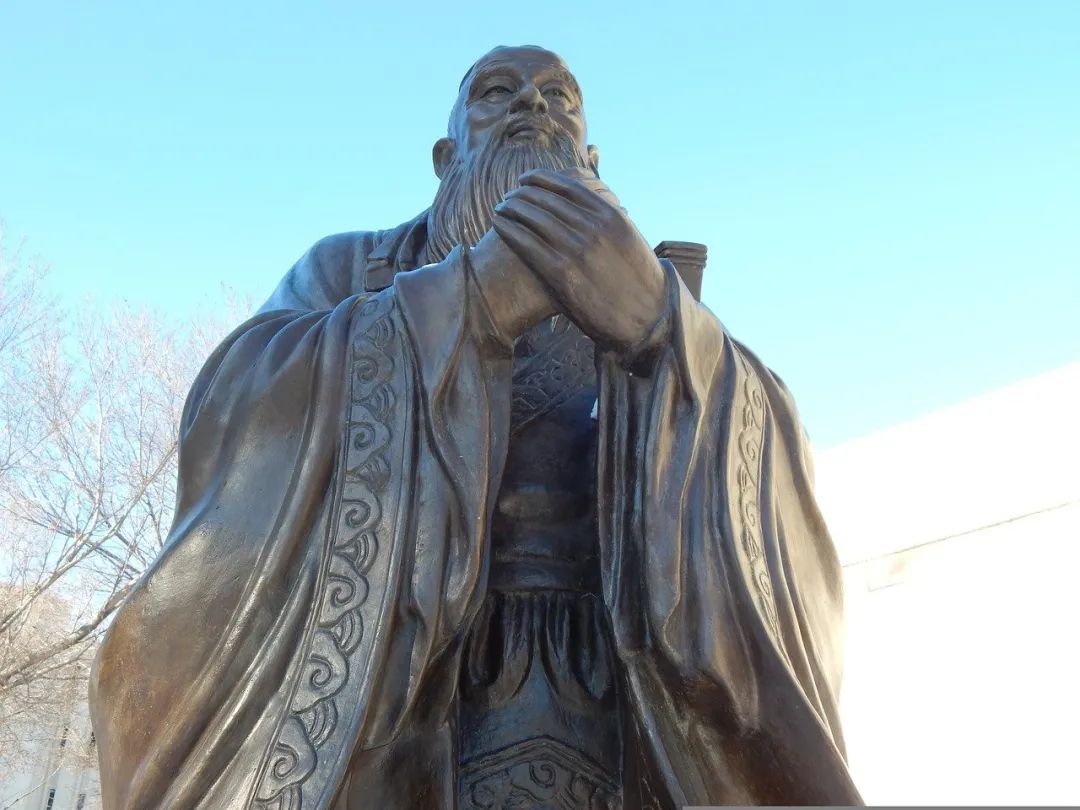
知道西方的这段历史,再回来看中国历来的思想家都想重新定位孔子,都想以自己的所思所想来解释孔子,也就没什么不合理了。孔子的出生比耶稣早了几百年。在中国,孔子的思想影响极大,历来关于他的意义、他的作用的讨论,当然多得不胜枚举,但可幸的是,中国从未因对孔子的解释不同而发生过战争。
孔子的“伟大”,一部分是孔子本身的伟大,一部分是后世的人让他变得更伟大。
我们知道,孔子在生前,是一个鲁国的读书人(当时称作“士”,是做官与读书人的一个模糊称呼)。孔子曾被鲁国的国君赏识,在鲁国做过短期的官,官位还不算小,但随即因不得志下台了。他在政治上虽然很有能力,但鲁君对他的信任不足,而当时鲁国政权旁落,就算鲁君对他信任也没有太大作用。后来他曾率领弟子周游列国,到过齐国、卫国、陈国、蔡国与楚国(其实都只在现在的山东、河南一带),以今天的标准而言,都不算远,不过在还是马车或徒步的古代,就也不算近了。孔子在外的日子大都不得志,不受重用,经历过许多无聊的日子,也经过不少风险的打击,最后还是回到了鲁国,专心整理古书与教育学生。
孔子活着的时候,对他的时代当然是有影响的,但影响力并不很大,范围大约只在鲁国(今山东中西部的一小片区域)一带,与整个中国相比,那是个很小的地方。孔子在学问上当然是有所创获的,但同时代或稍晚于他的人,有的也是有创获的。当时把每个在学问上有创获且有特色的人,都称为“子”。春秋战国时代,是诸“子”流行的时代,后世叫那时的学问,叫作“子学”或“诸子”学。孔子是当时的诸子之一,而孔子所代表的儒家也跟道家、稍后的墨家与之后的法家、名家等一样,都是当时的一个学术流派。
要说儒家这一学派,只能说是先秦的“显学”之一。战国时代是“百家争鸣”的时代,数得出来的学派就有“九流十家”。所谓“显学”,至少包括了儒家、道家、墨家与法家四家,“显学”是指它比其他学派的成就与影响都更明显一点,地位自然也更重要一点,但不是说它能操纵一切。
到了公元前2世纪,汉统一了天下,中国结束了从春秋战国到秦近五百年的分崩离析。汉初的时候,讲黄老之术的道家风行,主要是面对战国的乱局与秦统一后的暴政,人民需要休养生息,这一时期文帝与景帝当政,历史上称之为“文景之治”。汉武帝即位后,比较想有所作为,前两代的休养生息也让他有了机会: 在政治上,大权独揽;在军事上,对强大的北方匈奴不再继续保持守势;在学术上,采取了董仲舒(前179—前104)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统一帝国的思想化为有形的力量。这是儒家思想第一次以空前的君临天下的姿态进入权力的核心,成为政府施政治国的最高指导原则。
汉儒的说法,有点夸大,这六部经典,其实依后儒的考证,都没有经孔子“删”过、“订”过,孔子也没“赞”过《周易》,但这些古代留下的书都曾当过孔子施教的教材,可能多少都经过了孔子或孔门弟子的整理。除了《论语·子罕》有孔子说的“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能证明孔子在《诗经》上曾做过“正乐”的工作之外,对其他的书做了哪些事,因缺乏可信的记录,我们就无法知道全面的消息了。
关于孔子是否“述”“作”了《春秋》之外的“五经”,是中国经学史上重大的问题,讨论的文献很多,现在不详说。至于“作《春秋》”的说法,司马迁说“孔子因史记而作《春秋》”(凭借着历史记录而编写了《春秋》),也许不错,《春秋》这部书可能真是孔子写的,但历史是根据史料而编的,历史是不能“作”(创作)的,所以司马迁的“作《春秋》”的“作”当作“编”字解,不能视为一般“创作”的“作”,此字只能用广义来解释,不能作狭义的解释。
中国历代的思想家都想解释孔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连带也讨论儒家的性质、儒家该做什么事等问题。汉儒解释下的孔子,恐怕跟我们现在所知的孔子,是有着十万八千里的差异的。在汉儒(尤其是西汉今文经学派的学者)的眼中,几乎把孔子神明化了。这种看法起源自对统治者的看法。古时人对统治天下的君主,不论中西,往往都有神明的联想,所以中国称一统天下而治天下的人为“天子”,西方称君王的统治权是“君权神授”,起源都很相同,其实是神权统治的旧例。
西汉的很多学者认为孔子不但是政治家,而且认定孔子“该”是个统管天下的天子。当时脱神权时代未远,孔子如能统管天下,就该具有“神性”,具有神性的人就等于是神,神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有经天纬地的作用,所以孔子之言都极为重要,等于是神的告谕,这是西汉时一般人的观念。但真实的状况是什么呢?孔子其实是个古时的一个穷读书人,哪有神或天子的本事呢!
汉儒特别为孔子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名词,称孔子为“素王”。在秦始皇之前中国是没有人叫作皇帝的,统领天下的叫“王”,王下面的各国领袖叫诸侯,诸侯又依公、侯、伯、子、男的等第而位阶不同,称法各异。西周自武王之后的诸王都是当时天下的“共主”,是高高在上的天子,孔子被叫成“素王”,就是将之视同统领天下的天子了。但孔子是“素王”而不是“王”,表示与具有实际统治权的真“王”还是有差别的。“素”是什么意思呢?素在古时是指没经过染色的丝。丝虽没有经过染色,但还是丝,孔子因没有真实居于天子的位置,没有王的仪节文饰,故称“素王”,但究其实际,时人认为孔子是具有统领天下一切的本质的。
汉儒视孔子为“素王”,精神上尊他至高无上、独一无二,所以孔子经手的六本书都被命为“经”了。所有叫“经”的书都有神圣的、标准法式作用的意义,“六经”当然也不例外。汉代之前,孔子只是诸子之一;汉代之后,孔子不但是圣人,而且是“素王”了。儒术被独尊之后,连跟孔子有关的几部书也都成为“经”了,所以冯友兰(1895—1990)写的《中国哲学史》把中国的汉以后称作“经学时代”,汉之前称作“子学时代”。冯友兰的说法很特别,但从某个观念切入,是大体可以成立的。
西汉的儒学家在“六经”中特别注意的是《春秋》,因为经学家认为这本书是孔子所著的,当然比其他五经更为重要。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说:
《春秋》写得很简单(一方面孔子主张“词达而已”,另一方面可能是受当时书写工具的影响,不得不简单),因太简单了,所以给了许多后儒可用来作不同解释的机会。汉儒把这些说得不很清楚的话叫作“微言”,认为在《春秋》的“微言”中其实都藏有“大义”,将《春秋》深藏的“大义”解释出来是很有必要的,当时认为最具权威的解释是《春秋公羊传》。这本书,传说是公羊高氏写的。公羊高,传说是孔子的弟子子夏的门人,算起来该是战国初年的人物,但非常有意思的是,书里面附会了许多战国阴阳家的说法,倒像是秦汉之际人的作品,书中也有一些对未来预言的部分。《春秋》原本是一部记录历史的书,但在《公羊传》的解释下,孔子就成了既有治天下意图又似乎是充满权谋的人物了。
西汉讲公羊学的“公羊派”曾权倾一时,董仲舒本人是“公羊家”,他的《春秋繁露》里面的记载与推论都有很可笑的地方,尤其是他非常相信灾异,相信上天的“示警”。譬如他说:“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这种言论充满了汉代人习惯的谶纬说法与迷信色彩,今天看来是很荒谬、可笑的,但我们如果能回到那个时代,就知道那些荒谬与迷信,在时人看来既不荒谬也不迷信,那是时人对自己不很清楚的世界所作的一种他们认为“合理”的解释。
以今天的角度而言,当时人的看法是很有问题的,而当时的人都信以为真。历史学家司马迁是孔安国(孔子十一世孙)的学生,孔安国本身也是个“公羊家”。司马迁是个十分杰出的历史家,也是杰出的文学家,却也信公羊派说的那一套,他还是无法全面摆脱那个时代的迷雾,要知道很少有人能完全超越他所处时代的迷雾的。
直到东汉,因为政治气候改变,学术气候也有了改变。古文经已陆续被发现,古文经里的说法与今文经的说法往往大异其趣,尤其在历史的诠释上,相形之下,孔子神秘的面纱被揭开了,孔子与儒家典籍的神秘色彩也变淡了,当然速度是缓慢的。到东汉末年,儒学才有逐渐摆脱迷信、回到孔子本来面目的可能。
西汉的儒学是充满神秘色彩的,至东汉时代,慢慢得以廓清,因为《论语》里面说过“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虽生长在“迷信”的社会,但自己是很不迷信的,东汉的儒者不再在迷信事件上搅和,这一点,确实是进步了。随着研究经书的人增加,研究的成就也在提升,经学学术化了后,探讨者愈多,使得经书也有扩充的需要。
“六经”这名词是从“六艺”来的。在孔子的时代,“六艺”一方面指孔子以六种技艺教学,即礼、乐、射、御、书、数;另一方面也指后来的“六经”。但就在经学观念形成的西汉,“六经”其实也是个虚幻的名词,因为自始至终都只有“五经”而已,其中《乐经》早就不存在了。至于原因,有的说是毁于秦火,有的说《诗经》的可歌部分就是《乐经》,也有的说《礼记》里面的《乐记》就是《乐经》之旧,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唯一的事实是“六经”只剩下“五经”,汉初开设的是“五经博士”,未有“六经博士”。西汉人对经的定义很执着,所谓的经书,不是孔子所“手著”,就是孔子所“手订”,必须与孔子发生亲密关系的才能称得上“经”。譬如《论语》,其实是后世研究孔子与弟子言行最重要的一本书,实际价值有时比“五经”还重要。但在汉代,《论语》却不称为经,原因很简单,因为《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录的,不是孔子的著作,孔子也从未见过此书,不能目之为经。
东汉出了有异于前代的经学家,如扬雄(字子云,前53—18)、王充(字仲任,27—97)、许慎(字叔重,58—148)、马融(字季长,79—166)、郑玄(字康成,127—200)、服虔(字子慎,后汉人,生卒不可考)等,他们的论述,已超过西汉儒家喜欢谈的内容,对于公羊的今文观点也不那么拘泥,材料上也不轻视后出现的“古文经”,对学术材料往往以持平眼光看待。所以到了东汉末年,经典不但扩充了,儒家思想也变得比较能兼容,朝着博大深入之途一路开展过去。
但不久汉朝又陷入乱局,三国时代来临,之后从西晋、东晋到南北朝,中国由一统变为乱世与衰世,中央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原本很一致的思想,也逐渐产生了分歧。
魏晋之际的人喜欢归隐,喜欢过逍遥一点的生活,人聚在一起,喜欢“清谈”。所谓清谈,就是谈些与实际生活没有太大关系的事,语言的内容是充满玄虚意味的,所以也叫作“玄谈”或“谈玄”。这是当时的风气,可能与当时政治上很混乱,知识分子没有一定的出路有关。
“九经”这名词刚出现不久,儒学想借经典的开拓而振兴学术,一度是有望的,不料衰世来到,又使得经学衰微了。从魏晋到南北朝,道家思想比儒家兴盛,由于道家比儒家更具反向思考的本事,用它来唱反调再适合不过,一些仅剩的儒家为了争取读者,也纷纷用道家的方式来解释儒家的经典,其中以《周易》为最多。因为《周易》原本是占卜之书,里面有很玄秘的成分,能让喜好玄虚的士人有驰骋想象与议论的空间。
到了南北朝,佛教开始流行,带领出一种新的风气,隋、唐之际,佛教更为流行。唐代虽号称是盛世,但儒学并不是很昌盛。唐朝皇帝因姓李,自以为是老子后人,所以奉道教为国教,但从朝廷到民间,更流行的其实是外来的佛教。看唐代的历史,正统的儒家人物好像“出头”的机会都不多,在朝廷比较有力的,多是有佛道色彩的人物,以诗人而言,李白不在话下,有佛教名号的“摩诘居士”王维与“香山居士”白居易,比起一生信仰儒家思想的杜甫都混得好,就是明证。
在中唐有韩愈,曾因谏皇帝迎佛骨入宫而被贬远戍潮州,他的《原道》一文更指出中国的正统思想儒家在唐朝所遇到的危机。当时的天下大势,是“不入于老,则入于佛”,道与佛相较,佛教更为有力。韩愈提出建议,呼吁朝廷与社会要尽力地排除佛教,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口号。所谓“人其人”,是指要让佛教的出家人都还俗;“火其书”,是指把那些佛教经典都烧了;“庐其居”,是把所有佛教庙宇都改成住宅,给百姓去居住。历史证明秦始皇焚书坑儒是荒诞的,是错误的,而韩愈却要用这荒诞与错误的手法来对付他所说的外来的佛教,是否正确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韩愈与当时知识分子面对传统儒家的衰微感到忧心,于此可见一斑。
宋代比起唐代国力看起来是衰落了,中国所能控制的土地面积也小了很多,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争执,攻势较少,守势较多,表面上弱了许多。但我们不能光从这些表面的现象看,其实宋代也有强项。
宋代与唐代比较,是个很不同的时代。唐代的文化是一种闪耀式的文化,国势很强,首都长安有许多外国人,包括印度来的、西域来的与北方民族来的。中国文化一方面忙着与外国文化融合,另一方面也不吝惜展现自己的辉煌。但什么是中国文化,多少是真正传统的部分,多少是后来从外来文化加入的部分,并不那么好区别,好在一些本属外来的文化,进入中国之后,也逐渐被中国文化所“同化”,佛教的禅宗就是一例。所以唐代人讨论这个问题时,线条很乱,答案也不很明确。但到了宋代就不同了,国家小了,前朝的辉煌(多半是融合时所发的光辉)好像也流逝了,不在强光的迷惑之下,人容易去做内省的活动,人正好利用这个不那么辉煌的时代来沉淀思绪,所以宋代是一个比较具有沉思性格的时代。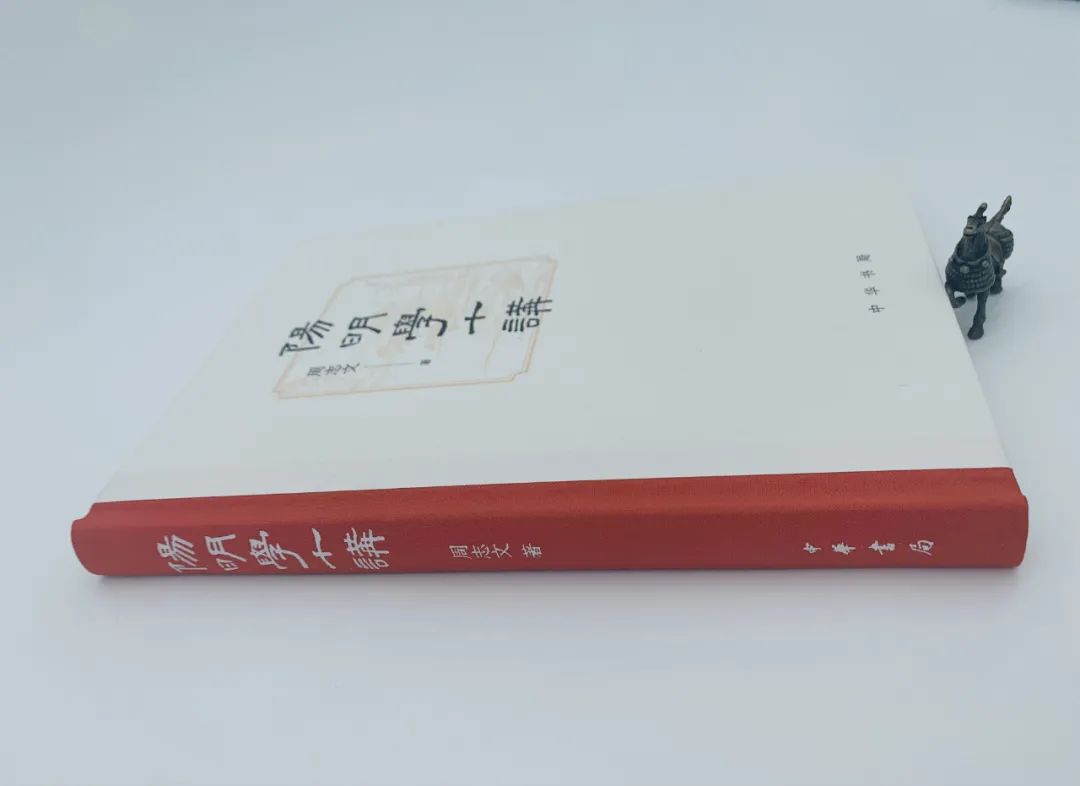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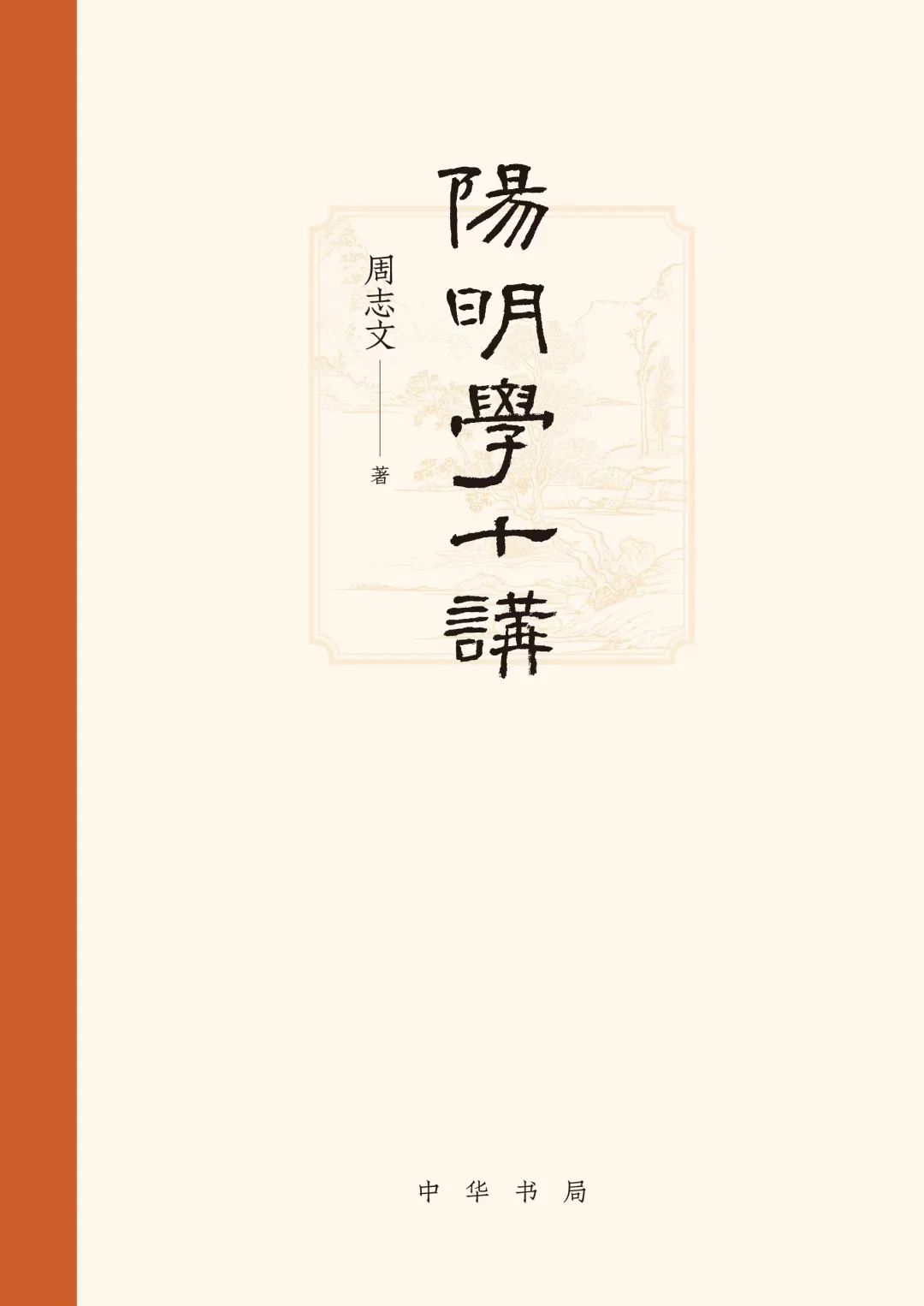

www.zhbc.com.cn zhbc@zhbc.com.cn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邮编: 10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