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文化教师素养读本
作者:楼宇烈,傅首清主编
定价:¥58.00
中华文化教师素养读本
作者:楼宇烈,傅首清主编
定价:¥58.0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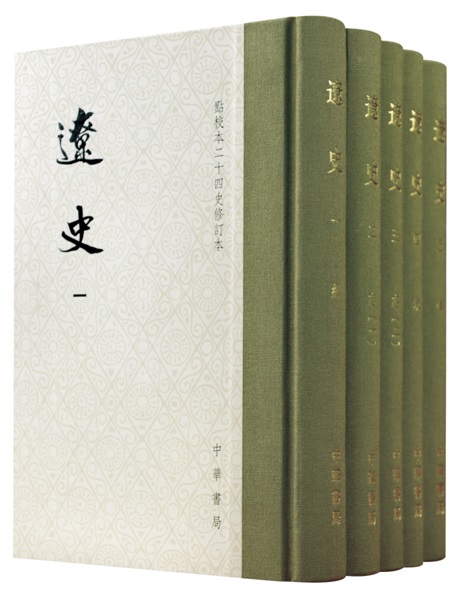 辽史--全五册(精)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
作者:脱脱著 刘浦江整理
定价:¥280.00
辽史--全五册(精)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
作者:脱脱著 刘浦江整理
定价:¥280.0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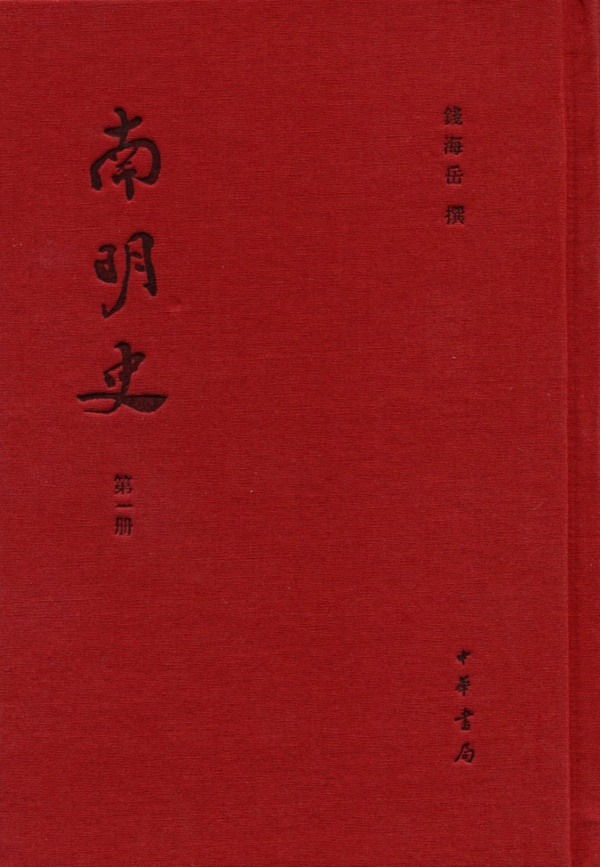 南明史(精装本)
作者:钱海岳撰
定价:¥980.00
南明史(精装本)
作者:钱海岳撰
定价:¥980.0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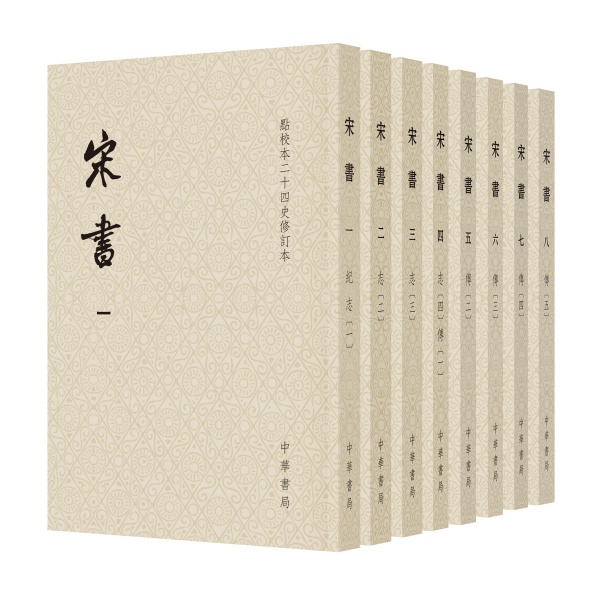 宋书(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平装本)
作者:(梁)沈约 撰
定价:¥360.00
宋书(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平装本)
作者:(梁)沈约 撰
定价:¥360.00
-
 魏书—(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精装)
作者:魏收著 何德章,冻国栋修订
定价:¥510.00
魏书—(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精装)
作者:魏收著 何德章,冻国栋修订
定价:¥510.00
-
 史记--全五册(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精
作者:[汉]司马迁撰 陈曦、王珏、王晓东、周旻译
定价:¥298.00
史记--全五册(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精
作者:[汉]司马迁撰 陈曦、王珏、王晓东、周旻译
定价:¥298.00
-
 全元词(全三册)--中国古典文学总集
作者:杨镰主编
定价:¥298.00
全元词(全三册)--中国古典文学总集
作者:杨镰主编
定价:¥298.00
-
 明实录 附校勘记(183册)布面精装
作者: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 黄彰健校勘
定价:¥45000.00
明实录 附校勘记(183册)布面精装
作者: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 黄彰健校勘
定价:¥45000.0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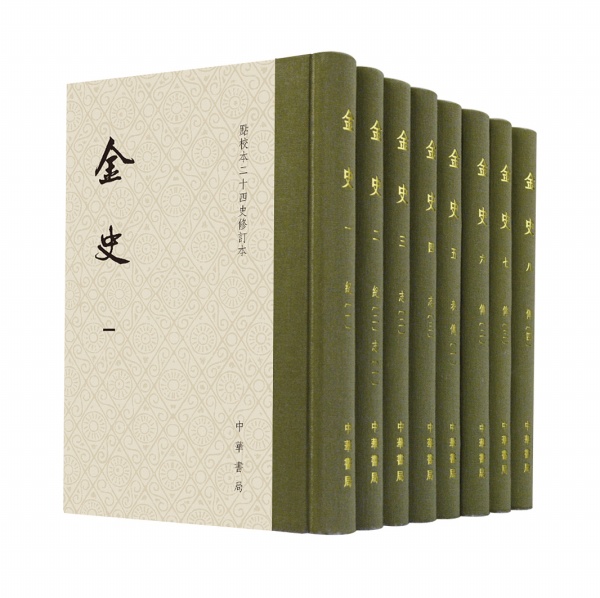 金史(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精)
作者:[元]脱脱等撰
定价:¥540.00
金史(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精)
作者:[元]脱脱等撰
定价:¥540.00
-
邹鲁文化研究 作者:贾庆超等 定价:¥0.00
唐朝人的婚姻讲究门第。婚姻讲究门当户对,这在家庭学中也可以叫作“同类婚”或者“地位族内婚”。婚姻看门第是一种习俗,也是一个传统,而习俗正是传统的积淀。门第婚姻使个人的行为,变成家庭乃至家族的行为,使男女之间的性爱和感情问题,变成了社会政治问题。
门第观念是自古至今都或多或少就存在的影响到男女择偶的因素之一,不独唐代为然。唐朝门第观念在婚姻上的表现是,它并不完全以政治地位的高低或者家庭财富的多寡作为衡量门第高下的标准。这其实在南朝就已经如此。侯景求婚王、谢,梁武帝认为:“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这些出身卑微而获宠致高位者都巴望与高门结亲。北朝则有卖婚之习俗,这种状况延续到唐代。
唐朝法律规定良贱不得为婚,没有规定不同门第的男女不能结婚。良贱不婚,是法律的刚性规定,门第不对而不婚是习俗的弹性约束。唐朝人所谓名门或者高门,又称旧族,乃是指南北朝以来的士族,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所谓山东士族崔、卢、李、郑、王诸家。这些家族在政治上的地位并不是最显赫的,经济上也不是最富有的,但是,在门第上却被认为是最高的。《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对宰相房玄龄说:
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
唐太宗这里是打着恢复礼经的旗号来批评山东旧族嫁娶中广索聘财的。但是,他所采取的实际措施则是下令重新编定氏族等级:“乃诏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牒,兼据凭史、传,剪其浮华,定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士廉等及进定氏族等第,遂以崔幹为第一等。”从主持这项工作的大臣来看,都属于唐朝主管人事、监察、决策和礼仪等方面事务的最高领导人,其中如渤海高氏、城南韦氏、代北令狐氏也都属于名门望族,只有岑文本是普通庶族。他们都一致认为应该以山东士族崔氏为第一,就很耐人寻味。这说明朝野各方都公认山东士族的门第为天下第一。对此,唐太宗非常不满,愤愤地说:
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际,则多索钱物。或才识庸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檟,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
为此,唐太宗提出了自己对于门第高下的评定标准:
且士大夫有能立功,爵位崇重,善事君父,忠孝可称;或道义清素,学艺通博,此亦足为门户,可谓天下士大夫。今崔、卢之属,唯矜远叶衣冠,宁比当朝之贵?公卿已下,何假多输钱物,兼与他气势,向声背实,以得为荣。我今定氏族者,诚欲崇树今朝冠冕,何因崔幹犹为第一等,只看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论数代已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宜一量定,用为永则。
按照这个标准编定《氏族志》后,皇帝之家被列为第一等,太宗下诏说:“氏族之美,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太宗虽然一再强调人伦(礼仪)名教,却把礼仪名教混同于冠冕。在他看来,失去官爵者也失去了礼仪名教,可见唐太宗实际上篡改了礼法文化的内涵。当然,用比较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推行自己另有图谋的政治主张历来是当权者的一种高明的政治技巧。唐太宗的本意是要加强新建朝廷的政治权威,打击旧的政治势力的“气势”,但是,他却挂羊头卖狗肉,采取了维护仁义和名教的说法。
其实,北朝的士族乃以礼法而著名,可以说是礼法文化的代表。而帮助唐太宗打天下的那些以关中军功贵族为核心的新朝权贵,倒是比较缺乏礼法文化的底蕴。李唐皇室在婚姻上不讲礼法的糊涂账姑且勿论,在北朝,北齐崔㥄“一门婚嫁,皆衣冠美族,吉凶仪范,为当时所称”。娄太后为博陵王纳其妹为妃,敕操办婚事的中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由此可见,礼法文化正是这些士族受到包括皇室在内的人尊敬的原因。公孙表的儿子轨娶渤海封氏女为妻,生儿子叡,叡之妻为崔浩弟女。叡的堂兄公孙邃的母亲是雁门李氏,地望悬隔,“吉凶会集,便有士庶之异”。所以,当时人说:“士大夫当须好婚亲。”显然,这里的士庶之异,乃是在吉凶会集之时,由于受到不同的礼法门风的熏陶所表现出来的在吉凶礼仪上举止的差异。
究竟是山东氏族不讲礼法名教,还是被列为氏族第一的李氏皇族缺乏礼法文化呢?一两百年后唐太宗的后代做了最好的回答。文宗欲以真源、临真二公主降士,谓宰相曰:“民间修昏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宣宗为公主求婚于士族,发现公主漠视小叔子患病,也不回家侍候婆婆,提出了批评。还有一位待嫁于士族家的小公主吃饭时发脾气折筷子,被宣宗大加呵斥,并且决定换一位性情温顺的公主出嫁。这些情况都表明,唐太宗的后裔们已经用主动向士族求婚的做法,证明了唐太宗当初批评山东士族不讲礼法文化,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正是因为唐太宗对于山东氏族的指责不尽符合历史事实,所以,即使朝廷有意压抑,山东氏族仍然旧望不减。
但是,唐太宗对山东旧族的指责也不是完全无的放矢。他指责山东旧族不讲礼法固然不符合事实,但是,他批评山东旧族据门第自高,索取高额聘财则并非无据。问题是,对于门第与聘财之间的关系,需要做进一步的讨论。
试以唐人小说中的一些故事为例进行分析。《玄怪录》卷一《张老》记载了一个男子求婚的故事。说是士族韦恕有“长女既笄,召里中媒媪,令访良才”。扬州六合的菜农张老闻之,把媒婆请回家,且备酒食,百般央求媒婆为自己说媒。媒婆骂他是不自量力:“岂有衣冠子女肯嫁园叟耶?此家诚贫,士大夫家之敌者不少。顾叟非匹……”但是,在张某的百般请求下,媒婆硬着头皮向韦家提这门亲事。韦恕大怒,责怪媒婆:“以我贫,轻我乃如是!且韦家焉有此事,况园叟何人,敢发此议!”并发难说:“为吾报之,令日内得五百缗则可。”要一个菜农一日之内拿500缗钱的聘礼,这显然是在出难题,意思是要张某放弃自己的想法。故事的神奇在于,张某居然马上携500缗钱来订婚。韦家大为尴尬。女儿也默认了这桩婚事,“乃曰:‘此固命乎!’遂许焉”。张某娶韦女后依旧在扬州种菜,“园业不废,负秽锄地,鬻蔬不辍”,过着平静的农家生活。但是,韦家的内外亲戚觉得此门亲事有伤体面,指责韦恕说:“居家诚贫,乡里岂无贫子弟,奈何以女妻园叟?既充之,何不令远去也!”意思是即使把女儿嫁给一个贫穷的士族子弟也比现在强。其实这也是韦女家长当初的想法,应该说这个观念在当时是极具典型性的。门第比财富要强。
张老与韦氏女婚姻缔结的典型意义值得分析。首先,婚姻的缔结,需要有媒妁之言,乡里似乎专门有从事婚介职业的媒婆:“召里中媒媪,令访良才。”媒婆当然要接受介绍费,尽管文中没有说。《玄怪录》还提到另外一位韦小姐的婚事。“京兆韦氏女者,既笄二年”,母亲告诉她,有秀才裴爽求婚,女儿笑而不允。“虽媒媪日来,盛陈裴之才,其家甚慕之,然终不谐。”过了一年,有前京兆府参军事王悟将来聘,媒人是京兆府司录、韦小姐的老舅张审约。韦女还是不允。再过了两年,进士张楚金求婚,“母以告之,女笑曰:‘吾之夫乃此人也。’母许之”,于是择吉日、成礼。结果韦女20岁才结婚。韦小姐15岁成笄,待字闺中五年,方答应嫁给如意郎君。这个故事反映出女孩子在择偶上还是有一定的自主权的,韦母也算比较开通。值得注意的是,最后韦女选定了张楚金为婿,故事没有忘记说“母许之”,清楚地点出了女儿同意了,也还是要家长同意不可。《户婚律》规定尊长拥有子女婚姻决定权,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不经过尊长的同意而成婚。“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即使已经订婚,只要未成婚,尊长都有权终止卑幼自行选择的配偶。这当然是法律的规定。在实际情况下,像京兆韦小姐那样自己决定、父母同意,或者如张老所娶的韦氏那样,父母决定、女儿接受的婚姻,当为普遍的情形。
根据疏议的解释,这条法律在尊长卑幼上有具体的适用范围:“尊长,谓祖父母、父母及伯叔父母、姑、兄、姊。”“卑幼,谓子孙、弟、侄等。”长辈对于子孙辈的人有婚姻决定权,自无疑问。但是,兄长对于弟妹的婚事恐怕没有决定权。敦煌判集有一则案例说,一位兄长代替寡居的妹妹去找婆家,妹妹不从,这位当哥哥的在婚约已成而不履约将违法的情况下,被迫让自己的女儿代姑姑去成亲,结果吃了官司。
女方究竟接受多少聘财才不是卖婚呢?唐朝甚至一度作出了法律上的规定。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十月诏:“天下嫁女受财,三品以上之家,不得过绢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过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过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过五十匹。皆充所嫁女资装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门之财。”这等于从法律上为聘财规定了一个上限。考虑到唐代太宗、高宗之世,正是打击山东士族“卖婚”行为的时期,这个限定多少有配合朝廷这一政策的政治含义,实际上是否执行则是要打问号的。从讨论的这则故事来说,500缗钱的价值恐怕超过了按规定平民之家所受聘财“不过五十匹”的许多倍!
正式的法律对于聘礼的多寡其实没有硬性规定。《唐律疏议》中说:“娉财无多少之限,酒食非。以财物为酒食者,亦同娉财。”也就是说聘礼在原则上只是一种信物,不在数额的多少。特别规定酒食非聘财,当是为了避免把男方宴请女家视为下聘礼,并不是说酒食之物不可以为聘财。所以,疏议中明确说“以财物为酒食者,亦同娉财”。而在实际生活中,聘财可能是影响男婚女嫁的一个重要因素。
比如《霍小玉传》言李益娶卢氏也提到聘财问题:“未至家日,太夫人已与商量表妹卢氏,言约已定。太夫人素严毅,生逡巡不敢辞让,遂就礼谢,便有近期。卢亦甲族也,嫁女于他门,聘财必以百万为约。不满此数,义在不行。生家素贫,事须求贷……”“百万”就相当于千缗(贯)。婚姻贪财也不仅限于士族高门,《郭代公》记载某乡村为免灾,嫁送女孩给妖兽乌将军。某少女之父“利乡人五百缗”,暗地答应将女儿应选出嫁。后来该少女为郭元振所救,乃数落其父说:“今日贪钱五十万,以嫁妖兽……”是500缗为50万。这里虽然是小说故事,贪心的父亲为了钱财把女儿出卖了,却也折射了买卖婚姻的背景。
回到故事上来说,媒婆本意是要寻找门当户对的人家。由于张身份低下且年老,尽管种菜所入,足够衣食之需,但是,媒婆即使吃了张老的酒食,也不愿意去做说客,说士大夫之家门第相匹配的子弟多的是,韦家的小姐怎么能与种菜的农户结亲呢?后来韦家亲戚批评韦父,也是说即使家里穷也不至于以女妻园叟。既然没有办法,嫁给了园叟,也不应该让他们夫妻在眼前种菜过日子,言下之意是有损士族之家的声望。这里提出了嫁女的两大原则,即门第与财富。一般来说婚嫁中有富与贵的问题,但是,士族之家并不是贵族,更多的是一种声望,唐太宗就说他们全无冠冕,只是贩鬻祖父坟上的松树,意思是凭门第来换钱。这个故事在表面上告诉我们士族之家宁愿嫁女给穷困的士族,也不愿意与没有门第的园叟结亲。但是,韦恕提出一天内准备500缗钱的聘礼,虽然有故意为难张某之意,却分明透露了金钱可以改变门第的可能性。从一个具体事例上印证了唐太宗说的士族在婚姻关系中贩卖祖宗门第现象的存在。这个故事中的张老是一个神仙式的人物,后来在与韦家的几次交往中,都是给予了大量的金钱,特别是在韦家生活困难需要金钱的时候,总是及时地获得张老的救助。
聘财的多寡其实还有更进一步的含义。某村王家的独生女儿,“先许适西村张家”,由于聘财不足而罢婚。但是,罢婚的原因不仅仅是聘财少,而且是把聘财的多寡赋予了另外的意义:“今日纳财,非意单寡,此乃相轻之义,已决罢婚矣。”女方习惯把聘财的多少看成男方对自己是否尊重的表示。后来前来借住的阎庚求婚,“主人辞以田舍家,然有喜色。仁亶固求,方许焉。以马驴及他赍为贽,数日成亲毕,留阎侯止王氏”。看来,农家王某也是愿意攀附仕宦之家的。
就王家拒婚一事来看,女方重视的不仅仅是聘财,还认为聘财的多寡说明了男方是否对女方及其家庭有足够的尊重,于是聘财成为衡量女方及其门第身份的砝码。衰落的山东士族从心理上说,仍然有很强的自尊心,最不愿意承认自己衰落的事实,更不愿意因此而受到别人的轻视。这就是韦恕以及整个韦氏家族对于张老求婚表示极度愤怒的重要原因。这种心理下,山东士族想通过对方以大量的钱财来表示对自己的门第的尊重和重视,其实是很自然的,也可以理解的补偿心理。唐太宗把这种行为说成为“卖婚”而大动肝火,埋怨在新王朝统治下人们竟然不重视本朝冠冕,反映了新权贵对于旧士族不满的心情,明显具有压抑山东旧士族的政治意味。
即使到了唐朝末年,也有人借口聘财过于丰厚而加罪于婚姻当事人的。“(李绅)镇淮海日,吴湘为江都尉,时有零落衣冠颜氏女,寄寓广陵,有容色,相国欲纳之,吴湘强委禽焉,于是大怒,因其婚姻聘财反(‘反’字衍)甚丰,乃罗织执勘,准其俸料之外,有陈设之具,坐赃,奏而杀之,惩无礼也……颜寻归澧阳,孀独而终。”因为聘财过丰而导致婚姻当事人罹罪,虽然只是借口,却也反映了其时婚姻观念和社会意识的复杂形态。
总之,士庶通婚的界限被金钱、官职等打破之后,突破了所谓身份内婚制。这种情况也可以借助西方家庭社会学的所谓价值交换理论来解释。这种理论认为婚姻当事人及其家族缔结一门婚事,其实在进行某种价值交换。士族高门用他们的社会身份与拥有金钱和政治地位的新富新贵进行交换,从而达到一种新的心理的和社会的平衡。
根据以上几节的讨论,我们发现,唐代婚姻礼仪并不完全受礼法的约束。不仅结婚仪式未必是遵照《大唐开元礼》等礼仪制度的规定,即使《唐律疏议》关于不同辈分者不婚等规定也未必完全遵循不替。“不遵礼法”其实正是那个时代婚姻关系中的现实情况。这不是说没有礼法,而是由于唐太宗等开国统治者把礼教、门第和官爵等同起来,压制了旧士族为代表的礼法文化。统治集团内部旧族讲究礼法而新贵从不讲礼法到遵从礼法,这就是社会的一个变化。统治阶层讲究礼法,从而也逐渐地影响到民间遵从礼法,这也是社会的一个变化。这些变化背后所包含的历史意义,乃是社会对于士族的社会价值观、伦理观等所谓礼法制度的认同。士族的价值观念也由此而向整个社会普及,礼法文化出现了一个扩大传播范围的历史趋势,它构成了中古社会变革的重要基本线索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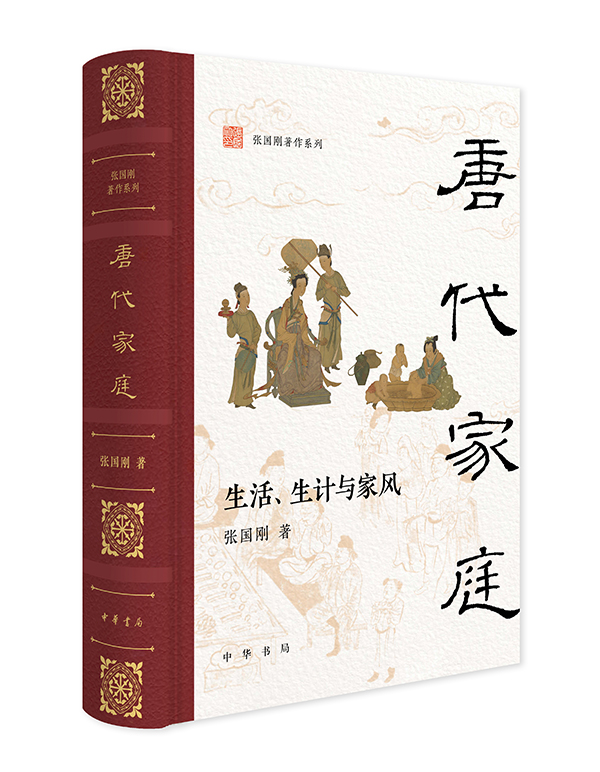


www.zhbc.com.cn zhbc@zhbc.com.cn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邮编: 1000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