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文化教师素养读本
作者:楼宇烈,傅首清主编
定价:¥58.00
中华文化教师素养读本
作者:楼宇烈,傅首清主编
定价:¥58.0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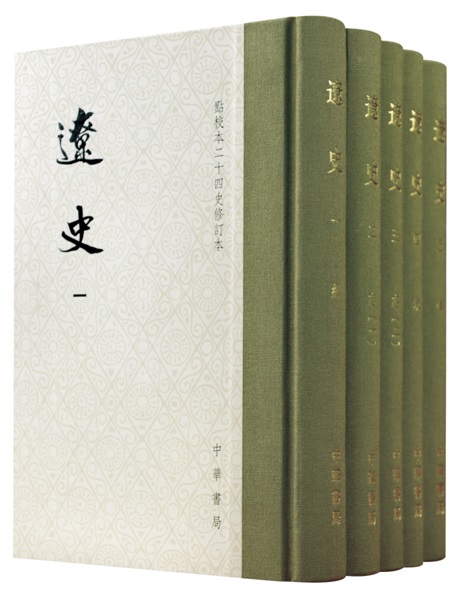 辽史--全五册(精)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
作者:脱脱著 刘浦江整理
定价:¥280.00
辽史--全五册(精)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
作者:脱脱著 刘浦江整理
定价:¥280.0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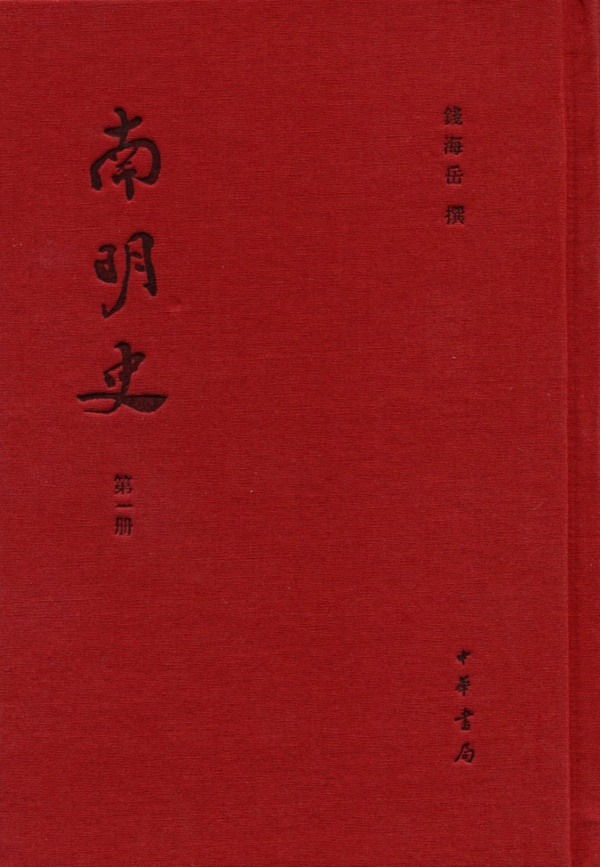 南明史(精装本)
作者:钱海岳撰
定价:¥980.00
南明史(精装本)
作者:钱海岳撰
定价:¥980.0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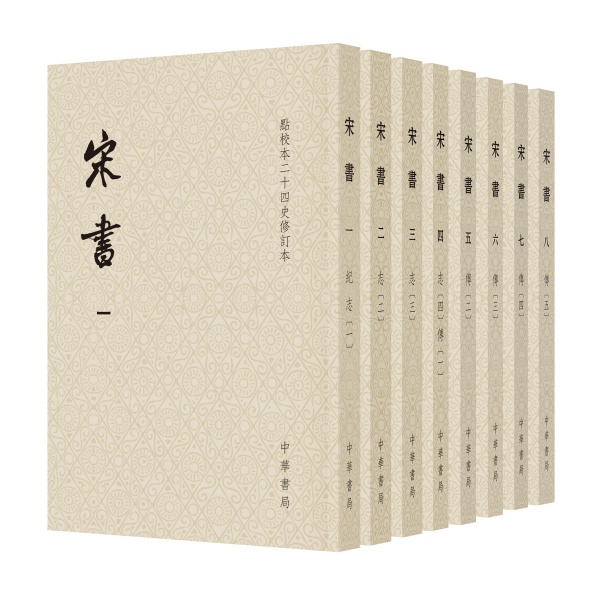 宋书(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平装本)
作者:(梁)沈约 撰
定价:¥360.00
宋书(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平装本)
作者:(梁)沈约 撰
定价:¥360.00
-
 魏书—(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精装)
作者:魏收著 何德章,冻国栋修订
定价:¥510.00
魏书—(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精装)
作者:魏收著 何德章,冻国栋修订
定价:¥510.00
-
 史记--全五册(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精
作者:[汉]司马迁撰 陈曦、王珏、王晓东、周旻译
定价:¥298.00
史记--全五册(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精
作者:[汉]司马迁撰 陈曦、王珏、王晓东、周旻译
定价:¥298.00
-
 全元词(全三册)--中国古典文学总集
作者:杨镰主编
定价:¥298.00
全元词(全三册)--中国古典文学总集
作者:杨镰主编
定价:¥298.0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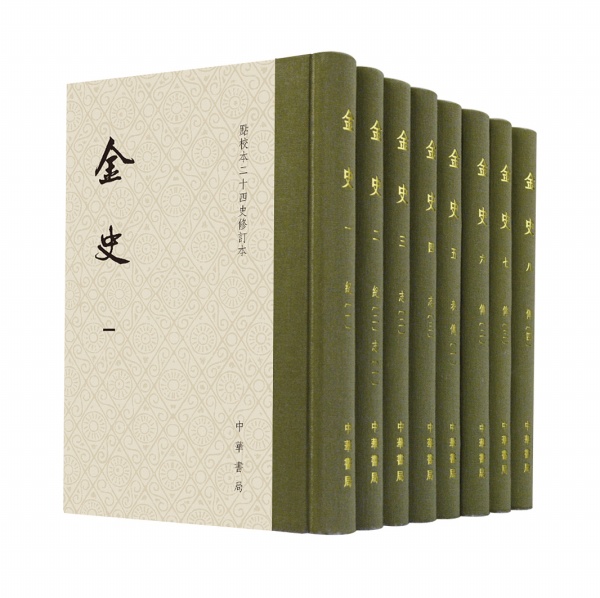 金史(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精)
作者:[元]脱脱等撰
定价:¥540.00
金史(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精)
作者:[元]脱脱等撰
定价:¥540.00
-
邹鲁文化研究 作者:贾庆超等 定价:¥0.00
-
 明实录 附校勘记(183册)布面精装
作者: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 黄彰健校勘
定价:¥45000.00
明实录 附校勘记(183册)布面精装
作者: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 黄彰健校勘
定价:¥45000.00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以下简称《三朝》),编年记述了万历四十六年(1618)至天启七年(1627)之间明王朝与后金政权在辽东地区的战争史。在这场战争中,明王朝是最终失败的一方,而在明朝阵营内部,作者王在晋本人也扮演着失败者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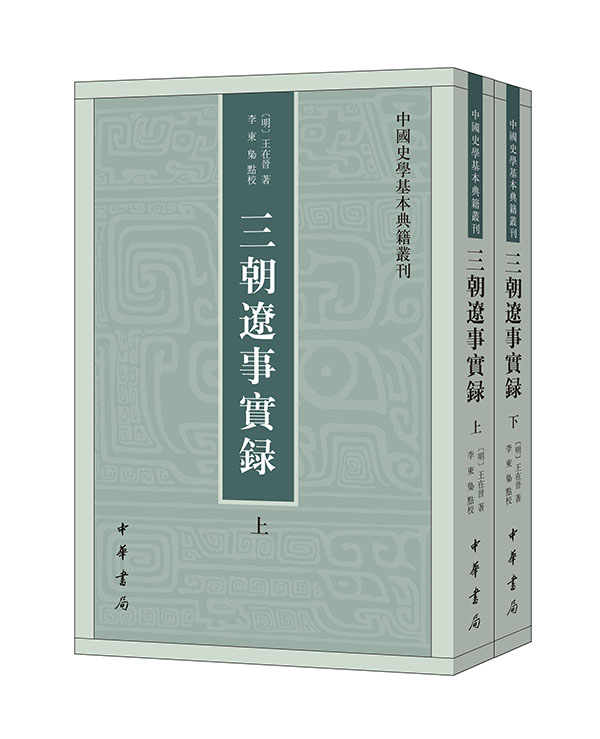
天启二年(1622),王在晋出任辽东经略,亲临战争的第一线。他的策略是稳固山海关一线的防御,反对贸然出击,因此主张在离山海关不远的八里铺筑城。此举遭到前来巡边的大学士孙承宗、王在晋的下属袁崇焕等人的联合反对,导致他被迫下野。孙承宗、袁崇焕都是清代大力表彰的明末忠臣,王在晋与他们的冲突被记入《明史·孙承宗传》,导致其人在主流的历史叙事中形象并不光彩。
王在晋写作《三朝》一书,不仅是记录历史,而且也是为身为失败者的自己辩白。由于抱着这样的写作目的,本书不仅对袁崇焕、孙承宗等人肆意丑诋,还“详略失当”:对其他人的奏疏,王在晋大多节略摘抄;而对自己任山东巡抚、兵部侍郎、辽东经略等职期间的奏疏,则是一字不落。以至于本书甚至更像是王在晋本人的一部奏议集,那些穿插在冗长奏疏之间的记事文字,就是对奏疏背景的注释。

然而,这种历史编纂上的“头重脚轻”之病,或许反而正是本书价值所在。文集、奏议作为明史史料之大宗,其独特价值越来越得到学界公认,尤其是督抚、经略这样的地方大员,通过他们的奏议可以了解明代政务运作、央地关系、财政经济、地方社会等方方面面。更遑论王在晋亲历辽东战争这样天崩地裂的大事件,直接参与军事决策,其每一篇奏疏对读者而言都弥足珍贵。
而且,晚明人物多有一股愤愤然的“不平之气”,为了一吐自己胸中块垒,争一时意气,莫说是历史编纂的原则、客观公正的写作道德,就是个人的性命,有时也不在话下。王在晋这种对自己的政敌毫不掩饰地诋毁谩骂,为自己不遗余力地辩白,虽有失忠恕之道,却隐隐透出晚明独特的时代风貌。这种充满“不平之气”、可笑可叹的时代风貌经过清代规行矩步的规训,现代化浪潮的洗礼,对今天的人们早已显得面目生疏,反而具备了独特的新鲜感和趣味。
而《三朝》一书作为失败一方的历史记录,也有其独特性。除去书中对胜利者带有感情色彩的贬抑,如“奴酋”“建夷”之类称呼字眼俯拾皆是,对于一些后来清王朝讳莫如深的事件,书中也有明确的记录,提供了来自明朝一侧的视角。例如创业前期,努尔哈赤与其弟舒尔哈齐之间的矛盾,《三朝》一书直言不讳地记载:“奴酋忌其弟速儿哈赤兵强,计杀之。”(《三朝辽事实录·总略》,点校本第16页)

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17世纪上半叶的这场辽东战争,绝不仅仅是明与建州女真双方的矛盾,东北亚地区的朝鲜、蒙古各部、女真各部也都卷入其中。关于朝鲜与明朝就辽东问题的交涉、明末蒙古各部在辽东地区的活动,《三朝》一书也都留下了宝贵的记载。当然,以上种种无一不刺激着清代统治者脆弱的神经,这直接导致了本书在清代传播不广,除崇祯十二年(1639)一种刻本之外,只能以各种抄本的形式流传。如此也更显现出这种“失败者的声音”能够从历史上流传下来,是一件多么可贵的事情。
晚明引人瞩目的大事除了辽东战争,就是东林党与其政敌之间的惨烈政争。历史研究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在看似毫不相干的史料中找到自己问题的答案,本书虽着墨于辽事,但对研究晚明政治史也有独特的价值。本书所涉及的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人,都或多或少地卷入了晚明的政治漩涡中,本书对研究他们与晚明政治的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如本书卷七详细记录了九卿、科道会议“经抚去留”问题的议单(点校本第263—265页),从中可以看到朝臣对于熊廷弼、王化贞二人矛盾的态度,进而可以破除“东林党支持熊廷弼,阉党支持王化贞”的成说。
除此之外,本书在政治史的研究方面,同样提供了来自失败者一方的声音。东林党在明末清初逐渐被树立为正义一方,其反对者在主流的历史叙事中遭到否定。无论是万历四十年代的“齐楚浙”三党,还是天启后期的阉党,其成员的著述均罕有传世。而《三朝》一书于朝中党争没有表现出很强的立场倾向。无论是万历末年当权的官应震、姚宗文等人,还是天启后期依附魏忠贤的王绍徽、崔呈秀等人,只要他们的奏疏有关辽事,本书都会加以摘录。今天的读者,阅读需求已转向尽可能客观地了解历史的不同面向,如此一来,《三朝》一书中这些来自“反面角色”的声音更显出了其独特的价值。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哲学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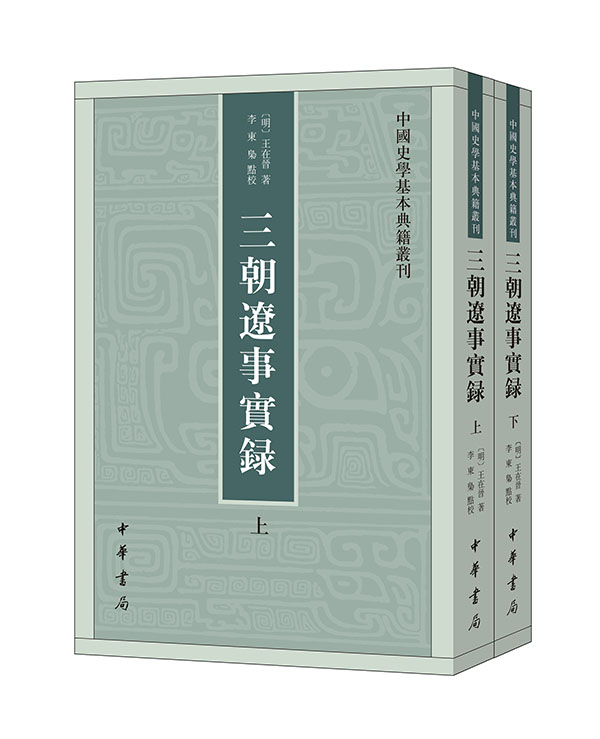
[明] 王在晋 著 李东枭 点校
《三朝辽事实录》是一部著名的明代军事著作,成书于崇祯十一年(1638),共十七卷,卷首另有总略一卷。本书在总略部分概述辽东的分野、区划、战略形势,以及辽东周边各民族的历史及与明朝的关系,作为明金战争的背景;正文部分按年月编排,历叙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努尔哈赤计袭抚顺至天启七年十二月明金战争相关事件,包括战守要略、朝廷决策、筹饷运饷、军队管理、方略争议等内容,引用了大量当时有关辽事的奏疏、邸抄等。本书还载录作者关于辽事的奏疏,借以表明对辽事的主张和建议。
《三朝辽事实录》在清乾隆年间被禁,版本源流相对单一,本次整理以现存最早的明崇祯刻本为底本,对于影响文意的疑误,利用他书出注论证。
王在晋(约1568-1643),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累迁江西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进河道总督,兵部左侍郎署部事。天启二年(1622)曾代熊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诗文方面颇多著述,著有《通漕类编》《海防纂要》《三朝辽事实录》等。
李东枭,1993年生,黑龙江哈尔滨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涉及晚明政局、明金战争等。2019-2022年在中华书局编校部工作。曾发表论文《熊廷弼反对“以辽守辽”探究》(《地域文化研究》2018年第5期)、《万历中后期明朝辽东战略的调整》(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明史纪事本末补遗·辽左兵端〉校读》(台湾《明代研究》第35期,2020年)。

www.zhbc.com.cn zhbc@zhbc.com.cn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邮编: 1000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