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文化教师素养读本
作者:楼宇烈,傅首清主编
定价:¥58.00
中华文化教师素养读本
作者:楼宇烈,傅首清主编
定价:¥58.00
-
 辽史--全五册(精)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
作者:脱脱著 刘浦江整理
定价:¥280.00
辽史--全五册(精)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
作者:脱脱著 刘浦江整理
定价:¥280.00
-
 南明史(精装本)
作者:钱海岳撰
定价:¥980.00
南明史(精装本)
作者:钱海岳撰
定价:¥980.00
-
 宋书(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平装本)
作者:(梁)沈约 撰
定价:¥360.00
宋书(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平装本)
作者:(梁)沈约 撰
定价:¥360.00
-
 魏书—(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精装)
作者:魏收著 何德章,冻国栋修订
定价:¥510.00
魏书—(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精装)
作者:魏收著 何德章,冻国栋修订
定价:¥510.00
-
 史记--全五册(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精
作者:[汉]司马迁撰 陈曦、王珏、王晓东、周旻译
定价:¥298.00
史记--全五册(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精
作者:[汉]司马迁撰 陈曦、王珏、王晓东、周旻译
定价:¥298.00
-
 全元词(全三册)--中国古典文学总集
作者:杨镰主编
定价:¥298.00
全元词(全三册)--中国古典文学总集
作者:杨镰主编
定价:¥298.00
-
 金史(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精)
作者:[元]脱脱等撰
定价:¥540.00
金史(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精)
作者:[元]脱脱等撰
定价:¥540.00
-
邹鲁文化研究 作者:贾庆超等 定价:¥0.00
-
 明实录 附校勘记(183册)布面精装
作者: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 黄彰健校勘
定价:¥45000.00
明实录 附校勘记(183册)布面精装
作者: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 黄彰健校勘
定价:¥45000.00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题为《先秦战略地理研究》,早在1999年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行,这次承蒙中华书局的重视予以改版再印,更名为《先秦战争与政治地理格局》对此谨表示由衷的感谢。今岁是导师宁可先生逝世十周年,回想我一生的治学经历,曾接受先生的诸多教诲。如果没有他的引导,自己是根本不能踏入宝山、斩获而归的。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我得以进入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就读,毕业留校任教后,宁可先生曾有三次重要的培养指导,使我得以在专业上进步攀升,至今记忆犹新,特借此机会叙述如下,或许能对读者有所助益。
1982年初,我成为一名高校教师,由宁先生指导的毕业论文《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几点认识》又在本校学报上发表,其观点后来被收入白钢先生编撰的专题论著【1】,因此踌躇满志,一心想写长篇大论。不料宁可先生安排我做微观问题的系列考据,他说汉代《九章算术》书中蕴藏了许多有价值的经济史料,以往未得到充分重视,要我对它进行系统的发掘研究。这部算术书包括246道应用题,涉及农耕、商贸、物价、交通、赋税、徭役以及爵位等广泛领域,但多数内容很琐碎,而且往往是孤证,在正史中很难找到相关记载,需要从庞杂的文献和金石、简牍资料里去搜寻有联系的线索来参照分析。这类研究工作可以借用一个围棋的术语来比喻,就是“治孤”。考据的原则是“孤证不立”,立论必须有较为充分的史料依据。而围棋的“孤子”也是死棋,必须做出两个“眼”或者是和附近的大棋联上才能成活。我对《九章算术》的探讨非常艰难,寻找可用的史料如同沙里淘金,完成某个具体问题的论证往往需要好几个月,这项课题拖延到1990年结束,陆续撰写了11篇论文,最后汇成专著《〈九章算术〉与汉代社会经济》出版。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这项研究得到了学界的关注,其中《〈九章算术〉记载的汉代徭役制度》《〈九章算术〉所反映的汉代交通状况》两篇论文被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九章算术〉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史料价值》一文受《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推荐,刊登在美国《波士顿科学哲学研究》年鉴第179卷上。
尽管《九章算术》的科研任务耗费了我8年光阴,但是由此练就了考据的本领,后来认识到这是自己在高校职场安身立命的必要技能,这才明白了导师的用心。考据虽然属于微观史学,却是宏观研究的基础。若是过不了这一关,那么撰写巨著难免会失之空泛和出现明显的疏误。治学的能力要逐步提高,从学会微观研究再过渡到宏观探讨,不可能一蹴而就。正是因为我熟练掌握了考据的基本方法,后来才有可能写出《汉代监狱制度研究》《汉代宫廷居住研究》等重要著作(前者入选2012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为此对老师深表感激。
另外闲扯两句,我喜欢阅读马里奥·普佐的《教父》,书中写到教父的养子汤姆·哈根在大学毕业之后,提出要担任家族的专职律师。教父科里昂表示同意,却坚持让他到律师事务所去实践了三年一般性的法律事务,这段经历后来证明是汤姆获得的无价之宝。他又经过两年处理刑事案件的锻炼,成熟之后才当上了家族的“军师”,即高级顾问。看到这里,我就联想起导师让我做了多年考据的事,小说写得合情合理,想想觉得有趣。虽然把两者相提并论有些欠妥,但都说明了提高业务能力必须循序渐进的道理。
《九章算术》的科研任务结束以后,在两三年的时间内,我没有大的课题可做,零零散散发表了几篇论文,内容属于不同领域,都是分散孤立的作品,彼此没有联系,就像俗话所说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宁可先生敏锐地注意到这个问题,又专门找我谈话,提醒我要注意集中研究方向。他形象地比喻说,搞科研不能是“狗熊掰棒子”,夹一个掉一个,最后肯定不会有丰富收获(这是委婉地批评我)。最好是进行“滚雪球”式的研讨,为自己设定一个规模较大的组合式课题,这样创作的各篇论文内容相互关联,不仅资料利用方便,而且容易启发拓展思路,编织成网络。成果则日积月累,越来越多,将来能够形成鸿篇巨著。他还推荐我阅读严耕望先生的《治史经验谈》,里面讲到史学研究的要旨之一,就是如何选题,强调年轻人经验和能力不足,应该“小题大做”,尽量把论文内容写得很充分;中年人年富力强,要“大题大做”;老年学者精力衰退,最好是“大题小做”,对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概要想法,可以由后人去充实。我想这正与宁可先生对我的教诲相吻合,他当初让我研究《九章算术》,就是“小题大做”,现在则需要“大题大做”了。
这次谈话之后,我开始认真地思考今后的科研道路与课题方向。首先,是要确定在哪个领域开展探讨,我搞了8年社会经济史,觉得它有些枯燥与冷漠,如某位学者所说,是“缺乏人性化的研究”,不太符合自己的性格与志趣。我一向喜欢阅读军事历史,特别是战争史,要是能把兴趣爱好与职业劳动结合起来,工作就会更有激情和动力。但是有关中国古代战争史的论著连篇累牍,尤其是当时军事科学院主编发行的17卷20册《中国军事通史》巨著,对每个朝代的兵制、装备和战史都有系统深入的论述。自己要想在这个领域有所创建,必须另辟蹊径,采用新的研究视角或理论方法,才能获得突破。这时我想起了大学三年级时,宁可先生开设的课程中有一个系列专题——《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理环境》【2】,他讲授了东亚大陆及其内部各历史区域的概况与特点,以及它们对中国古代历史进程起到的重要影响,内容高瞻远瞩,发人深省。后来我与几位同学议论,大家都认为这是本科学习期间印象最为深刻而且收获颇多的课程。那么自己是否能够以此为例,从地理角度出发去探索中国古代战争的规律和特点呢?有了这个想法,我就开始学习军事地理学的论著,并关注这个领域的发展动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国的军事地理学出现了重要的变化,就是衍生出一个分支,即战略地理学。开始是一些论文,后来涌现出几部专著,例如陈力的《战略地理论》、雷杰的《战略地理学概论》,还有董良庆的《战略地理学》。这门学科的任务,是以地理环境为依据,来分析战争形势,拟定战略方针和计划。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它的研究对象,有战争爆发的地理背景、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御的主要方向及交通路线、后方根据地与前线的联系、全国的兵力部署、战线的分布、战区的设置、战场的选择等等。战略地理学采用了崭新的理论与研究视角,虽然它分析探讨的是现代战争,但也适用于研究古代的军事领域,正如某位先哲所言:人体解剖可以作为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我了解上述情况之后,随即怀着喜悦激动的心情向宁可先生做了汇报,并且提出来想把科研的重点从经济史转移到军事历史地理方面,采用新的理论方法来指导研究工作,感觉这样做可能会取得更多的成果。宁可先生听后表示赞同,并且提出一个研究方向,让我考虑一下“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对抗与南北战争”这个课题。它的时间跨度很大,从先秦一直延续到南宋末年,自元朝以后,中国不再有长期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他说这项研究可以从先秦时代开始,在它的三个历史阶段:三代(夏、商、西周)与春秋、战国,政治和军事斗争的地理表现形式差异非常明显,各有自己的鲜明特点。三代是东西对抗,春秋主要是齐、晋与楚、吴进行南北争霸,战国在商鞅变法后逐渐演变为秦与六国的东西抗衡。另外,宁先生还强调在研究当中要注意宏观与微观问题的结合,既要有对战略形势的总体分析,又得顾及具体的战场和作战区域,特别是地理枢纽,即所谓“兵家必争之地”。他还让我再读一下以前推荐过的世界名著,即英国学者麦金德所著《历史的地理枢纽》。
按照先生的指示,我开始着手写作,在两年内完成了课题中“三代篇”的三篇论文,并在发表后引起学界注意。其中《三代中国的经济区划、政治格局与国家防御战略》和《三代的城市经济与防御战争》被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前者还被《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摘要转载。这增加了我继续努力的信心,并产生了在宁可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的想法。记得《〈九章算术〉与汉代社会经济》一书出版后,我呈送给宁先生,他当时说“这可以算作一篇像模像样的硕士论文”,似乎对我是本科学历、未能读研深造有些遗憾。这次写作的《先秦战略地理研究》,若能以博士学位论文来完成,就可以使自己成为老师门下更高层次的学生。读博不仅能够提高我的业务能力,而且会有更加充分的时间来进行研究,因为学校规定教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最后一年可以免除教学任务。我找宁先生谈了自己的想法,他听了很高兴,表示支持,说专业考试估计我没什么问题,毕竟讲了这么多年通史课,但一定要重视外语考试,做好充分准备。结果一切顺利,我在1996年夏通过考试,秋季入学。本科毕业十几年后,又搬进了母校提供的宿舍,见到前两届的几位同门博士生,他们都比我年轻得多,却调侃说考入宁先生门下的时间要比我早,让我叫他们师兄。我回答说15年前撰写本科毕业论文的时候,先生就是我的指导教师了,自己入门要比他们早得多。
在转向做军事历史地理研究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些非议,有人说军事问题应该由部队院校的专家们去研讨,这不是历史学者的任务。年轻教师不去钻研经济、政治和文化课题,却要搞什么军事和战略,这属于不务正业。我知道后有些担心,便和老师讲了,宁先生听后一笑置之,说有这种观念的并不是个别人,还有些人比他们稍微开明一些,认为历史学可以研究兵制,但其他的军事问题除外。他说西汉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包括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其中就没有兵家。但时至今日,这种思想就变得陈旧了。尤其在先秦时代,战争对社会的影响非常重要,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军事问题理所当然是历史研究的对象,让我不要理睬那些流言蜚语,只管安心研讨。
另外,有位同行看了我的论文,提出战略应该是将帅指挥作战的计划和谋略,而我从地理角度出发,论述的内容有些是国家在和平时期的兵力部署,还有都城的设置与居民迁徙等措施,和战斗厮杀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根本就算不上是战略。对此要做一些说明,我和这位同行所表述的“战略”概念是有区别的,“战略”这个现代名词具有两个层面,即军事战略和所谓“大战略”,前者即如那位同行所言,是统帅将领指挥作战的谋略,完全是从军事方面来考虑、制订和施行的,故其早期又称作“将道”。后者则是国家从全局考量并实施的一种长远的总体作战规划,它的内容除了军事战略还有政治、经济,乃至科技等诸多方面的举措,争取在战前或在战时能够最大限度地削弱现实与潜在的敌手,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因此是宏观的、综合性的。对这种复杂的国家战略应该从多种角度进行分析研讨,这样对它的认识就会更加全面和深入。正如《易经》所言:“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就是说可以用各种思路和视角来完成对某个问题的探讨理解,而不要拘泥于一孔之见。在我的研究中使用的是后一种广义的“战略”概念,而那位同行对此并不清楚,所以产生了某些误会。
读博期间经过老师的引荐,我结识了几位前辈学者,请他们审阅和帮助改进博士论文,其中有北京大学的吴荣曾先生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洪廷彦先生。这些前辈都很热情,对我进行了鼓励和辅导,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洪廷彦先生喜欢研读《左传》,他说看了我的博士论文,当即打电话给一位老朋友,说有个年轻人熟读《左传》,他写的书稿很有意思,你也来看一看吧。洪先生说现在许多搞先秦史的青年人不愿投入大量时间去阅读经书和诸子,热衷于“短平快”的工作,抢着给新出土的器物与甲骨金文作考释。这样做当然很有必要,而且容易发表成果,但是此类资料数量有限,以致相关论文经常出现重复“撞车”的现象,而且长此以往,个人的研究会陷入“碎片化”,难以完成宏博的课题。年轻人像你这样运用古籍研究先秦历史的并不多见,所以我看了书稿很高兴。后来吴、洪两位先生参加了我的论文答辩,由年长的洪廷彦先生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他们都对论文给予了很好的评价。
《先秦战略地理研究》结束后,我未能把宁可先生提出的“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对抗与南北战争”这项课题沿续完成。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缺乏工作时间,按照历史系的安排,我提升教授后要招收培养秦汉史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并负责这个专业方向的学科建设,不仅承担相关的科研、教学任务,还要申报秦汉史领域的社科项目,需要投入许多时间和精力。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必须认真努力地对待,绝不能敷衍。但是这样一来,有关军事历史地理的研究就变成了我的副业,甚至是业余活动,无法像读博期间那样把全部身心灌注进去。第二是自己的能力不足,从秦汉到南宋末季历时千余年,在此期间的战略地理研究内容过于庞大。试想先秦时代资料有限,我的博士论文还花费了6年时间,那后边各个朝代的史料和参考论著越来越多,可以说是浩如烟海。以个人眇眇之身,要想全部阅读领会,再都写成论文,恐怕终生也完成不了。正如庄子所言:“以有涯随无涯,殆矣!”无奈之下,我采取了取巧的办法,就是从宁可先生提出的大方向中选取一系列要点来建立课题,写作一部《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在先秦到南宋的每个朝代选择一两个“兵家必争之地”来进行探讨。先秦几个战略枢纽的研究已经写好了,就从秦汉三国开始。这样经过十度春秋的努力,终于在2009年写成了这部著作,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发行,将它交到了老师的手里。
回想宁可先生对我的培养,屡次在自己学术成长过程的关键时刻给予指导,使我能够顺利跨越几道重要的门限,为此感恩不尽。有一次和我谈话时,他的心情很好,说起对学生的辅导教育。宁可先生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创建元老之一,他说那时候指导几个青年教师,言传身教非常认真仔细,几乎是手把手地教他们专业写作,要求非常严格,甚至在教案中发现几个错字,都会把作者叫过来训斥一顿。但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他的教育方法和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先生说现在看到你们的论文有错误或是别字,我也就是用笔勾画一下,提醒你们自己注意纠正罢了。他关注的主要是学生们的研究方向与文章立论等重大问题,其指导也是启发式的,往往点到为止,不做深究,让你自己去领悟。先生从不在我们研究的具体问题和看法上进行干涉,任凭大家自由发挥。记得有位学友的论文观点相当偏颇,宁可先生对此并不认同,但是经他点拨后,那位同学仍不愿改动,先生也顺其自然,未予强迫。这正是孔子所说的“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直到后来,那位同学的论文在外审时遇到了麻烦,几位专家都提出了质疑和反对,这才在先生的协调帮助下修正通过。
读博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给我很大的震动。我在写完《春秋地理形势与列强的争霸战略》一章之后,觉得它的质量比以前发表的几篇论文要更好一些,于是斗胆投稿到一家知名刊物。过后接到责任编辑的电话,说编辑部经过讨论,愿意发表稿件。但是这家刊物的用稿都要经过某位权威专家的审阅,由他来最终决定取舍,让我再等等消息。这位专家素有声望,我对他的学识和著作很是敬佩。可是他已然年迈,又身兼数项要职,拥有很高的地位,怎么还会屈尊下驾,亲自审查这家刊物发表的所有稿件,无论长短一一裁定,这样岂不是过于辛劳、大材小用?我虽然觉得有些诧异,但也没有往心里去。
几天以后又接到编辑的电话,说先生看了你的文章表示认可,同意在刊物上发表,并写了几点修改意见,我们已经将它邮寄给你。刊物准备在近期采用这份稿件,请你尽快订正后寄送回来。我获悉论文得到权威人士的肯定,为此兴奋不已,随后接到这位先生的手书便笺,立即遵照指示修改寄回。不料过后编辑再次打来电话,有些尴尬地对我说,他们把近期准备发表的一组稿件最后送给那位先生过目,没想到他看见你的文章勃然大怒,厉声道:“这篇稿子不能用!必须退稿!”我们非常吃惊,不明白先生为什么突然改变态度,也不知道你的论文怎么会惹他发那么大的火,我们不敢询问,只好把稿子拿了回来。编辑随后又对我说,他在这家刊物工作多年,从未发生过此类事情,也没有见过先生发这么大的脾气。无论如何,这篇稿子是不能用了,请你改投别的刊物吧。
此前我经历过几次杂志社的退稿,都能心平气和地对待,但这次退稿相当荒谬,让我瞠目结舌。虽然心里颇有想法,但出于对那位专家的尊重,我不愿把它写出来。后来看央视的电视剧《大染坊》,剧里的陈掌柜说:“什么叫走运,遇见明白人就是走运。”我对此深有同感。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如果不是遇到那些热情友善、胸怀开阔,而且乐于提携后进的前辈学者,怎么会有今天的些许成绩?能够获得宁可先生的多年指导,实在是我毕生的幸运。
最后说一下,首都师范大学的杨生民教授,对我写作这篇博士学位论文提供了诚恳的帮助,使我获益良多。我在大学二年级时撰写的第一篇论文习作,被任课教师呈送宁可先生,他认为具有新意,就推荐给本校学报。编辑部同意刊发,但要求压缩到7000字以下。那篇论文原来有2万多字,我减到1万来字,就无论如何删不动了,以至于智力枯竭,无从下手。多亏杨生民先生亲自动笔,替我把论文删到6700余字,而且文章的脉络保持完整,重要的论点和史料引证都能保留,最终得以发表。杨老师当时主动为一个普通学生修改文章,使我摆脱困境,他的仁心善举和专业水准令我感动钦佩不已,始终难以忘怀,在这里一并致谢。
注释
(1)参见白钢编著:《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14—215页。
(2)笔者按:宁可先生的《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理环境》一文,已经收入《宁可文集》第八卷《地理环境和中国古代历史》,人民出版社,202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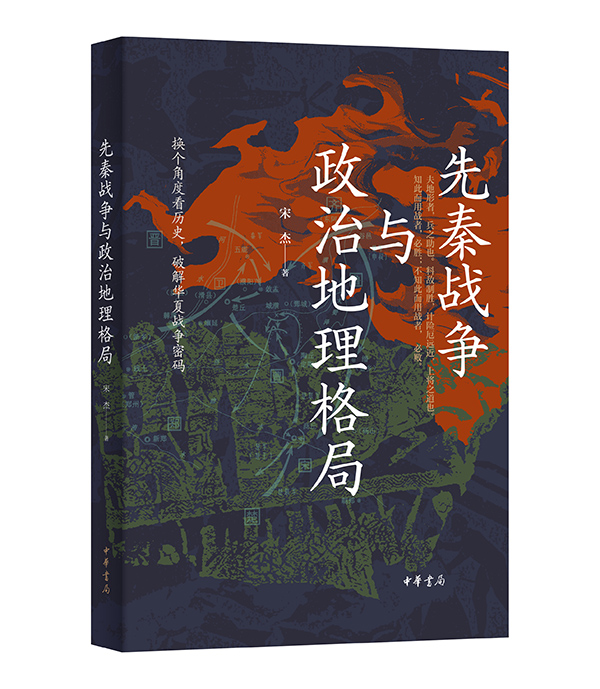
《先秦战争与政治地理格局》一书,对先秦各历史阶段经济区域、人口、民族和政治力量的分布,以及各区域的地形、水文、风俗文化状况与相互来往的交通路线进行考察,并着重探讨这些因素对作战方略形成、演变所起的制约作用,即地域差异与空间变化和军事活动之间的的密切关系。全书分为《三代篇》《春秋篇》和《战国篇》。本书为军事地理专家宋杰教授的博士论文,本次出版做了细致修订,并增加18幅战争形势示意图,双色印刷。本书资料详实,视角新颖,换个角度看中国史,看清战争背后藏着的秘密,破解华夏战争密码。
宋杰,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史及历史军事地理,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著有《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三国军事地理与攻防战略》《三国战争与地要天时》《三国人物风云录》《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两魏周齐战争中的河东》《先秦战略地理研究》《汉代监狱制度研究》《汉代死刑制度研究》《〈九章算术〉与汉代社会经济》《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等,其中《汉代监狱制度研究》入选2012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www.zhbc.com.cn zhbc@zhbc.com.cn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邮编: 100073

